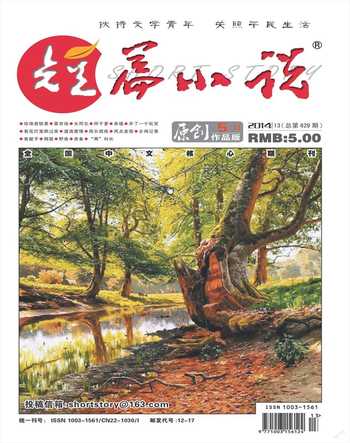《消逝的大列》映射的當代農村小說敘事策略
張亞婷
大多優秀的文學作品都是通過塑造清新感人的人物形象來追求事件真實的本質。因此在不同時期,中國當代作家在創作過程中以各自不同的思想差異為基礎,在否定中扎實前行,為我們展示出了形態各異的中國形象。作為農業大國,中國農村人口數量的比重較大。因此在國際化的今天,農民形象被認為是中國的主要形象之一。那么,透過集中和零散的文學作品,深入地理解和清楚地表達當代農村小說中所展現的中國形象和中國特色就顯得意義重大。本文以《消逝的大列》為例分析當代農村小說的敘事策略。
一、典型的集體主義背景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經濟主要是推行前蘇聯模式,在全面發展重工業的同時,加強農業生產。在國際事務中,同樣依靠前蘇聯,聯合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奉行著底層外交政策。為了國內經濟能夠進一步發展,加之同時開展的抗美援朝國際行動,集體主義、大公無私成了光榮、輝煌的代名詞。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分析,只有集體主義才能夠實現革命的真正目的。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就是要確立集體利益,使私人利益和集體利益保持高度的一致。而與前蘇聯關系破裂以后。為了抗擊前蘇聯和美帝國主義對我國經濟、政治帶來的侵略和影響,中國開始團結亞洲和非洲等的發展中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使得集體主義語境成為了不同小說中共同的中國形象。
在小說《消逝的大列》中提到農民張三每天都要“開著川野車去拉玉米秸”,而“這大列一停就是一個多小時,結果張三的秸稈沒按時拉完”。作者通過這典型的集體主義語境向我們展現了小說中的時代背景,介紹了集體主義背景下農民家家戶戶被集體分配任務的實際勞動情況。該小說用詞簡潔,語言樸素,用故事中最簡單的敘述在故事的開頭既寫出了事件的起因,也交代了背景,便于讀者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了理解人物的行為和心理。
二、復雜的人物形象
隨著文學的進步,新時期以后,彰顯個性成為文學創作中的新主題,人物性格不再如舊時期般單一,而是越來越復雜。作家們不愿再去講述英雄人物的事跡,而是有意地塑造個人英雄主義形象。小說創作中的人物形象塑造方向發生了巨大的改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逐漸變得模糊。作家在作品中還原生活的同時,再也無法創作出和平年代的先進農民形象了。因為他們不再單一地將人分為好人和壞人,不再模仿魯迅的批判,更不會與沈從文一起討論真善美與假惡丑之間的關系。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商品經濟的涌入,許多作品都受到了影響。在小說《消逝的大列》中,主人公張三便是以全新的文學視野和性格理論所打造出的典型農民形象。伴隨著改革開放前進的步伐,農民的命運也發生了改變。生長于這個時期的農民張三將農民的全部特點集于一身,既勤勞,又狹隘,正是這樣一個生動的人物形象與老百姓拉近了距離。而人物本身性格復雜的特征和清晰的條理使得張三這個人物更加真實可信。該小說中張三的性格看似簡單,實則復雜。作者周到地考慮到了每一個因素,因此張三這個人物的性格既不單調,也不凌亂,在復雜中達到了一種和諧。
另一篇與《消逝的大列》中人物性格相似的是1982年在雜志《收獲》上曾經刊登過的一篇中篇小說《人生》,該篇小說以獨特的視角、細膩的筆觸對農民的思想意識進行了生動的刻畫。通過對主人公高加林的人物塑造,為廣大讀者展現了一個生活在城鄉接合處的生活不順的年輕人形象。而正是這不同以往的人物卻以其思考的深度展現了非凡的魅力。高加林聰明好學,勤奮刻苦,他不滿足于現狀,希望自己的人生變得更好。為了實現這一目的,他背棄追求多年的女友去追求城市姑娘。高加林的這種自私和自我的表現不同于一般作品中我們所看到的上進青年,因此顯得個性更加鮮明。正是這樣個人主義色彩濃厚的人物形象映射出了中國青年農民的形象。高加林再次返回農村,這時在讀者心里城市變成了道德失落的代表詞。在理解高加林這個人物的時候,我們不能脫離作品的背景來分析人物個性。也許高加林并不是一個英雄或者模范,但是我們也不應該一味地批評他是一個逃避的懦夫,抑或是十惡不赦的壞人。我們應當結合作品中高加林所處的環境和經歷進行合理的分析。而分析后便不難看出,高加林的思想內涵及其個性的多元化代表了那個時期中國農民形象特征。
三、負面的人物性格
21世紀的中國,隨著改革開放腳步的不斷加快,市場經濟也在不停地向前穩步發展,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都有了不小的進步。加入了WTO之后,中國對外實行務實的外交政策,更多地參與到國際和地區事務中來,并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以上的這一切都使得現在的中國具有了更加獨特且更加真實的魅力。隨著中國不斷地繁榮富強,全世界的目光都在聚焦中國,這也使得中國文學在世界上越來越受到各方面的關注。而這一時期的農村題材小說開始走出原有的模式,創新思路,更多地關心農民當下的生活狀態,關注“三農”問題。在我國,農業、農村和農民這“三農”問題關系到國富民強及社會的穩定繁榮。因此在農村題材的小說中,農業實施產業化、戶籍制度導致的城鄉二元分割,以及如何提高農民素養和減少農民稅負等問題,就成為當代農村題材作品的主要表現內容。這固然將小說中所體現出的中國形象帶入了一個嶄新的藝術層面。21世紀的今天,許多作家仍然在自己的作品中以農民的負面性格作為主要題材,小說《消逝的大列》中主人公張三貪小利吃大虧的人物形象就充分地展示了人性固有的本性和欲望,形象地描繪出了當代農民自私貪婪的人物形象。
四、真實的生存狀態
進入21世紀,中國在世界上已不再是單一的勤勞勇敢和妖魔化的封建形象,而是極具民族性格的多元化形象。而農民工形象則成為了這個時代農民轉型過程中的記錄存在于文學作品之中。他們大多在經濟較為發達的大城市里打工,無奈的選擇和苦悶的工作成為了他們生活的全部。而正是這樣的生活讓我們看到了新的中國農村影像。在小說《城市里的一棵莊稼》中,女主人公崔喜被作家李鐵塑造成了一個充滿矛盾的農村女子形象。她的內心既自卑又自尊,對于愛情與家庭,既渴望又壓抑。小說通過對崔喜的人物刻畫向我們展示了一個農村女子從農村到城市的心路歷程。對大多數農村姑娘而言,去往城市充滿了神秘色彩。正是這樣的神秘在吸引著她們的同時也帶給她們許許多多難以訴說的苦痛與掙扎。然而作品中的崔喜通過婚姻獲得了城市戶口之后,卻無法真正融入其中。在擁有了城市人的生活之后,她卻走入了“既不像農村人,也不像城里人”的模糊地帶。城市的神秘色彩吸引著農民工不斷涌入,并堅定著他們的信念。可是農民工對城市的單純思想與城市本身現代化的復雜形成了想象與現實的錯位。于是若干年后,他們成了農村與城市之間游走的一族,依舊追逐著夢想,也依舊盲目。作家賈平凹于1996年出版的《土門》中對農民個體欲望的描寫極具代表性。小說中通過城鄉對比,明確了農村逐漸向城市轉變的趨勢,對現實中城鄉的各有利弊也進行了雙重解釋。這種對農村的描寫,往往體現了作者對故鄉的思念。作者在以平民視角的敘述中為讀者展現著當下城鄉結合的當代農村。
通過《消逝的大列》不難看出,當代農村小說的敘事策略無外乎是典型的集體主義背景、復雜的人物形象、負面的人物性格以及現實生存狀態的反映。可以說,中國當代小說中的中國農村與小說中農民映射出的中國形象是利弊并存的。在作家眼中,中國農民是作為中國形象的映射載體出現的,是新的希望與詬病的統一,是理想中的文化載體。而中國的鄉村往往在作家們的筆下成為了神話一般的存在,其中農民性格的兩面性更是作為作家們慣用的素材激發著他們的靈感。可是不論大家以怎樣的方式去了解鄉村,用何種視角去觀察農民,以什么樣的心態去評價中國形象,農民都是以一種“既淳樸,又有些簡單自私”的構想方式存在著。這些題材的農村小說中展示出的中國形象意義非凡,影響深遠。作品依照鄉村農民的現實生活情況和對他們喜怒哀樂的描述,展現著他們真實的心態和生存狀態。這些小說通過展現現實生活中深層次的矛盾沖突,通過對愛和憐憫的刻畫,將中國形象不斷向更高尚的精神層面延伸著。可以說,這樣的形象塑造令我們感到些許的振奮。可我們必須要指出,個人主義的肆意滋長在無形中腐蝕著集體主義和某些“公共的東西”。于是,團結在一起的集體身份再一次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進入我們的視線,震撼著我們的心靈。
[參考文獻]
[1]首作帝,張衛中.“十七年”農村小說話語的分層與配置——以《三里灣》《創業史》《山鄉巨變》為中心的考察[J].南京社會科學,2008(02).
[2]王慶,90年代農村小說的苦難意識[J].江漢論壇,2001(04).
[3]李美善,李文求與胡學文的農村小說比較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學,2013.
[4]王國雄,塞北農村變革與農民命運的深情抒寫[D].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