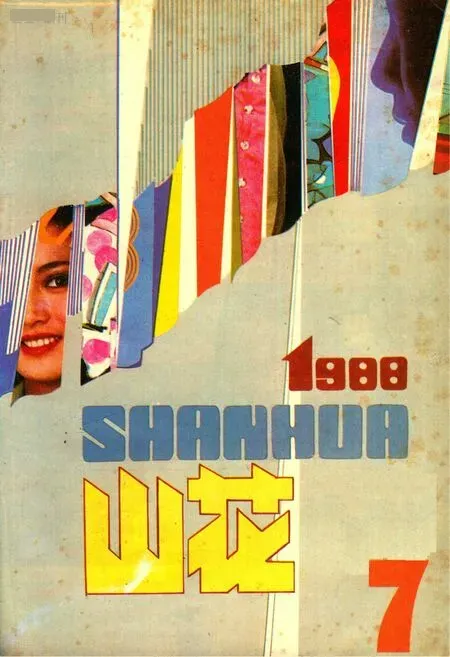故事盡頭
楊慶祥
《鬼雀》中有一種奇怪的聲音:“嘔,嘔”。這個擬聲詞并不常見,也許是作者想象出來的一種聲音,也或許某些偏僻的區域確實有這樣一種鳥類的存在,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敘述者需要這樣一種聲音來推動故事的發展。“嘔,嘔”在小說中反復出現,帶有一種宿命的意味,伴隨著這種聲音的,是一個個意料之外的死亡事件。《鬼雀》這部小說讓我想起80年代的某些香港恐怖片:在一個偏遠的,似乎處于文明社會之外的區域,存在著一種不遵循現代理性的生活,這一生活由此變得似乎難以理解,同時,也生成一種詭異的氣氛,讓生活在現代的讀者感覺到驚悚和恐懼。其實這一傳統最初的締造者是愛倫坡,他成功地將現代生活重新拋擲于“非現代”的原始語境,從而揭示人心的幽暗和人性的深不可測。《鬼雀》的發生學是否如此復雜?也許我是多慮了,也許在作者甫躍輝那里,文本的發生并不需要理智的多思,一種聲音,一種氣息,一個莫名其妙的夢境,或者,僅僅是站在上海的夜晚回想起故鄉的某個細節——就像普魯斯特《追憶逝水年華》中的瑪德蘭小點心一樣,故事就開始了。
《鬼雀》中有一種細膩的對于感官的敏感。那個懵懂的少年并不理解世事的兇險。他唯一與這個世界關聯的,就是他極其敏銳的聽覺。正是由這種聽覺,他和他周圍的世界發生了某種聯系。這種聯系同樣是懵懂而曖昧的,帶有人類在生命初期的那種原始性和神秘性。這篇小說最打動人的地方可能也正在于此:一切仿佛都在羊水之中,意識的源頭一片混沌。唯一的“聽覺”作為最基本的介質,試圖突破這種混沌,讓我們了解生命的本相。至此我們可以稍微回到故事之中:少年人聽到鬼雀的叫聲,擔心阿公死亡,接下來一連串的死亡開始發生:阿幺死了,奶奶死了,老太太死了,最后,阿公也死了。死亡在這里成為“事件”,因為死亡并非按照自然的規律來發生,它變形了,在某一個時間段以“重復”的發生昭示其不可抗拒的力量。少年人不服從這一力量,他以一種罕見的倔強試圖與“鬼雀叫,人要翹”的心理暗示和奇風異俗進行抗爭,而他的這種對抗,不過是招致了更多“不幸”的發生。相對于少年的這種不屈不撓,阿公——像所有小說中的智慧者一樣——選擇順從。他遵循古老的習俗去理解世界和死亡,去理解他聽到的聲音,即使這聲音將使他失去生命。少年人和老年人構成了這篇小說所營造的世界的兩極,他們構成一種成長式的平衡——老年人不過是從少年人蛻變而來,而少年,無論生命的意志多么頑強,都不得不接受無常的懲罰,并領受命運的安排。
即使作為短篇小說,僅僅憑借這一故事還是顯得單薄,但好在作者有另外的自覺,他試圖探討重要的話題,比如死亡:“阿幺死時,他沒哭;奶奶死時,他沒哭;阿幺曾祖母死時,他也沒哭。那時候,他只是被突如其來的死亡震住了,這就是死啊!直接、沉默、不可動搖。現在,這震住他的死亡的帷幕掀開了,后面竟還有一個廣大的、柔軟的、綿綿無盡的世界。他從來沒想到,還有這樣一個看不見的世界!這世界的遼闊和堅硬,讓他無所適從,也讓他無比哀傷。”他將死亡作為一個本體性的而非功能性(僅僅用來結構故事)的東西來進行思考,對死亡的兒童式的恐懼慢慢消失,一種更溫柔的感動上升——原來死亡如此廣闊,如此令人哀傷,而不僅僅是簡單的恐懼和拒絕。這少年人真的意識到了這一點嗎?還是甫躍輝故作老成地將自己的理解加之于作品中的人物?這些我們且不管他,因為在一個短篇中討論“死亡”之類觀念性的東西,畢竟有些風險,哪怕僅僅是意識到了這一點,這個作品已經相當不容易。我更感興趣的地方在于,在經歷了小說里發生的一切之后——或者說,在故事的盡頭,我們的主人公與世界之間的契約是否發生了變化?他與這個世界究竟構成了一種什么樣的關系?
回答這個問題不能僅僅局限在這一篇小說里面。這里有必要提到甫躍輝的另外一篇小說,同時也是他的代表作——《動物園》。這篇作品寫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相愛,他們兩情相悅,從各個角度看似乎都沒有什么障礙能阻止他們“從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動物園》的題目已經提醒我們這并非是一個童話,當作者安排他的主人公顧零洲住在動物園旁邊,一開窗就能聞到動物的氣味的時候,我們大概已經能夠猜測到,這意味著將出現不一樣的東西。這不一樣的東西出現了:男人喜愛動物園的氣味,而女人則討厭這種氣味。男人和女人因為這種不同的對氣味的態度而起了爭執,這爭執一路發展,竟然變成了兩個人之間一種隱秘的帶有強迫癥式的戰爭:他們彼此防范,像斗法一般開窗關窗。窗外就是動物園,紅色的象群在夜色中若隱若現。《動物園》里同樣有一種發達得過于敏感的感官,顧零洲有特別的嗅覺,他著迷于動物園的氣味,并試圖在這一“氣味”中建構出一個與眾不同的“自我”。這一氣味究竟是什么?李敬澤揣測其為一種“氣息”:“這是什么樣的氣息呢?我想甫躍輝其實也是說不清的,但他相信,有這樣一種氣息,它不是從外面來的,它來自生命的內部,這是‘存在的某種提醒,某種無法言喻的不安。”(李敬澤:《一句玩笑,換了人間》)因為這種提醒和不安,顧零洲和虞麗的愛情走了另外一條路——盡管他們在做愛的時刻是那么心心相印——但生命本身的裂隙不可避免地涌出,并狡黠地置換了最初的目的。
無論是《動物園》中的青年顧零洲,還是《鬼雀》中的少年阿育,他們都生活在一個日常的世界之中,并構成了這個日常世界的一部分——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一分子。但是,他們似乎有保持有某種“異秉”,他們的感官世界還保持著生命最初的敏感,并與外部世界保持著一種敏銳的互動——少年阿育聽到了鬼雀的叫聲,青年顧零洲聞到了象群的氣味——他們由此發現了生活和生命本身的空洞和裂隙,并透過這一空洞和裂隙,發現了常態中的“變態”,“有常”背后的“無常”。《動物園》和《鬼雀》的空間背景迥異,一個是偏遠的遠離現代的鄉土世界,一個是現代性的城市中心,慣性思維者會不加辯駁地將此做“鄉土寫作”和“城市寫作”的二分,這顯然是簡單而無效的。空間的背景在此其實并不重要,與其說甫躍輝關心的是一個空間問題,莫不如說他關心的是一個時間性問題。在將生活時間和故事時間錯置的過程中,空間的背景消失了,因為人活在永恒的時間之流中,所要追問的,不過是宿命的安排為何是此時此刻?只有在這個意義上,空間出現,并變得重要起來,因為,在這個重新出現的空間里,自我被重新規劃了。
在另外一篇小說《驚雷》中,開篇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非正常性的時空:雷雨之夜的一個橋洞。這個橋洞類似一個戲劇的舞臺,而閃電和雨聲構成了舞臺的背景,三個演員和一個觀眾——中學生、小青年、中年人以及敘述者——開始其告白,由此我們知道了中年人原來是一個殺人犯,他殺死了為生存所迫做妓女的妻子;青年人是一個小偷,他通過“偷”的方式反抗公司對他的無人性的盤剝;中學生則一臉無辜,他僅僅是來尋找他在雷雨中走失的狗。——在一個并非日常的,不過是暫時性存在的空間里,卻通過不同的敘述展示廣闊的社會視域,這是這篇小說的可取之處。它懸置了道德的判斷和同情心的廉價泛濫,僅僅是通過對話和動作來展示他們的性格和命運,通過回溯個人的歷史來揭示外部世界的冷酷荒謬。但即使如此,敘述者的態度也不過是,“他沒有太難過,拉上包的拉鏈,背在身后,默默地從橋下走出,慢慢地從河坡爬上公路。”這是很典型的甫躍輝的方式,無論是個人和外部世界之間發生了任何形式的沖突、摩擦和碰撞,他最終都回到人物的內部來化解這一切,由此那些錯置的空間,那些被敏銳的感官所觸碰到的異樣的世界,那些在“雷雨交加”之際所涌現出來的具有爆發力的人性和力量——可以與“巨象”媲美的力量——都消失得無影無蹤。
這或許就是我們這個時代意識和想象的無可奈何,在故事和生活的盡頭,并沒有大象,而僅僅是大象在無限遙遠的遠方傳來的一絲氣息,我們深深地吸一口氣,然后,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