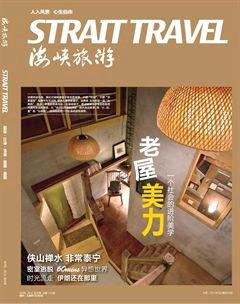落入孟加拉灣的安達曼

事實上,次大陸有很多邊緣封閉的區域,大多是在喜馬拉雅山南側,譬如拉達克,1972年才對外國游客開放;而印度東北靠近緬甸的幾個基督教少數民族邦,游客拿到許可也并不容易;尼泊爾的木斯塘,1999年才正式對游客開放,但時至今日,還是必須繳納500美元的許可費,再參加旅行社的團隊進入;至于把整個國家用價格來隔離嬉皮士和背包客的不丹就更不用說了。
安達曼群島和它們不同。如果說,喜馬拉雅山南側那些地域,敏感在中印戰爭后兩國的對恃。距離緬甸和泰國只有一個小時航程的安達曼群島對于印度的意義,卻是將印度洋真正變為“印度之洋”,島嶼也因而成了前哨。在拉達克開放了20年后,這個印度最遙遠的離島群才開始接待外國游客。
從次大陸到島上可以從加爾各答或者金奈飛,也可以搭乘一個星期的輪船抵達。我搭乘香料航空的班機到達群島的首府布萊爾港,飛行兩個小時多一點。在飛機上看地圖,群島最南端的那個小島,離蘇門答臘僅有兩百多公里,這使我對群島的居民充滿幻想,以為定然會是跳脫次大陸的典型面孔,跟東南亞邊緣的我相近,從而如在東南亞旅行一樣,獲得“自己人”的價格和自在。
在機場入境處認真填了旅游許可申請。仔細一看條款,原來緬甸公民不能去北安達曼島,這跟不允許中國游客進入拉達克的班公措部分倒是異曲同工。可是老實說,在1947年緬甸和印度分道揚鑣以后,能夠從安達曼島越過海洋到達下緬甸的人,一定也必須有魯濱遜的水平吧。印度對邊境的緊張程度,早就遠勝中國了。
機場外一片耀目的陽光,天空藍得像是電腦處理過的寶萊塢風光片畫面,絕無可能出現在現實生活中污染嚴重的次大陸,而掮客和三輪車司機都是與次大陸沒什么差異的臉孔。我坐在三輪車上,看著小城里的飯店招牌,不是孟加拉風味,就是泰米爾特色。那些海洋中依然聚居的原住民據說人口已僅有幾千人,且不是在北方的林區,就是在靠近馬六甲海峽的那些島嶼居住,想探訪他們,得老老實實留出起碼半個月時間。
我沒有那么多時間,只能直奔安達曼主島以東的哈弗羅島(Havelock island)。這個小島擁有群島中最漂亮的海灘群之一,而且居民不少,足以為游人提供食宿。要知道,整個群島也僅有26萬人口,除去那些前葡萄牙和法國殖民地,幾乎是印度最小的省級行政。
兩個多小時的快船抵達碼頭后,我跳上島上僅有的公共汽車,直奔第七海灘。這里的村落和海灘都以數字命名,頗讓人猜測其墾殖移民的歷史。而第七海灘果然名不虛傳,細白漫長的沙灘邊上,是茂密的,有著巨大樹冠的高大雨林,這比起椰林更可愛多了。記得第二天我躺在沙灘看夕陽將落的時候,森林一側的印度廟忽而搖搖晃晃走出兩頭大象,那是馴象人每日的遛象日程,也只有在印度的海洋,才能見到這樣一幕。
不由想起在讀關于蘇聯古拉格監獄系統著作時,看到的羅曼·羅蘭對蘇聯的辯護:“哪個國家沒有這樣的問題,英國人也將印度的政治犯丟到海中的安達曼。”但,如果他看過安達曼霞光萬丈的夕陽,永夏的海灘上清涼的海水,悶頭游泳的時候能看見清晰的白沙底,還會將這個世界跟西伯利亞最北的凍土帶相比嗎?
羅曼·羅蘭的確到過南印度,也見過孟加拉灣的海洋,他在金奈南邊一百多公里的法國殖民地本地治里呆過一段時間。然而把孟加拉灣的海水和安達曼的海水相比,就像拿蘇州河邊公寓里的自來水,跟喜馬拉雅山深處的泉水相比,徒惹人笑。
到底一個是擁擠的大陸,一個是海中央的天之涯。
我試圖在哈弗羅島步行旅行,然而很快就被灼熱的陽光打敗。盡管如此,經過那一座座丘陵之后的谷地,我還是能看出一些世外島民的樂趣,彈琴喝酒的男人,裸著上身自如沐浴的婦人,在禮教森嚴的次大陸,是不大可能存在的。
次大陸的禮教,在這遙遠的天涯,大概也收起不少。早晨和黃昏迷人的沙灘上,一對對印度本地情侶在甜蜜地擁抱,親吻,對著夕陽自拍。禮教尚有效的表征是:沒有人穿游泳衣,即使男人也不例外,短褲和T恤,已是勇敢的、開放的印度青年在海灘的大膽穿著。
不彈琴不作樂,好像也很難在這孤獨又熱鬧的島呆下去。盡管這里的時區實際上與仰光相同,但政府和人們都還老老實實地使用德里時間。這導致四點多就已天黑,而“早晨”八點的海灘,陽光已經大得不太適合跑步了。手機信號倒已經覆蓋了島上主要的居民區和旅館區,但是互聯網數據卻是被掐斷的,僅有罕見的兩三家網吧提供仿佛是20年前速度的網絡(打開郵箱需要等待幾分鐘),卻收取五星級酒店的收費標準。這仿佛在提醒人們,這里已是印度的遙遠前哨。
我試著騎自行車環島,卻發現并沒有真正的海岸線公路,吹了三四公里的海風后,常常會上坡,拐進一個個被丘陵擋風的平靜小盆地。從印度次大陸過來的移民在這里種植稻米和香蕉,從村屋的稀落程度看,他們可操作的農田,一定要比次大陸本土多得多。
呆了三天之后,我準備從哈弗羅島搭船回到布萊爾港,雨卻一直下個不停。波浪起伏,藍天碧海一下子被渾黃吞沒,瞬間變了世界。在浪里,我趕上了最后一輛敢于開動的船。
雨連下了三天,打亂了我要去內爾島(Neil island)的計劃,只能在海灣中的城市徜徉。昔日山頂關押那些“印度獨立分子”的監獄,如今掛滿了當年坐牢的革命者的照片。他們理所當然被視為英雄,但應該崇敬他們的那些21世紀印度青年,仿佛對研究他們的名字沒有興趣,只興奮地沖上牢房的最高頂,對著一望無際的海洋自拍。
大概天下的青年都是這樣罷,只關心手中的數碼設備。我猶記得在飛機上打開Kindle時,被旁邊一對情侶興奮地打招呼。原來男青年在亞馬遜的印度公司工作,問他印度人也會網購嗎,他自豪地說當然,盡管我很難想象,以印度繁瑣的工作效率和擁擠的路面交通,能將這購物的樂趣做到幾何。
“安達曼”之名來自印度神話系統中那個神通廣大的猴神(它也被認為是孫悟空這個形象的來源),可見它在印度文化向東南亞傳播的地位。然而,次大陸本土的帝國從來沒有征服這個群島,真正的征服者是英國人,他們在1789年開始經營群島。山頂上的監獄便是其最大的杰作。然后這幫享受的英倫精英,便在布萊爾港對面可看見監獄的一個小島,建起了喝茶的花園和大宅。從西邊來的印度人,和從北邊來的緬甸人,都不能在這個名叫玫瑰(Rose island)的小島上居住,除了仆役。
好景總是難以常在,更何況這用木舟就可以銜接緬甸和馬六甲的群島。第二次世界大戰日軍攻陷緬甸時,自然而然地把安達曼群島也當成了占領目標。玫瑰島在狂轟濫炸后,花不再開,紅顏亦憔悴。日本人和英國人都走了以后,經過將近七十年的封塵,這個小島成了另一個密林中的吳哥窟,只是那椰子樹下的殘垣,留的是維多利亞時代的步步驚心了。
搭乘快艇上島,穿行于這些破敗的熱帶英式大屋,有如身臨那些文明被毀的好萊塢科幻電影。然而看到海港周圍無處不在的日軍防空工事時又不能不感慨。我已經在蘇拉威西的托吉安群島見過日本墓,覺得20世紀的戰爭狂人們都要感謝地理大發現和航海人,現代地圖使他們可以比成吉思汗更能地毯式席卷平原與島嶼,一個不漏,這哪是從前的征服者所能想象的。
1947年以后,居住于安達曼的緬甸人大部分回去了他們的家鄉。布萊爾港唯一留下的關于他們的印記,只是一座非常小的南傳佛塔。安達曼已經成了印度人從英國人手中接來的海角遺珠,從此牢牢不放松。
尼佬,云南土著,Lonely Planet作者和專欄作者,一年在路有半載的旅行者,2013年底,深入印度三個多月,體驗經典的次大陸旅人漫游。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