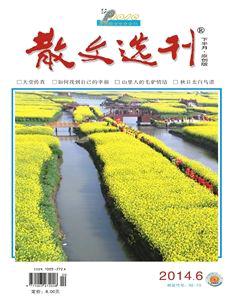水泉坪記憶
趙攀強

秦嶺南麓,漢江北部,有個令人難忘的地方,因為那里有我青春的足跡和銘心的記憶。
那是1987年冬季的某天,到村上已經是晚上,什么也看不見了,只記得從山下走到山上用了好長好長的時間,山勢陡峭,行走艱難。
在村干部家吃了晚飯,然后坐下來聊天。他們介紹說,村里有一條神水,有一口神泉,還有一片神坪,千百年來人們都把這個地方叫水泉坪。
天還沒亮,我就起床了,因為我根本就睡不著,我被這個地方的神奇故事吸引了,有點興奮,迫不及待想去看個究竟。
我們先來到那口神泉,只見那株千年銀杏樹下有口不大不小的水泉,泉中清水翻滾,霧氣騰騰。我舀起一瓢泉水洗臉,溫熱適度,通身舒服,看來泉水“冬溫夏涼”的說法一點不假。
來到河邊,舉目四望,我被眼前的神奇景象驚呆了,我還從來沒有見過這么美妙的地方,我覺得這里比陶淵明筆下的“世外桃源”美多了。
藍天白云下高高聳起兩座大山,千畝平原鑲嵌兩山之間,清清的水泉河在平原中間蜿蜒流淌,一字排列的石板房分布平原兩邊,美輪美奐,優哉妙哉!
如果這樣的景觀放在其他地方不足為奇,奇就奇在它地處海拔千米的高山,那條水泉河流過山巔八里平原后,沖出谷口,飛落山下,形成巨大瀑布,氣勢恢宏,聲震百里,蔚為壯觀。
當地人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古時旬陽縣城選址,看中了水泉坪這塊寶地,破土動工那天,掘地三尺,泉水奔涌,水中竟然跑出一只羊來,人們尋羊到現今的旬陽縣城的龔家梁,不見了羊,便開挖尋找,發現那里的土質比水泉坪的土質重三錢,于是就將縣城建在龔家梁,定名為“尋羊城”,后譯音為“旬陽城”。這個民間傳說的真假無可考證,但人們對水泉坪的贊美卻是眼見的現實。
住在水泉坪的人都有一種自豪感,他們對我談起它,總是笑容滿面,神采飛揚。可不是么,在這座高高的王莽山上,山坡有千畝毛栗,山谷有千畝稻田,田間有小橋流水,田邊有百戶石板房,房前屋后有百株銀杏樹,還有那千年神泉的故事和王莽追劉秀的傳說,件件都是寶啊!
可是,水泉坪人也有揪心的事情,村干部對我說,雖然他們身居寶地,但百姓日子過得很苦,脫不了窮根呀!我不解地問,千畝稻田土地肥沃,糧食總該夠吃吧?村干部說,糧食產量低,還要賣糧變錢,不夠吃。我又問,毛栗能賣錢,錢該夠用吧?村干部說,毛栗個兒小結得又少,能賣幾個錢?不夠用。我走訪了不少農戶,情況和村干部說得差不多,百姓很窮!
回到區上,水泉坪的影子老在眼前晃來晃去,揮之不去。一邊是風景如畫的“美”,一邊是生活艱難的“窮”,形成明顯的反差。
這天晚上,我來到區林特站。我是安康農校畢業的,當年七月剛剛分配到小河區委任青年干部,同時分配到小河林特站的同學有小曹等,站上其他同志,不是師哥就是師姐,平時關系融洽,無話不談。聽了我提出要在水泉坪村改良野生毛栗,抓嫁接板栗試點的想法后,他們很贊同。
我又向區委書記作了匯報,書記表示支持。1988年春天驚蟄前夕,我和林特站技術員小曹來到水泉坪村,對農民進行嫁接板栗技術培訓,然后進山在野生毛栗樹上嫁接板栗。晚上休息了,群眾紛紛前來詢問各種問題,熱情很高。
完成這件工作,我很高興,覺得為群眾做了一件事情,頗有成就感。
有天晚上,我來到區農技站,站上同志基本上都是同學或者校友。我詢問提高水稻產量的方法,他們說推廣“兩段育秧”高產穩產,我建議他們到水泉坪進行試點。這年育秧季節,我陪農技站同志來到水泉坪推廣“兩段育秧”新技術,進展順利,當年水稻產量大幅度提高,群眾得到了實惠。
農技站的同志在水泉坪推廣水稻“兩段育秧”試點成功后,看上了這塊寶地,覺得這是一塊絕佳的農業試驗基地。他們積極爭取陜西省農業部門將水泉坪列為“秦油二號”油菜制種基地,為當地農民找到了一條新的致富門路。
隨著產業升級,群眾生活改善了,但交通問題成了制約水泉坪村經濟發展的瓶頸。當時區委宣傳干部是個老同志,叫鄧應祥,家就住在水泉坪村,馬上就要退休了。那天我找到他,談了很多水泉坪村的情況,老鄧也有決心回村發揮余熱。
記得那是1989年的事情,老鄧從區委退休后竟然又挑起了水泉坪村黨支部書記的擔子。聽說他回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組織群眾修路,我很激動,打心底里敬佩他。為了表示對老人家的支持,我再次來到水泉坪村,幫他組織勞力,監督工程。這時村上的風景更美了,山上綠綠蔥蔥,山下遍地金黃,那是春天油菜花開的芬芳,那是秋天稻谷飄香的波浪。
時隔若干年后,我又到水泉坪村,這時鄉村兩級正在該村實施新農村建設,著力打造中國最美鄉村,水泉坪越來越成為當地的一張名片了。繞村一圈之后,心中頓生一種怪怪的感覺,思來想去,原來是兩處景點變了樣子:那處飛流直下、震耳欲聾的瀑布沒有了,聽說村上修路時將谷口的那斷絕崖炸毀了,巖石填進深壑,水流自然失去了往日的氣勢;還有那條美麗的水泉河上一下子增添了五六座小橋,聽說他們為了打造小橋流水人家而特意建造的,反而失去了昔日只有谷口和中間兩座小橋時那種自然清幽的意境了。
我對隨行的干部說,新農村建設一定要保留那些石板房,如果再把那些老房子拆掉了,水泉坪的風景也就破壞了,其神秘感也就消失了。
前兩年,我又到了水泉坪,看見家家都在翻蓋新房,那些石板房拆得差不多了。我悵然若失,不知說什么好,心情無論如何都高興不起來。
我走到一處正在翻蓋新房的農民跟前說,石板房拆了實在可惜。那人回答說,現在有錢了,住舊房子太土氣了,外邊都在蓋樓房,我們不蓋差距太大了。我對干部說,石板房確實不應該拆除。干部回答說,這個村是新農村建設布點村,舊的不拆,新的沒地方建呀!
現在人們都在跟形勢,講發展,談變化,我看有些東西可以變,有些東西就不能變,如果硬要把它改變了,特色就退色了,傳統就沒有了,文化也就消失了,價值也就貶值了。
責任編輯:黃艷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