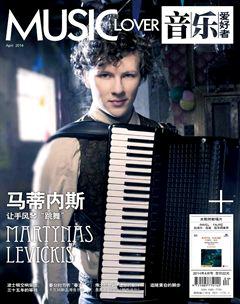三十五年間的因緣
人生的一大有趣之處是因果難辨。不知是哪里栽下的因就結成了之后的果,而結成的果又催生出新的因緣。
1979年,當波士頓交響樂團在上海交響樂團的排練廳里與上海的樂手一起排練時,有一個十二歲的小男孩偷偷地站在排練廳外聽著他們的排練。這個小男孩,在十年后成為了波士頓交響樂團里的第一位華人小提琴手,并且跟小澤征爾同臺演出了十三年。這位小男孩名叫黃思敬。
黃思敬的父母都是當年上海交響樂團的樂手。那年十二歲的他,和父母一起住在上海交響樂團的宿舍里。“十二歲是已經可以記事的年齡,我清晰地記得當時的情景。那時上海交響樂團的排練廳很小,沒有觀眾席,我就站在外面聽。”一年后,黃思敬跟隨父母移民美國,1989年在朱利亞音樂學校畢業后考入了波士頓交響樂團。
作為美國最有傳統的五大交響樂團之一,波士頓交響樂團無疑是黃思敬心目中的最佳歸屬。“我對樂團是很有感情了。在美國的幾大交響樂團中,波士頓交響樂團有著悠久的歷史,特別是樂團夏季的坦格爾伍德音樂節讓我覺得能在這樣的樂團工作是我的好運氣。夏天的坦格伍爾德是室外的音樂圣地,大大的草坪,環境優美。所有大樂團都能夠在音樂廳演奏,但像坦格爾伍德這樣的地方實在是太少了。”黃思敬對于坦格爾伍德的鐘情也源于他剛到樂團的經歷:“我來到波士頓交響樂團的第一個音樂季正是伯恩斯坦的最后一場音樂會,就是在坦格爾伍德演出。當時他的身體狀況已經不太好,但指揮的貝多芬《第七交響曲》至今仍讓我印象深刻。”
除了坦格爾伍德音樂節以外,樂團還有在波士頓交響樂團音樂廳以及波士頓大眾樂團的演出,一年的音樂會超過一百八十場,平均每周四場,有時一天需要演奏兩場。這樣緊湊的節奏,再加上自己室內樂團的音樂會,這二十五年間,黃思敬沒有回過中國。而這次,他會帶著自己的父母一起回到久違的故鄉。
樂團里的另一位中國樂手周黎的父母也是1979年波士頓交響樂團中國之行的見證人和參與者。同在中央樂團交響樂隊的他們親歷了與小澤征爾一起的排練和音樂會。周黎的父親是樂團的長笛手,母親則是豎琴首席。受到母親的影響,周黎九歲便跟隨媽媽的老師在中央音樂學院附中學習豎琴,直到十三歲移民美國。
如今已獲得不少國際豎琴比賽大獎并在2009年成為波士頓交響樂團豎琴首席的周黎,也走過一段漫長的音樂求學之路。從寄宿制藝術高中甄特洛根藝術學院到朱利亞音樂學校,從畢業后先在紐約城市歌劇院團擔任豎琴首席五年,再到通過重重考試進入波士頓交響樂團,周黎說自己很幸運,因為一路以來都遇到了不少好老師。其中,朱利亞音樂學校的南希·艾倫(Nancy Allen)老師對她影響深遠。“南希老師謙遜的為人和因材施教的教育方式都對我和我自己的教學工作影響很大,特別是我還在讀書時她就給我創造了許多與紐約愛樂樂團演奏的機會,讓我學到了許多琴房里學不到的知識,積累了很多舞臺經驗。”不過,雖然有多年的專業學習和舞臺演奏經驗,周黎考入波士頓交響樂團也并不輕松。
在業界,波士頓交響樂團的甄選是出了名的難。樂手一般需要先寄自己的演奏樣本,通過第一輪海選后是至少三輪的公開考試。由于每個樂團只需要一名豎琴演奏者,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在通過了三輪的公開考試后,周黎與樂團一起試奏了兩周,最后還單獨演奏給當時的樂團音樂總監萊文聽,經過如此殘酷的層層選拔,周黎才最終進入了樂團。在她之前,樂團有整整一百二十五年沒有招考過豎琴。“我之前的豎琴首席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就在樂團了。1979年跟隨樂團到中國巡演時,她是第二豎琴,待當時的首席退休后,她就直接成為了首席,并沒有經過如今這般的甄選。”
有過和不少其他樂團合作經歷的周黎說波士頓交響樂團最吸引她的是“和諧”。“有的樂團喜歡突出首席,而波士頓交響樂團的演奏是一個和諧的整體,大家都會聽彼此的演奏。而且,這種和諧不僅體現在音樂演奏上,樂團成員的關系也是如此。我剛剛生了寶寶,大家都非常關心我。”
對于黃思敬和周黎而言,樂團已然成為他們的另一個家。樂團制度穩定,運營規范,又擁有自己的音樂廳。此外,由于樂手一旦通過甄選,并順利通過第一年的試用期后就能和樂團簽訂終身制的合同,這種種因素加起來使樂團團員的更換率非常低。大家常常都是幾十年在一起演奏,關系就像親人一般。
雖然如此,樂團的生活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樂團每年都會和不同的指揮、獨奏家一起合作,也委約過不少新作品。大眾樂團和坦格爾伍德的演出也與音樂廳的樂季不同,所有這些都時時帶給他們挑戰,也促進他們在演出技術上的不斷成長。
有很多親戚在中國的周黎每年都會回國,不過跟樂團一起回去還是第一次。“如今,雖然有很多國外的樂團都已經到過中國,但波士頓交響樂團是隔了三十五年才重新踏上這片土地。這對于樂團是件重大的事情,我個人也非常激動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