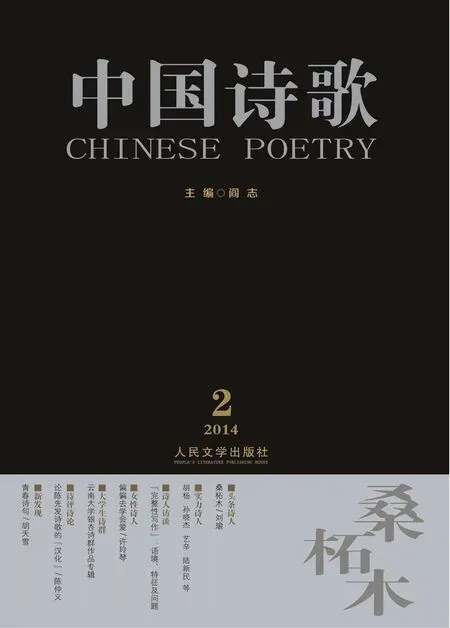痖弦詩選
2014-06-19 03:27:30痖弦
中國詩歌
2014年2期
痖弦詩選

上校
那純粹是另一種玫瑰
自火焰中誕生
在蕎麥田里他們遇見最大的會戰
而他的一條腿訣別于一九四三年
他曾經聽到過歷史和笑
甚么是不朽呢
咳嗽藥刮臉刀上月房租如此等等
而在妻的縫紉機的零星戰斗下
他覺得惟一能俘虜他的
便是太陽
紅玉米
宣統那年的風吹著
吹著那串紅玉米
它就在屋檐下
掛著
好像整個北方
整個北方的憂郁
都掛在那兒
猶似一些逃學的下午
雪使私塾先生的戒尺冷了
表姊的驢兒就拴在桑樹下面
猶似嗩吶吹起
道士們喃喃著
祖父的亡靈到京城去還沒有回來
猶似叫哥哥的葫蘆兒藏在棉袍里
一點點凄涼,一點點溫暖
以及銅環滾過崗子
遙見外婆家的蕎麥田
便哭了
就是那種紅玉米
掛著,久久地
在屋檐底下
宣統那年的風吹著
你們永不懂得
那樣的紅玉米
它掛在那兒的姿態
和它的顏色
我底南方出生的女兒也不懂得
凡爾哈侖也不懂得
猶似現在
我已老邁
在記憶的屋檐下
紅玉米掛著
一九五八年的風吹著
紅玉米掛著
坤伶
十六歲她的名字便流落在城里
一種凄然的旋律
那杏仁色的雙臂應由宦官來守衛
小小的髻兒啊清朝人為它心碎
是玉堂春吧
(夜夜滿園子嗑瓜子兒的臉!)
“苦啊……”
雙手放在枷里的她
有人說
在佳木斯曾跟一個白俄軍官混過
一種凄然的旋律
每個婦人詛咒她在每個城里
C教授
到六月他的白色硬領仍將繼續支撐他底古典
每個早晨,以大戰前的姿態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