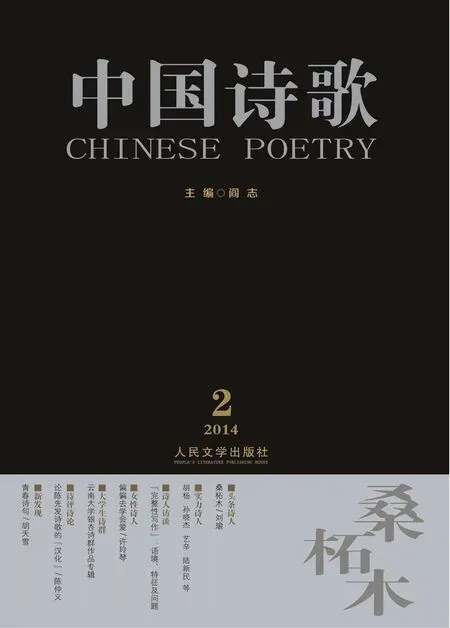詩學觀點
□王婉/輯
詩學觀點
□王婉/輯
●江非認為在洛盞的大部分詩作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正是這樣的一種“思”,才讓他獲得了一個對自我的辨認和承認的安慰與確定性。自我是一種運動之中的沒有完結的生成,洛盞再用他的“思”在他的詩歌書寫里尋求它的根源。這個根源,在詩人洛盞看來,似乎首先就在于詞語之中,在詞語內部的那種意義的間距和潛在之中,或者說,是在詞語—語言—意義—觀念的這種內部間距演變和改寫,所映指的一種歷史“間性”之中。洛盞在借用詩的書寫尋找自我和那個大寫的“我”的過程中,首先去做的工作就是要釋放這個詞語內部的潛在,讓它變得清晰起來,而這種“讓清晰”的工作,對于洛盞來說,似乎就是他本人對自己以及對“在我一側”的事物的澄明與看見。他想實現一種相對的看,這個“看”從我出發,經由詞語而到達那個被看之物,之后再通過被看之物重新嵌入詞語,從而讓詞語回到當下和對于自我的理解之中。所以,洛盞所寫下的大部分詩作,似乎都是一種名詞解釋,而他無意中給自己確立的個人詩歌書寫的近期趨向,似乎就是一項關于詞典編纂的工作。
(《洛盞的詞典詩學》,《詩刊》2013年10月下半月刊)
●詩人湯養宗認為在這個時代里,如果不是恰好是我們來到,別人也會來到。如果不是我們要這樣呈現,別人也會去以另一種方式呈現。這其實都不是最重要的,要緊的是,詩歌在這個時代里它的內部產生了什么新的變化。這個時代一切精神的指向,是屬于真正重建起來的那部分。它使詩歌在某一時間的斷層里,已區分了其他任何一個時代的文字表達方式。新的詩歌敘述力量已為它做出了什么。我們在這個時代里真正只做了所謂有用的這一點點事。我們似乎再不能為詩歌做一點別的什么。其余的使命,對于詩歌,我們真的是已來得太早又來得太遲。
我們為什么要生活在這個時代也許并沒有什么依據,但是,我們又恰好與它相遇。作為詩人,這是我們的榮幸,也是我們命中注定的對重新打開詩歌的挑戰。
(《所謂當代,其實是恰好被我們偶然相遇》,《詩潮》2013年第11期)
●朱金晨認為丁及是詩壇上一位有著自己特色的詩人,他的處事方式是平靜如水,他的詩歌創作追求也是從容如水,幾乎每一行里都能擰出清清的甜甜的江南水鄉的水,讓人貪婪地聞著那漸行漸遠的十分難得的江南味道與水鄉氣息。
無論是《簫聲》七首,或是《風中》八首,還是《清淺的腳步》九首,字里行間承繼著他一貫崇尚的藝術風格,淡淡的筆墨,淡淡的情緒,襯托出一重重淡淡的境界。盡管寫的也是竹籬花墻,也是阡陌村井,也是碧水中一座古色古香的戲臺,但細細讀下去,就別有一番妙不可言的風味了。別人縱然寫過這樣的題材這樣的內容,但絕無丁及這樣的感覺這樣的韻味。難怪會有詩評家如此評論他:丁及的詩作,幾乎每一首都是一幅抒情的蘇州水墨畫,江南水墨畫。能在詩行中給受眾這樣的藝術享受,這自然源于丁及對詩歌創作的追求與認識。他從不跟風那種花哨的、時髦的、變異的創作手法,厭惡寫詩像教師爺一樣令人眼花繚亂地耍弄刀槍,認為那只是唬人的玩藝而已,沒有實在的藝術內容。他覺得無論是前衛的,還是傳統的,詩的本質永遠不會變,離不開詩人恪守的藝術情操,以及出自內心的真情,尤其是后者,以情動人,以情感人,那是詩的真諦。
(《丁及其人其詩》,《詩歌月刊》2013年第10期)
由此見出,詩歌與現實之間的古老敵意進入了它新的化身:面對被敗壞的大地上的種種語言瘟疫,詩歌要重新命名我們所遭遇的事物,發明心靈與事物之間的親密性,并將之轉換為詞語之光的優雅和溫暖。
(《化解與對立——試談當代漢語新詩中的矛盾修辭》,《山花》2013年第10期)
●啞石認為語言當然是聲音組織的物質形態。詩人的耳朵,不僅僅應該傾聽到其中傳統意義下“俄耳甫斯式”的彈撥吟唱,也要考慮將聽覺神經的震顫,租賃給語言的當代困境——漢語新詩使用的語言,不像當代英語、法語那般充分吸收了現代文明,從而有一個基本“穩定”的面貌。在寫作中,現代漢語不得不處于一種開放、混雜的狀態,其特殊困難和新的可能,同樣醒目而灼人——對此有著具體警覺的當下新詩寫作者,并不是多數。對聲音的天賦是一回事,是否能夠自覺地將這天賦敞向當代語言經驗和文明,是另一回事;再則,詩人能否哪怕局部有效地為漢語當代經驗的形塑,貢獻出點滴華彩,又是另一回事。張爾的作品,顯示出對此的相當自覺(不管他的思考路徑,是否和上述理解重疊)。一方面,他努力調動天賦來傾聽、重塑當代事物的語言形象,這會讓某些慣于在傳統、衛生的意識積習中打發光景的人不適應;另一方面,他也明顯警醒于要努力防止自己在無可旁借、斧正的“忙乎”中,滑入粗暴、簡單和廉價的放縱。
(《拒絕流俗的新詩寫作》,《特區文學》2013年第5期)
●傅浩認為客體主義對美國詩歌產生了極深遠的影響,其后效仿者層出不窮。當然,追根溯源,應當祖述意象主義。如果說,龐德是美國現代詩的點火播種者,那么,威廉斯則是使其發揚光大者和承先啟后的中間。威廉斯與其他意象主義者不同,除了有自己的想法之外,似乎更能領會龐德的意旨。可以不夸張地說,他畢生都一直與龐德競爭并在競爭之中發展和修正著自己的詩學。龐德所謂的意象蘊涵情與思,相當于新鮮的暗喻或個人象征,尚與中古以來的文學傳統糾纏不清。威廉斯則似更進一步,與傳統決裂得更徹底,或者說,回溯到更遠的源頭去了,主要寫從日常經驗中提煉素材的“生活詩”。
(《事物之外別無理念——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詩學理念》,《世界文學》2013年第5期)
●詩人朱春生認為好的詩歌,首先是一種純粹。純粹的感情,純粹的意蘊,純粹的思想。當然,所謂的純粹,并不是很單純地為了寫詩而寫詩,畢竟詩歌是如今四大文體之一,它也和小說、戲劇、散文一樣,需要自身的寫作技巧,甚至詩的寫作技巧與小說、戲劇、散文都是相通的。如果有人可以游刃有余地在這四種文體中行走,我相信他寫出來的詩會比一般詩人的詩更勝一籌。
其次,詩歌是一種自言自語的筆畫。詩歌最基本的因素就是感情,而每一個人都具有充沛的感情,從這個角度分析,所有的人都可以成為詩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為詩人,感情的呈現還需要一種表述技巧。
第三,詩歌是使人們向外界表述自己內心的一個媒介。詩人們寫出了詩歌,其目的在于表露自己的內心世界。一首好詩,總會引起很多人的共鳴,一首好詩,總會使讀者了解詩人的現狀。但是,這個媒介總會給讀者一個想象的空間,從繪畫的角度分析,這就是留白。不同的人會涌現不同的情感。
(《2013:河北省青年詩觀》,《詩選刊》2013年第10期)
●洪燭認為倉央嘉措是一個未被詩歌史記載的詩人,可他的情詩比許多進入詩歌史的詩人有更廣泛的影響。倉央嘉措是一個不知道自己是詩人的詩人,他寫詩純粹為了抒情,抒個人之私情,并未當做文學創作,可他比許多胸懷大任的詩人,獲得了更多領域的讀者的認同。倉央嘉措是活佛,他寫詩頂多屬于業余寫作,卻比所謂專業的詩人更接近詩的真諦。我刻意把倉央嘉措稱為詩人,是為了證明:他這樣的,才是詩的原教旨主義者。他寫的那些極原始的詩,更像是詩的雛形,可在這個無比先進的時代,仍比許多現代派或后現代的詩更能打動普通讀者。也許,詩變了,每個年代的詩都在突飛猛進,可讀者沒變,讀者的心靈一點沒變,只會為最簡單的愛與美而感動。最簡單的愛與美其實又是最本質的愛與美。現代詩把讀者遠遠甩到后面了,造成了詩與讀者的脫節,不過沒關系,倉央嘉措以及許多古典的詩歌,仍然在收容走得慢的讀者,使他們感受到詩意的存在。
(《倉央嘉措:詩人就是超人》,《星星》詩歌原創版2013年10月上旬刊)
●耿占春在談到駱英的組詩《水·魅》時認為,《水·魅》既可以視為五十八首相互獨立的詩篇的組合,也可以視為對同一首詩歌同一種主題不斷深入的重寫,或許,更像是對一種不斷被推延的信念的緩慢辨認,逐漸呈現出一種思想的旅程,在沒有概念的表象世界中,它們共同指向一種困難的確認。世界的表象與個人生活乃至社會進程重新相遇。詩人最終說出了這一心中的秘密,“我承認我是以一種嫉妒和癡醉的心情在此刻想起了種種生死離別”。人們在這個時代這個社會加以否定的生活,詩人在他自己先前的詩作中也曾經加以嘲諷的生活,最終得到了肯定,而且是如泣如訴的充滿“嫉妒”與“癡醉”的肯定。歸根結蒂,只有走向不斷消亡的事物并肯定著這一進程的生命——而不是沒有變化的石頭——才算是活著。
(《為微物之神而歌——讀駱英〈水·魅〉》,《揚子江》2013年第6期)
●孫民樂認為撇開歷史上權力話語與詩學政治對詩歌史記憶的明顯的有意識操控與涂抹,以“史觀優先”和強烈的“意義”索取意識為特征的現代文學史編纂模式也同樣加劇了新詩史的“危機”。即使是那些相對保持了“客觀”、“中立”立場的詩歌史寫作,同樣無法避免某種特定的歷史“眼光”對詩歌史對象的無情過濾,能夠進入其視野的只能是極為有限的詩歌史對象。這些對象之所以會被“挑選”出來,與其說是出于客觀公正,倒不如說是因為它們更適合于被納入某種以特定的歷史想象為基礎的“情節編纂模式”。因而,那些最終被遴選出來作為詩歌史“中堅”或“偉大的傳統”擔荷者的詩歌實踐,也總是如旁若無人的“極地突進”,失掉了其廣泛的歷史關聯,進而也難于維持其穩定的信譽。
(《“不屈不撓的博學”——評劉福春《中國新詩編年史》》,《現代中文學刊》2013年第5期)
●張江認為詩是以語言為材料的藝術品。沒有語言,詩人就無法思維和表達。他所采用的語言,必須取自于群眾整體創造和參與、被廣泛使用的交流符號系統,參照的是一套約定俗成、共同遵守的語法規則體系。詩歌的語言離不開大眾創造和使用的語言。由語言結織而成的詩歌文本,滲透著大眾的語言經驗和文化沉淀。
詩歌語言的進步,以大眾語言的發展為基礎。生產、生活與交往的需要,促使大眾不斷創造新鮮、活潑的語言。語言攜帶的意義和信息,也在大眾的使用中不斷地流轉和豐實。詩人把這種動態性反映在詩歌中,不斷改變著詩歌的語言面貌。大眾生生不息的語言活力,讓詩歌的語言繁茂而新鮮。
(《當代詩歌的斷裂與成長:從“誦讀”到“視讀”》,《文藝研究》2013年第10期)
●李犁認為詩歌就是技術,詩歌的每一次進步都是技術的進步。好的詩歌首先是技術的成功,詩貴出新就是這個道理。有些詩歌看似平淡樸實沒有技術,其實是技術已化成了詩人的素質,高到無痕了。這顯然也是趙明舒努力的方向和目標,具體說就是真實樸素簡單直接。這八個字是形式,也是內容,更是詩人自己的胸襟和品格。但是怎么把這八個字具體地呈現出來,趙明舒除了前面說過的把詩歌情節化,弄出一個出人意料的直搗本質的結尾等方法外,還有個基本原則就是新奇巧。新奇巧看似陳舊,其實它是所有好詩歌共有的品行,也是所有優秀藝術共享的絕技。新奇巧也是趙明舒有意或無意中在應用和要抵達的方法與目的。這種新奇巧貫穿在趙明舒所有的詩歌中,它成為了趙明舒寫作的一種習慣一種趨向甚至潛意識。
(《趙明舒:在小品的嬉笑中乍現鋒芒》,《海燕》201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