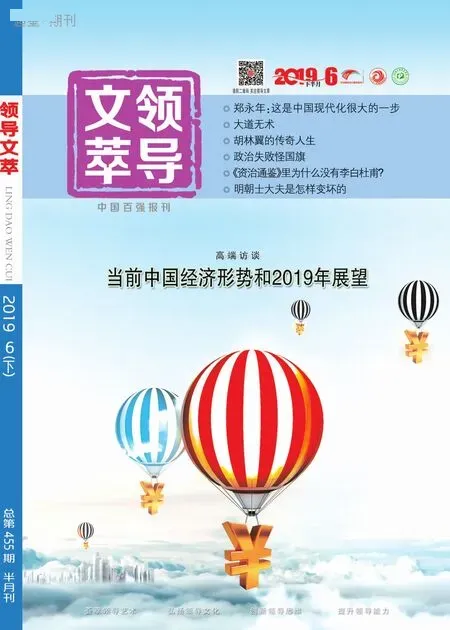解讀“中國夢”的美國視角
□孫浩
中國究竟什么樣?該怎么和中國人做生意?中國經濟奇跡是怎么一回事,可持續嗎?中國實力會超越美國嗎?這些都是在美國常見的“中國疑問”。如今,討論間又多了一個新話題——“中國夢”。
自去年年底以來,“中國夢”成了美國媒體和各界人士展望和評判中國變化的一個新的切入點。這體現出美國對中國的關注不再局限于國務層面或重大事件,也在向社會各個層面拓展,而這種趨勢,亦折射出美國社會對大洋彼岸這個古老又年輕、與自己面貌迥然的國度的興趣日漸濃厚,而且,支撐這份興趣的需求日益旺盛。
新的“國民身份”
中共十八大召開以及中國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亮相前夕,美國評論員托馬斯·弗里德曼于2012年10月曾在《紐約時報》上專門撰文,題目恰恰是《中國需要自己的夢》。
他在文中說,外界確定的是,習近平將成為中國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外界還不清楚的是,習近平會擁有一個怎樣的“中國夢”——而這或許才是最重要的。
他引述麻省理工學院華裔畢業生、麥肯錫公司前咨詢人士的話說,中國現在渴望創造一種新的“國民身份”,既能融入傳統的中式價值觀,也能適應現代都市的語境,而創造一個可持續、有效平衡發展、滿足環保需求的“中國夢”,是這種新身份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可以在世界范圍內引起共鳴。
弗里德曼強調說,中國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面臨著兩大艱巨挑戰:一是如何繼續保持高增長率,二是如何解決快速增長所帶來的問題,包括縮小貧富差距、解決好農民工問題、治理污染等。而將兩者結合在一起的途徑,就是真正帶來一個“中國夢”。
社會進步的訊號
習近平主席與奧巴馬總統舉行加州會晤期間及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在美舉行期間,美國媒體上集中出現對“中國夢”的報道和討論。
“習奧會”前夕,《紐約時報》于當年6月2日發表了國際投資銀行家羅伯特·勞倫斯·庫恩的評論文章。他提到,中國政府就“中國夢”給出的核心定義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體解讀為“兩個百年目標”,內涵涉及富強中國、文明中國、和諧中國和美麗中國四部分。文章還盡量用美國讀者容易理解的方式,解釋了上述內容中有關中等發達國家、現代化等概念。
其實,美國媒體一直對中國的腐敗問題、污染問題、法治問題等頗為關注,這一特點也延續到了對“中國夢”的報道中。
6月2日,《華盛頓郵報》發表了該報社論版編輯弗雷德·希亞特的評論文章《習近平的“中國夢”是否包括法治?》。文章先是問道,習近平所提出的“中國夢”的落腳點到底是繼續推進改革開放、打造中產階級社會,還是打擊腐敗、減小貧富差距,抑或致力于在國際舞臺上拓展中國影響力、提升中國話語權?隨后回答,應該是三者兼顧。
也有一些美國主流媒體結合中國與鄰國的領土爭端等國際熱點,將“中國夢”簡單地與中國國內的民族主義思潮聯系起來。究其原因,恐怕很大一部分是為了在標題和內容上吸引眼球。
盡管文化和制度等差異導致一些美國媒體不可避免地戴著“有色眼鏡”看待“中國夢”,但一些對中國有更深入了解的人還是捕捉到了“中國夢”所帶來的社會進步的訊號。
7月中旬,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特別系列節目《中國進行時》(On China)專門制作了一期訪談節目,片名就是《中國夢》。這檔節目請來了中國資深外交官吳建民、《紐約客》雜志駐中國記者歐逸文和摩根大通中國區全球市場主席李晶等人一起探討這個話題。
歐逸文說,中國人關心的已不僅僅是自己皮夾子的薄厚,對于高質量生活的定義變得更豐富了。比如,他們會說,“我希望自己生活在一個空氣清潔的城市。”他們會說,希望自己在遇到官司時能得到公平裁決。
吳建民回應說,民主和法治本來就是中國改革的目標之一,中國新一屆領導集體對這個立場的表述非常清晰,只不過這個過程是漸進的,必須一步步來。
李晶提到,過去二十年間中國已經有很多人先富起來并創造了巨大個人財富,中國政府希望今后能構建更平等的社會,提高最低收入階層的生活水平,而不是突出精英階層。
“中國夢”與“美國夢”
“美國夢”普遍為人接受的內涵,是對財富和成功的追求。而美國媒體和學界在討論“中國夢”的同時,也很難不把它與“美國夢”聯系起來。
評論員托馬斯·弗里德曼預言,中國中產階級的規模將從目前的3億人迅速擴大至2025年的8億人,這一群體對生活的需求將和“美國夢”的內容差不多,重點在于追求更高的生活質量。
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資深研究員李成認為,“中國夢”的實踐過程無疑也將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也會不斷遭遇新現實的挑戰。以“美國夢”為參照,美國民主制度也有自身的問題,也有其嚴重的國內矛盾,所以“美國夢”至今也是不斷爭取的過程。
他特別指出,中國將在未來15年到20年真正步入中產階級社會,“中國夢”從內容到外延可以與這一發展趨勢合拍,以產生最大凝聚力。此外,在中國社會日益多元化的現實下,“中國夢”從實踐和宣傳角度都可以填充更全面、更明確、更具象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