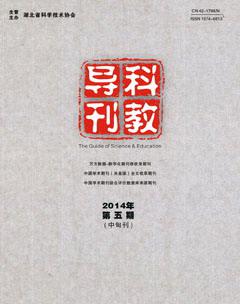重構《圣經》中的女性形象
陳玉偉
摘 要 《圣經》作為父權制的文化產物,其中的女性一直被塑造為邊緣化和被詛咒的形象,以此來維護男權的社會地位。本文試圖借助于福柯的權力話語理論來分析處于邊緣地位的夏娃的形象,來探析夏娃邊緣話語的真正原因,并在此基礎上重塑一個新型的夏娃形象——人類智慧的勇敢追求者。
關鍵詞 《圣經》 福柯 權力話語理論 夏娃 重塑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Reconstruction of the Female Image in "Bible"
——Human Wisdom Brave Suitors - Eve
CHEN Yuwei
(Chengdu Institute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1844)
Abstract "Bible" as a cultural product of patriarchy, where women have been portrayed as marginalized and cursed image,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social status of male power.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id the power to analyze Foucault's discourse theory marginalized Eve's image, the real reason to Probe Eve edge of discourse, and reshape the image of a new Eve on the basis of human intelligence --- brave suitors.
Key words "Bible"; Foucault; power discourse theory; Eve; reconstruction
0 引言
《圣經》是父權制的產物,男性作者以《圣經》為傳聲筒,向讀者展示了一個男權社會,以及在男權社會下被邊緣化的女性形象。女性,作為《圣經》中極小部分的人物形象(約占有5%),①一直處于“失語”的狀態。夏娃,作為人類始祖之一,也同樣在《圣經》中幾乎沒有話語權。福柯在他的話語理論中提出“話語本身既是權力的產物,也是權力的組成部分。權力的施展,一方面不斷創造新的話語;另一方面這些新的話語也會導致、加固某種權力,或者削弱、對抗這種權力。”②這也就意味著權力可以賦予話語主導地位,反之,無權力則導致失語或者邊緣話語。在父權制下,男性為了保證自己的話語權,就要借助于自身的權力和話語對弱勢的女性話語和身體進行壓制和馴服。而《圣經》就是男性進行話語權壓制的工具之一。本文試圖以夏娃為分析對象,根據福柯的話語理論分析她在《圣經》中處于邊緣話語的真正原因,并在此基礎上重新解讀《圣經》中的夏娃形象,塑造一個為了人類的智慧而努力追求的勇敢女性形象。
1 邊緣話語下的夏娃
在《圣經》中,夏娃是一個處于邊緣化話語的人物。她的被創造,只是繼亞當后,上帝怕亞當“獨居不好”(創世紀 2:18),而為亞當創造的一個附屬品。據《舊約·圣經·創世紀》記載:“只是那人沒有遇見配偶幫助他。耶和華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條肋骨,又把肉合起來。耶和華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個女人……”(創世紀 2:20-1)女性的誕生只是作為男人的一個附屬品,而并不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她從屬于男人,服從于男人,而沒有自己的話語權。正如西蒙·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闡釋所講的女性只是相對于男人的“他者”。在男權社會下,“人就是指男性……女人只是相對于男人的不能自主的人。女人是附屬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對立的次要者。他是主體,是絕對的,而她是他者,被邊緣化的。”(波伏娃,1988,11)夏娃的出現,除了做亞當的幫手外,也是為了凸顯人類唯一的男性的統治地位。其次,夏娃作為偷食“禁果”的第一個人被認為是貪婪的、墮落的。經不起撒旦的誘惑,夏娃偷吃了“禁果”,并且也誘惑其男人—— 亞當吃了“禁果”。從此人類被趕出了伊甸園,開始了勞苦的工作。人們把一切的罪責都歸咎給夏娃,把她推向“罪惡”的淵源。而在這一場上帝的“審判”中,夏娃只做了一次回答,而且也不是為自己辯護。“那蛇引誘我,我就吃了。”(創世紀 3:13)根據福柯的話語理論,夏娃在這場辯論中,沒有任何話語上的主導優勢,即便有自己的話語,也只是在陳述一個客觀事實。總之,夏娃在《圣經》中幾乎是處于失語狀態,她被限定為男人的附屬品,秩序的破壞者,人類“原罪”的始作俑者,但卻沒有為自己辯護的機會和權利。
2 勇敢追求智慧的夏娃
人類在偷食“禁果”之前,是不知善惡的。因為《圣經》中記載,“耶和華神吩咐他(亞當)說:‘園中各樣書上的果子,你可以隨便吃,只是分辨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死。(創世紀 2:16)”從這里可以看出,所謂的“禁果”是“分辨善惡的果子”。所以是夏娃帶領人類走出了最初的混沌狀態,而有了分辨善惡之能力。
首先,夏娃偷食“禁果”是為了尋求人類的智慧。在遇到撒旦之前,夏娃也看到善惡樹是賞心悅目的,但是她并不知道可以使人得到智慧。而當撒旦告訴她“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能如神能知道善惡”(創世紀 3:5)時,夏娃才起了偷食“禁果”之心。足以可見,她并不是因為貪婪于樹上果子的“悅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創世紀 3:6),而是因為好奇樹上果子“能使人有智慧”(創世紀 3:6),才最終偷食了“禁果”。
其次,夏娃在追求智慧的征程中,表現得異常勇敢。亞當一定向她傳達過上帝的命令,偷食善惡之樹的果子必死。然而為了尋求智慧,她置生死于不顧,果斷地吃了善惡之果,而且還讓自己的丈夫也吃了。正如撒旦所說,他們吃了善惡之果后,眼睛立刻亮了,而他們獲得的第一個智慧就是關于性,他們“才知自己是赤身露體,便拿無花果樹的葉子,為自己編作裙子”(創世紀 3:7)。那么從此人類就開始了探尋文明之旅。而在此之前,人類的生活無異于其他動物,吃飯、睡覺、勞作。正是人類獲得了智慧,才有別于其他的任何生物。所以說,是夏娃的勇敢,帶領人類走出蒙昧,走向智慧。
在尋求智慧的征途中,夏娃并沒有過多的語言,根據福柯的話語理論,夏娃是沒有掌控權力的主導優勢。這是因為在男權文化體制中,女性話語長期被壓制。《圣經》,作為男權社會的產物,在男性作家的筆下,夏娃是不可能掌控話語的主導權的,因為一旦給予女性足夠的話語權,女性必然會顛覆男權社會的統治地位。然而權力抑制的背后必然蘊含著顛覆性的反抗力量。夏娃在追求智慧的過程中,選擇無聲的語言和勇敢、反叛者的行為,不僅顛覆了她丈夫的權威,同時也挑戰了上帝的權威,獲取了和上帝一樣的分辨善惡的智慧。
3 結論
在希伯來文化中,女性是處于低下的社會地位。為了鞏固和加強自己的社會主導地位,男權社會又迫使她們失去了話語權。所以在《圣經》中,即便是人類的始祖——夏娃,也避免不了成為犧牲品,被詛咒的對象,讓女人自身也認為她們生而有“罪”卻無辯駁的機會。作為宗教的經典,《圣經》無時無刻不在維護著上帝的權威,維護著男權社會的主導地位。然而女性在人類文化的進程中,也無時無刻不在試圖掙脫枷鎖,努力尋求自我,改變自己的現狀。正如人類的始祖—— 夏娃一樣,即便在失語狀態下,在男權社會的枷鎖下,同樣為了尋求人類的智慧,而執著于勇敢的追求進程中,最終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獲取智慧的勇敢的女性。
注釋
① 李滟波.《舊約圣經》中女性形象的文化解讀.湘潭:湘潭大學學報,2004(3):56.
② 黃華.權力,身體與自我——福柯與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109.
參考文獻
[1] Barrett, Michele. The Politics of Truth: From Marx to Foucaul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2] 圣經.中英文和合本.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中國基督教協會出版.南京:南京愛德印刷有限公司,2010.6.
[3] 諾斯洛夫·弗萊著.偉大的代碼——圣經與文學.赫振益,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4] 西蒙·德·波伏娃著.第二性. 陶鐵柱,譯.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