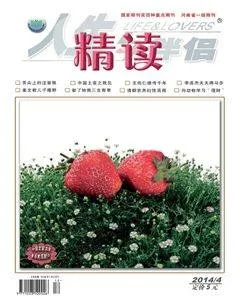李敖這個父親
2014-06-24 04:58:21李文
人生與伴侶·共同關注 2014年12期
關鍵詞:教育
我和爸爸相處的時間并不多。在我最需要他陪伴的時候,他卻深陷囹圄,無法為童年的我遮風避雨。爸爸曾在《坐牢家爸爸給女兒的八十封信》一書里寫道:“我對李文最大的虧欠是我一身的麻煩使她不能跟我住,不能很好地教育她。”
其實爸爸只是虧欠了我很多父女相依的日子,他從不虧欠對我的教育。記得小時候,爸爸每隔一周就會從監獄寄信給我,用這種特殊的方式教給我很多做人的道理。那是爸爸在當時情景下唯一可選擇的辦法,他把自己對女兒的牽掛凝聚在字里行間,筆鋒過處仿佛鏗鏘有聲,絲毫不見牢獄生涯的凄涼困苦。
爸爸用他一生的時間,以一己之力對抗傳統文化中的反動及不合理。有人形容他是戰神,我想并不為過,但很少有人能夠讀出爸爸慷慨激昂背后的辛酸無奈、沉痛悲涼。爸爸在這一過程中漸漸養成了對簿公堂的嗜好,他喜歡上了打官司。為什么喜歡打官司?因為有很多憤懣,很多不平,很多不公正的遭遇。
爸爸說,不認識我們的人喜歡看我們的文章,認識我們的人喜歡聽我們的講話,了解我們的人喜歡我們這個人,我們做人比我們講的話好,我們的講話比我們的文章好。光看我們的文章,一定會以為我們是窮兇極惡的家伙,可是聽了我們的講話,一定會覺得我們比我們的文章更可愛,等對我們有了更深一層的了解,他會發現我們又厲害又善良。別人是惡霸,我們是善霸。我們也是一霸,絕對不是窩囊沒用、被人欺負的濫好人。
爸爸在他過完74歲生日的時候,對我說感覺自己老了,頭腦不再像以前那樣靈活,有時候甚至會做錯事。他提到自己正在“逝去”,意思是他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離開人世,而他也已接受這個事實。爸爸讓我將“逝去”原文語錄找出來,在此呈現如下獻給爸爸:
老兵不死,只會慢慢凋零。
(摘自《跨世紀》)
猜你喜歡
華人時刊(2022年13期)2022-10-27 08:55:52
英語文摘(2022年8期)2022-09-02 01:59:30
當代陜西(2022年4期)2022-04-19 12:08:52
軟件導刊(2022年3期)2022-03-25 04:44:48
當代陜西(2021年15期)2021-10-14 08:24:24
贏未來(2020年1期)2021-01-07 00:52:26
人大建設(2020年1期)2020-07-27 02:47:08
當代陜西(2019年21期)2019-12-09 08:36:36
福建基礎教育研究(2019年9期)2019-05-28 01:34:27
商周刊(2018年25期)2019-01-08 03:3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