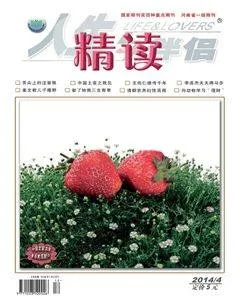我和蹦子司機(jī)
陳亞豪
7月中旬大學(xué)畢業(yè)后,我來到北京工作,單位離家不算近,先坐一個(gè)小時(shí)的地鐵,下了地鐵到單位還有將近5公里的距離。好在北京這一片有非常發(fā)達(dá)的三蹦子市場,北京俗稱蹦子,就是那種燒油的三輪車,經(jīng)常在路上和汽車飆,毫不示弱,還總是一蹦一蹦的,坐在里面總有種隨時(shí)翻車的刺激感。從地鐵口到公司10元錢,價(jià)錢合理,又能享受到飛起來的感覺。坐三蹦子就這樣成為我每天生活必不可少的一件樂事……
他讓我叫他小六,來北京打工3年,今年22歲,和我一樣大,但堅(jiān)持叫我大哥,不是因?yàn)槲矣写蟾绲姆叮凰f坐他車的都是大哥,請我不要再拒絕。我們的相識(shí)緣自我常坐他的蹦子,后來慢慢熟悉,從老顧客成為蹦友。每天清晨我走出地鐵口的時(shí)候他都會(huì)在路邊叼根“紅梅”等著我,這個(gè)時(shí)間點(diǎn)如果出現(xiàn)別的顧客他都會(huì)道歉謝絕,死心塌地地等我。小六是我所體驗(yàn)過的最優(yōu)秀的三蹦子駕駛員,他常用的招牌駕駛姿勢是下身蹺著二郎腿,就這樣炫酷的姿勢卻能把車騎得極穩(wěn),實(shí)在天賦異秉。
小六每天都會(huì)樂著給我講點(diǎn)生活趣事:昨天哪個(gè)競爭對(duì)手翻車了,前天哪個(gè)哥們一不留神撞到了城管,有他千里之外的家里事,還有他半年前得了怪病的小兒子。
我喜歡小六,因?yàn)樗偸莾裳鄄[成一條線,樂呵呵的。每天早上看到他,我都覺得陽光暖得可以融化掉北京的霧霾。
9月中旬的—個(gè)早晨,我繼續(xù)坐著小六的三蹦子藐視所有我們一路超過的汽車。那天小六沒要我的錢,他說他要回趟老家,估計(jì)月末才能回來,這段時(shí)間送不了我了,給我推薦了兩個(gè)同行好哥們,叫我以后坐他們的車并告訴我他們是這一帶排名第二和第三的三蹦子駕駛員。
第二天,小六的身影便沒有再出現(xiàn)在地鐵口。生活還要繼續(xù),我依然坐著三蹦子去公司。不過第一天沒有小六的日子,我乘坐的三蹦子就為了搶路和同樣目空一切的馬路霸主——公交車蹭上了,險(xiǎn)些側(cè)翻。
我很懷念小六。
總有一天你會(huì)明白,如果你遇見了—個(gè)優(yōu)秀的三蹦子駕駛員之后,其他蹦子都會(huì)變得不值一提。
一個(gè)星期后,小六提前回來了,在地鐵口看到他時(shí)我蹦蹦跳跳地就過去上了他的車。他依然眼睛瞇成一條細(xì)線,樂呵呵的,只是眼角的皺紋比走那天深了一些。我開心得不得了,過去乘蹦奔騰、策蹦馳騁的日子又回來了,我又可以在小六的蹦子上睥睨一切豪車了。小六的技術(shù)絲毫沒有退步,駕起車來反而更加迅猛,像一頭壓抑許久的野獸,在向這個(gè)世界怒吼著。
那天到公司的時(shí)間較已往早了幾分鐘,下車時(shí)我想起還一直沒問他之前突然回老家的原因,“六子,那會(huì)怎么突然說走就走了,家里沒出啥事吧?”“沒事大哥,兒子病情嚴(yán)重了,媳婦和我娘著急,讓我回去看看。”
“那他現(xiàn)在好些了吧?看你沒到月末就回來了。”
“死了,喘不上氣,眼看著死的,小臉都憋紫了。”
我一時(shí)怔住,嗓子里像卡進(jìn)了玻璃碎片,再也說不出任何話語,連唾液都忘了該如何吞咽。
“死就死了吧,這娃命苦,生下來就受這活罪,我沒出息,實(shí)在沒法治好他,早點(diǎn)投胎去個(gè)好人家,千萬別再給我當(dāng)兒子。”
沒有悲憤,沒有凄涼,甚至連情緒的變化都沒有,小六就這樣平靜地講述著一個(gè)好像與他毫無關(guān)系的孩童的死去。
可他眼角下那在一周里好像被錐子鑿刻了的皺紋,沒能藏住他內(nèi)心的悲痛。
秋日清晨的暖陽照射到小六的臉上,他的眼睛又重新瞇了起來,嘴角再次咧出弧度,“大哥,你快去上班吧,我回去趴活了,明兒見。”
- 人生與伴侶·共同關(guān)注的其它文章
- 逃跑有時(shí)是一種勝利
- 想飛的夢想是塊金
- 只做自己懂的事
- 見我心
- 指責(zé)別人先反省自己
- 糧食的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