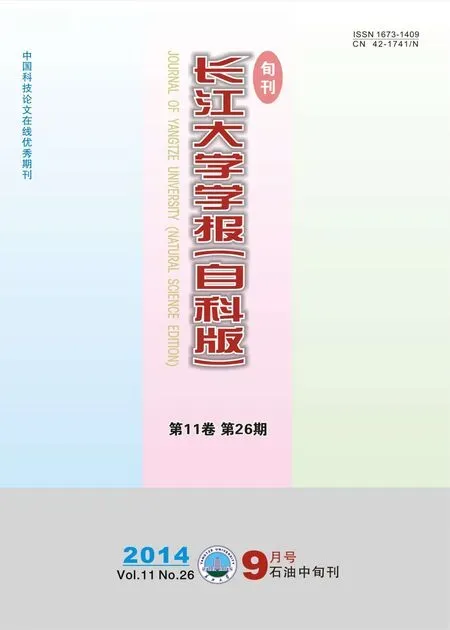古-中生代生物滅絕與華南早三疊世錯時相沉積研究
何冰輝 (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地球科學與資源學院,北京 100083)
常藍天 (山西潞安環保能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五陽煤礦,山西長治 046200)
吳鵬,陳心路,李超
王永超,張安東 (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地球科學與資源學院,北京 100083)
白玉 (安徽省地質環境監測總站,安徽合肥 230001)
李王鵬,季慧麗 (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地球科學與資源學院,北京 100083)
古-中生代生物滅絕與華南早三疊世錯時相沉積研究
何冰輝 (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地球科學與資源學院,北京 100083)
常藍天 (山西潞安環保能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五陽煤礦,山西長治 046200)
吳鵬,陳心路,李超
王永超,張安東 (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地球科學與資源學院,北京 100083)
白玉 (安徽省地質環境監測總站,安徽合肥 230001)
李王鵬,季慧麗 (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地球科學與資源學院,北京 100083)
古-中生代之交生物滅絕是顯生宙以來生態系遭受最具重創的一次生物大滅絕事件(P-T事件),其誘發機制可能與泛大陸聚合、核幔圈層變動以及地幔柱有關。P-T事件后,全球古環境、古氣候發生急劇變化,早三疊世生態系統以低分異度的廣適性分子和機會分子為主,通過對紋層狀和薄層狀灰巖、條帶狀灰巖、扁平礫石灰巖、微生物巖、蠕蟲狀灰巖、潮下皺紋構造以及海底碳酸鹽膠結巖扇等錯時相現象進行詳細論述。表明生物大滅絕后錯時相沉積及構造的出現是古-中生代之交全球異常海洋生態環境的自然響應,它們在華南地區廣泛發育,為研究和認識PTB滅絕后的全球環境變化以及生物滅絕-復蘇提供了重要依據。
PTB滅絕;華南;早三疊世;錯時相;生態系
顯生宙以來共發生了5次規模巨大、影響深遠的生物大滅絕事件,分別發生在奧陶紀末期、泥盆紀晚期、二疊紀末期、三疊紀末期以及白堊紀末期[1]。地質歷史演化過程中每次的生物大滅絕都與當時的全球環境背景密切相關,研究表明地球生命演化是曲折多變的,經歷了很多大的波動,同樣地質歷史時期全球環境背景也發生著重大的變動。筆者著重敘述了古-中生代之交的生物大滅絕事件(P-T事件)以及隨P-T事件后在華南早三疊世地層中廣泛出現的錯時相沉積及其相關構造,錯時相沉積成為認識和研究全球古環境、古氣候變化的新視角。
1 P-T事件
地球生命演化進程中最為關鍵的2大轉折期為新元古代-寒武紀轉折期和二疊紀-三疊紀轉折期,分別發生了寒武紀生命大爆發以及二疊紀末期生物大滅絕事件[2]。在整個古生代的演化歷史中,二疊紀末的生物大滅絕事件是生物演化史上最具災難性的滅絕事件,導致約90%的海洋生物以及約70%的陸地脊椎動物絕滅[3]。與古生代奧陶紀末期、泥盆紀晚期生物滅絕事件相比,這次滅絕事件對整個生態系統產生了根本性影響,破壞了存在約200Ma之久的海洋生態系統結構,促使了以非能動型動物為主的生態結構轉變為以能動型動物為主的生態結構[4],完成了古生代動物群向中生代動物群的轉變。
中國南部的浙江長興縣煤山剖面是很多地質學家一直以來研究二疊紀-三疊紀過渡時期地質演化的重要剖面,煤山剖面具有豐富的生物地層資料[5],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將二疊系-三疊系界線(PTB)正式確定在煤山D剖面及其27c層之底,即牙形石Hindeodus parvus的初現處[6]。PTB的確定以及相關研究的深入,一些學者發現古、中生代之交的生物大滅絕可分為2幕,分別發生在二疊紀末和三疊紀初,稱之為PTB滅絕[7],也即P-T滅絕、P-T事件。
關于PTB滅絕的誘發機制,不同的學者提出了不同的觀點和假設用來解釋生物滅絕事件的主要起因,主要有大規模的火山活動[8-10],海底CO2以及CH4等有毒氣體的大量釋放[11-13]以及缺氧事件[14]等。盡管提出的觀點很多,但大部分研究者趨于尋找地內原因解釋,殷鴻福等[7]研究認為地球內部圈層變動導致地球表層系統的變化,進而導致生物演化的進行,因此提出了PTB滅絕與泛大陸聚合、核幔圈層變動以及地幔柱有關的觀點,認為在泛大陸聚合過程中大量洋殼在消減帶拆沉堆積在核幔邊界,當大量冷的物質下沉到核幔邊界以后,“D”層(核幔邊界)將因熱補償啟動地幔柱,地幔柱的較小一枝于260Ma左右到達地表,導致峨眉山玄武巖的噴發,與之相伴隨發生了中、晚二疊世之交(GLB)的滅絕;到古、中生代之交,地幔柱到達地表,導致了通古斯大爆炸,形成了通古斯大火成巖省(LlPs), PTB滅絕開始發生[7]。P-T事件后,全球古環境、古生態系統發生急劇變化[15],生物復蘇過程曲折復雜,大滅絕后的生物復蘇一直延遲至中三疊世,早三疊世生態系統以低分異度的廣適性分子和機會分子為主[16],且廣泛出現大量異常沉積記錄。
2 錯時相沉積
我國華南地區完整地記錄了古、中生代之交海相生物系統的滅絕與復蘇的過程,成為了全球研究PTB滅絕以及早三疊世生物復蘇最理想的地區。PTB滅絕后,全球環境發生劇烈變化,海洋生態系統遭受重創,沉積類型也發生了劇烈變化。在早三疊世地層中出現了硅間斷[17]、礁間斷[18]以及煤間斷[19],在淺海環境中,相應的變化表現為大量特殊沉積及其相關構造在早三疊世地層中廣泛出現,如紋層狀和薄層狀灰巖、條帶狀灰巖、扁平礫石灰巖、微生物巖、蠕蟲狀灰巖、潮下皺紋構造以及海底碳酸鹽膠結巖扇等[20]。這些特殊沉積及構造在奧陶紀之前的海洋環境中曾廣泛分布,但在奧陶紀后生動物大發展之后,它們一般僅見于某些極端和異常環境中,當它們在早三疊世正常淺海環境中再次廣泛出現時,被認為在時間上或環境上發生了錯位,故被稱為錯時相[21]。由于早三疊世整個生態系是極為蕭條的,化石保存稀少單調,這就使得研究者把認識早三疊世全球環境變化的視角轉為研究沉積及構造等,因此錯時相沉積的研究成為了探索PTB滅絕及生物復蘇的一個新途徑。
2.1 紋層狀和薄層狀灰巖、條帶狀灰巖
在華南地區,紋層狀、薄層狀灰巖以及條帶狀灰巖在早三疊世地層中廣泛發育,反映了當時相對安靜、低能的沉積環境,預示著早三疊世時期特提斯洋流活動趨于停滯,這一現象與全球缺氧環境以及海洋循環的停滯[22]相一致[23]。羅茂等[24]對貴陽花溪下三疊統大冶組地層研究中發現,早三疊世淺海生態環境處于缺氧環境,這種環境直到早三疊世晚期才趨于正常,在遺跡化石產出上表現為見沿層面水平擾動的表生跡,缺乏垂直遺跡化石。垂向生物擾動活動的缺乏,有利于紋層狀、薄層狀沉積構造的保存,成為這種錯時相沉積在早三疊世地層中廣泛發育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溫度和季風等氣候因素也是形成紋層狀沉積的控制因素,隨季節性變動形成的各種物質,按不同季節形成連續的沉積紋層[25]。
時志強等[25]在四川廣元上寺以及重慶北碚等地早三疊世地層均發現有紋層狀泥質微晶灰巖,部分地區含較多的粉砂級陸源碎屑物質,推測為三疊紀巨型季風成因,即季風發育時期從上揚子古陸地區帶來懸浮物質,在季風停歇期沉積下來。需要指出的是,在不同地區不同沉積環境以及同一地區不同沉積背景下,紋層狀、薄層狀灰巖以及條帶狀灰巖在巖性特征、顏色變化和成分組成上都有較大的差異[26]。
2.2 扁平礫石灰巖
扁平礫石灰巖由板條狀或扁平狀的泥晶灰巖礫石和灰泥基質組成,灰巖礫石有一定的磨圓性,礫石中缺乏化石[20],反映了PTB滅絕后,后生動物的活動受到了很大的抑制。扁平礫石灰巖主要有2種,為板條狀灰巖和竹葉狀灰巖[27],在寒武紀以及前寒武紀陸架環境中普遍發育,形成于缺乏垂向生物擾動的低能環境下,由早期成巖階段形成的尚未完全固結的條帶狀或薄層灰巖,在風暴巨浪或者重力流下被破碎,而后以微晶-泥晶灰巖礫屑的形式重新堆積成巖[20,28]。
扁平礫石灰巖的形成與風暴作用密切相關,部分灰巖中可見菊花狀構造,發育丘狀交錯層理以及沖刷侵蝕面[23],其中丘狀交錯層理是風暴巖中獨特的原生沉積構造,是識別風暴沉積最明顯的標志之一。時志強等[27]研究發現在川西北地區飛仙關組下部地層中,單個丘狀交錯層理保存不完整,大多數是多個丘狀交錯層相互疊加形成,表明當時風暴活動持續時間較長,具多期次等特點。
關于扁平礫石灰巖的形成機制,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因素。扁平狀灰巖礫石是由薄層狀、條帶狀灰巖破碎而成,許多學者在這一點上的認識都是一致的,然而薄層狀微晶-泥晶灰巖是靜水環境下的產物,在外力作用下要破碎形成礫石而不是形成更細的灰泥,這就要求它在破碎前已經基本固結了[29]。Sepkoski等[21]提出了扁平礫石灰巖得以發育的3個主要條件:薄層碳酸鹽巖和泥巖互層、未擾動的碳酸鹽巖層快速膠結、扁平狀灰巖顆粒遭受強烈的風暴作用的侵蝕和改造。三疊紀上揚子地區巨型季風盛行,早三疊世早期和晚三疊世卡尼期是三疊紀巨型季風最為劇烈的2個時期,PTB生物大滅絕引發的Gaia效應很有可能是早三疊世早期巨型季風盛行的主導因素[25]。Gaia理論認為,生物對其生活環境有很大的影響,并調節全球的環境,它強調生物對整個地球系統的調節作用,生物對全球環境起到了反饋作用,主要是負反饋,遏制地球系統向極端情況發展,使生物與環境協同發展[30-32]。在古、中生代之交,生物大量滅絕,生物對整個地球系統的調節作用大大減弱,全球環境變得極端惡劣且得不到有效遏制,從而可能導致巨型季風的形成,成為扁平礫石灰巖形成的誘發因素。在外力作用下,條帶狀或薄層灰巖破碎形成角礫,角礫進而經過磨圓形成扁平狀礫石,在此過程中,礫石除了受到動蕩水體底部運動引起的機械磨圓外,更重要的是受到了化學溶蝕作用[29]。因為扁平礫石灰巖常常與薄層狀、紋層狀泥晶灰巖互層,巨型季風引起的風暴作用是偶發事件,礫屑大多數處于相對安靜的靜水環境,機械磨蝕時間很短,而且扁平狀灰巖礫屑是易溶的,因此當水中溶解的CO2濃度達到一定的程度,灰質礫屑邊緣就會發生一定的化學溶蝕作用。當風暴等作用攪動水體時,會增加水體中O2的溶解量,從而使礫石邊緣氧化成紅色或淺紫色。
2.3 蠕蟲狀灰巖
蠕蟲狀灰巖,因這種灰巖內含有形似蠕蟲的個體,故命名為蠕蟲狀灰巖,其主要由2部分組成,即蠕體和基質。蠕體呈深灰色,主要由為微晶方解石組成,黏土等含量極少,形態很不規則,多具有塑性變形特征,大小不一;基質呈淺色,主要成分為微晶方解石,但黏土礦物等含量稍高些,最高可達15%左右,并含有少量的石英、長石等陸源礦物[33]。宏觀上看,蠕蟲狀灰巖中蠕體顏色較基質顏色深,但是在顯微鏡下卻相反,蠕體因含黏土礦物極少而顯得透明,顏色較淺;基質由于含稍高的黏土礦物,鏡下顏色較深[34]。
按不同的分類依據,蠕蟲狀灰巖有不同的分類方法。根據蠕體的產出形態,可以把蠕蟲狀灰巖分為3類[34]:①順層連續線紋狀,蠕體呈線狀平直連續產出,且平行于層面;②順層斷續點狀,蠕體孤立呈點狀,大致沿層面或平行層面分布,可連接成線狀;③異形雜亂狀,蠕體形態不規則,呈橢圓狀、團塊狀、蝌蚪狀、彎曲狀等形態,在基質中雜亂分布。趙小明等[35]根據蠕體的形態,將蠕蟲狀灰巖分為4種類型:①層狀或似層狀蠕蟲狀灰巖,蠕體平行于層面連續或斷續產出;②不規則粒狀蠕蟲狀灰巖,蠕體排列雜亂,大小不一,呈不規則的粒狀或斑點狀;③變形柱狀蠕蟲狀灰巖,蠕體呈短柱狀、管狀,與層面垂直或斜交;④橢球狀蠕蟲狀灰巖,蠕體呈規則的球狀-橢球狀。這2種方案都是根據蠕體產出形態的分類,在本質上是相同的。時志強等[23]按成因將蠕蟲狀灰巖分為2類:a型蠕蟲狀灰巖(即生物成因的蠕蟲狀灰巖)和b型蠕蟲狀灰巖(即生物、水動力及化學等復合成因的蠕蟲狀灰巖)。黃思靜等[36]按成因將蠕蟲狀灰巖分為2類:①主要由物理沉積和化學凝聚作用形成的蠕粒狀泥晶灰巖;②主要是由生物作用形成的生物潛穴擾動灰巖。蠕蟲狀灰巖中有豐富的沉積構造,在一定情況下它能反映當時的沉積環境,如介質動力條件、沉積速度以及沉積物負載壓力等,對研究蠕蟲狀灰巖的成因有重要意義[37]。在蠕蟲狀灰巖中常見的沉積構造有底模構造、旋渦狀構造、平行層理、丘狀交錯層理,以及滑動變形構造、蠕蟲狀變形構造、包卷層理、泄水構造等同生變形構造,其中同生變形構造的發育,表明了蠕蟲狀灰巖是快速堆積作用下形成的,并不是在低能條件下形成的灰泥石灰巖[33,37]。盡管許多學者從各個方面對蠕蟲狀灰巖的性質進行了詳細的研究,但是對其成因即形成機理,一直存在爭議,還沒有統一的認識,目前比較流行的觀點有機械破碎作用、化學凝聚作用、生物擾動作用以及復合作用成因等。可以肯定的是蠕蟲狀灰巖的成因很復雜,不同的類型有著不同的成因條件[35]。

圖1 蠕蟲狀灰巖形成機理圖

圖2 蠕蟲狀灰巖的類型及形成機理
錢守榮[33,37]通過對蠕蟲狀灰巖沉積特征的研究,認為蠕蟲狀灰巖的形成與風暴作用有關,是風暴濁流下快速堆積的產物,且主要形成于陸棚或斜坡上部地帶。在正常情況下,海底沉積以灰泥為主,當受到早三疊世早期巨型季風[25]的影響時,可形成風暴濁流,風暴濁流沖蝕海底灰質軟泥,形成蠕蟲狀灰巖。由于風暴能量、自身流態以及搬運距離等的不同,往往會形成不同的蠕蟲狀灰巖類型。在風暴濁流能量較高的情況下,以渦流作用為主,形成異形蠕蟲狀灰巖;當風暴濁流能量大大減弱,以牽引流作用為主時,形成層狀蠕蟲狀灰巖[33]。筆者認為風暴濁流下快速堆積形成的蠕蟲狀灰巖,實際上是一種原生沉積層經后期改造再沉積形成的灰巖。姜月華等[38]認為蠕蟲狀灰巖是由多種成因復合或疊加改造形成的,沉積作用、沉積分異作用是形成蠕蟲狀灰巖的重要前提,生物擾動作用、水流作用以及壓實壓溶作用是形成各種蠕蟲狀灰巖的關鍵。可以歸納為,先期形成的條紋狀、條帶狀灰泥灰巖,被生物擾動,隨著生物擾動強度的增強,依次形成順層連續蠕蟲狀灰巖、順層斷續蠕蟲狀灰巖、斑點或斑塊狀蠕蟲狀灰巖、泥質灰巖;已經形成的蠕蟲狀灰巖經受后期風暴等作用的改造再沉積,形成蠕粒狀灰巖(一種粒屑灰巖),經受壓實壓溶作用,可形成透鏡狀蠕蟲狀灰巖[38](見圖1)。
朱洪發等[34]通過研究認為,極薄層的灰質與泥質互層沉積在上部斜坡帶環境,因斜坡帶的重力滑動引起不同程度的破裂、位移,部分疊加了生物擾動作用的改造,再加上成巖壓實作用,最終導致了各種蠕蟲狀灰巖的形成(見圖2)。
需要注意的是,蠕蟲狀灰巖與瘤狀灰巖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兩者在成因、成分上均有不同。瘤狀灰巖的瘤體和蠕蟲狀灰巖的蠕體成分均主要為方解石,黏土物質含量極少;蠕蟲狀灰巖的基質成分也主要為方解石,含一定量的黏土物質和長石、石英等陸源碎屑,含量可達15%左右,而瘤狀灰巖的基質中方解石含量不超過45%,其余主要為黏土礦物等[39]。根據前人的研究成果,關于蠕蟲狀灰巖的形成機理,可以提出一個比較合理且有一定說服力的觀點,即蠕蟲狀灰巖是在紋層狀、條帶狀、薄層狀微晶-泥晶灰巖沉積的基礎上,經差異壓實、生物擾動以及機械破碎等作用形成的。蠕蟲狀灰巖形成過程中的生物作用,是低水平的生物擾動,該類作用參與形成的蠕蟲狀灰巖的出現,標志著底層環境的改善和底棲生物群落及其活動能力的加強[35]。
2.4 微生物巖
微生物巖一詞最早由Burne和Moor[40]提出,后隨著微生物巖的研究和認識的不斷深入,將微生物巖定義為:由底棲微生物群落的生長和生理活動,引起沉積質點粘結和圈捕、或表面礦物沉淀、或生物礦化作用而產生的生物沉積巖,主要類型包括疊層石、核形石、樹枝石、凝塊石以及某些鮞粒、團粒、球粒和泥晶[41]。但是關于微生物巖的一些類型仍存在爭議,吳亞生等[42]在研究二疊紀-三疊紀之交缺氧環境的微生物巖時,就曾在文章中指出存在的爭議。如Kershaw等[43]在重慶附近PTB剖面發現一種含樹枝狀構造的特殊沉積,對其歸入微生物巖表示懷疑,并不能確定其成因,并指出也許根本不是生物成因的。但是后來,Ezaki等[44]在該特殊沉積的樹枝體內部發現了小球狀的微生物化石,故認為該特殊沉積是微生物成因的。
在地質歷史時期,每次生物大滅絕后,都出現微生物繁盛現象,微生物的繁盛與后生動物的絕滅導致生存競爭的減少有關,而且形成的微生物巖中記錄了很多重要信息,對其研究主要是根據地層中保存下來的微生物巖和微生物有機個體,當它們保存狀態很差時,一般可以采用類脂物生物標志化合物進行研究分析[45]。
古-中生代之交發生了顯生宙以來最大的生物絕滅事件,大量海洋生物滅絕,海洋生態系統遭受重創[3],之后,微生物巖在全球廣泛發育,而且大部分都發育在低緯度的淺水海洋環境,向深水區很快尖滅[46]。微生物巖在早三疊世再現于正常淺海地層中,并一直延續到早三疊世末,這正是對始于二疊紀末惡劣環境狀況和后生動物稀少的生態系面貌的自然響應[20,47]。吳亞生等[42]研究發現,早三疊世的微生物巖與通常意義的生物礁在形成機制和環境意義上有本質的區別,因而不能看成是生物礁巖,在微生物巖中常發現有細小草莓狀黃鐵礦,說明形成于缺氧環境中,并且形成于不適宜大多數生物生存的環境,由微生物機會主義繁盛形成;而生物礁一般形成于適宜生物生存的溫暖、富氧環境。
微生物巖的發育與火山活動的強度有關,在華南地區,PTB火山活動最強,那里的微生物巖最發育,且普遍含Eu異常[7]。華南地區的微生物巖主要分布在礁頂或淺水碳酸鹽巖臺地上,向周圍深水區則很快尖滅,微生物巖的出現往往代表一種特殊的生態環境,對這套微生物巖的研究有助于揭示二疊紀末-早三疊世全球事件在礁相或淺水碳酸鹽巖臺地上的具體反映[48]。
劉建波等[49]研究發現,微生物巖形成于早三疊世最早期,相當于Hindeodus parvus帶,在二疊紀末華南地區海平面下降,造成某些地區二疊紀地層與早三疊世微生物巖之間存在沉積間斷或剝蝕,并可使三疊紀牙形石混入二疊紀末期的沉積地層中,因此在研究微生物巖沉積地層時要尤其注意。在早三疊世地層中發育的微生物巖在分布上具有全球普遍性,在產出時間上具有全球等時性,對其研究能為認識二疊紀末-早三疊世全球海洋環境的演化提供了重要信息[50]。
2.5 潮下皺紋構造和海底碳酸鹽膠結巖扇
潮下皺紋構造一般發育于陸架背景下具沙紋層理的碎屑巖層面,形態類似于干涉波痕,波峰呈扁平狀或尖棱狀,且常伴有小型水平遺跡[20]。Hagadorn等[51]認為潮下皺紋構造是以微生物席為媒介形成的,在奧陶紀之后的地層中很少出現,當其再現于早三疊世地層中時,被認為是錯時相沉積[21]。已在早三疊世地層中發現的潮下皺紋構造均分布在大洋邊緣,野外露頭主要產于碳酸鹽巖和陸源碎屑巖互層中,主要形成于低能、開闊的海陸過渡相環境,一般常在正常浪基面和風暴浪基面之間的潮下帶環境中沉積[52]。海底碳酸鹽膠結巖扇是由放射狀晶體形成的半球狀集合體,排列方式雜亂[20],鏡下鑒定表明其為同沉積海底膠結文石扇,后被方解石交代[53-54]。Woods等[55]認為,海底碳酸鹽膠結巖扇形成于缺氧環境,有機質的硫酸鹽還原作用導致深水域的增加,同時伴隨著CO2濃度和堿性的增加。海底碳酸鹽膠結巖扇被認為局限于元古代,其再現于早三疊世地層中,表明當時的海洋環境處于缺氧、高堿度、CaCO3過飽和的極端環境,與元古代的環境相類似[20]。目前為止,在整個華南地區早三疊世地層中尚未發現有海底碳酸鹽膠結巖扇以及潮下皺紋構造沉積,關于其成因機制和沉積環境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和探討[26]。
3 討論
1)根據早三疊世地層中廣泛發育的大量錯時相沉積[20]以及Gaia理論[32],可以推斷在古-中生代之交生物集群滅絕,生物對全球系統的調節作用大大減弱,全球古環境與古氣候變得極端惡劣。錯時相是一種典型的特殊海洋環境的標志,緊接著PTB滅絕后廣泛出現的微生物巖正是該種特殊環境開始的標志,也是大滅絕后后生動物在生態系統中的主導地位被剝奪的標志[56]。趙小明等[35]通過對華南地區早三疊世錯時相沉積的研究認為,PTB生物大滅絕后,錯時相沉積大量發育,并隨著海洋系統的重建而退出了正常淺海環境,該耦合關系正是沉積體系和生態系對古-中生代地質突變以及其導致的異常環境的自然響應。
2)錯時相沉積在早三疊世地層中的廣泛發育,表明當時的大洋環境處于一種異常狀態,這種環境狀態是造成三疊紀初生物遲緩復蘇的重要原因,早三疊世的海洋環境也曾發生過多次強烈波動,波動的原因可能是異常環境的周期性介入以及生態系統重建過程中生物與環境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56]。在P-T界限附近,C同位素表現為強烈負偏現象[12],這可能與火山活動、缺氧環境以及海底CH4水合物的釋放等有關[26]。
3)扁平狀礫石灰巖、紋層狀和薄層狀灰巖、條帶狀灰巖、微生物巖、蠕蟲狀灰巖、潮下皺紋構造以及海底碳酸鹽膠結巖扇等錯時相的廣泛發育,不僅與后生動物的減少和垂向擾動的降低有關,而且同沉積海底膠結作用也是其形成的關鍵因素[35],快速的同沉積海底膠結作用使早期形成的沉積物在遭受破壞、擾動之前就已基本固結成巖,當遭受風暴等作用破碎時,以致于形成較大的碎塊而不是更細的灰泥等物質,這是形成扁平狀礫石灰巖的前提。趙小明等[35]認為廣泛的海底膠結作用,可能源于當時海洋翻轉造成的大洋深部碳酸鹽過飽和的貧氧海水上翻,以及海水堿度的升高,大大促進了同沉積海底膠結作用的發生。P-T事件后,早三疊世時期,海洋環境處于大幅度的動蕩環境,這與當時全球CO2增加導致的全球變暖、海水溫度升高以及當時盛行的巨型季風誘發的強烈風暴作用有關[57]。早三疊世生態系以分異度極低的廣適性分子和機會主義分子為主,化石保存單調且稀少,這就使得錯時相沉積及其相關構造成為研究生物滅絕與復蘇的全新視角[20]。此外,早三疊世時期極端惡劣的環境頻繁波動,導致生物復蘇遲緩,隨著生物的逐漸復蘇和環境的逐漸改善,錯時相沉積也漸漸消失了,因此錯時相的消失可作為生態環境得到明顯改善和生物復蘇期結束的標志[35]。此外,一些研究表明新元古代-寒武紀和P-T時期的地質和生物演化歷史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許多發生在新元古代-寒武紀之交的重大地質事件在P-T之交重復發生,只是具體型式、幅度和過程有明顯的差別[2],這一發現為認識地質歷史時期全球發生的重大地質事件提供了新的思考以及研究思路。
[1]Raup D M,Sepkoski J J.Mass Extinctions in the Marine Fossil Record[J].Science,1982,215:1501-1503.
[2]沈樹忠,朱茂炎,王向東,等.新元古代-寒武紀與二疊-三疊紀轉折時期生物和地質事件及其環境背景之比較[J].中國科學(D 輯:地球科學),2010,40(9):1228-1240.
[3]Erwin D H.The Permo-Triassic extinction[J].Nature,1994,367:231-236.
[4]Haijun Song,Wignall P B,Jinnan Tong,et al.Two pulses of extinction during the Permian-Triassic crisis[J].Nature Geoscience, 2013,6(1):52-56.
[5]曹長群,鄭全峰.煤山二疊紀-三疊紀過渡期事件地層時序的微觀地層記錄[J].中國科學(D輯:地球科學),2009,39(4):481-487.
[6]殷鴻福,張克信,童金南,等.全球二疊系-三疊系界線層型剖面和點[J].中國基礎科學,2001(10):10-23.
[7]殷鴻福,宋海軍.古、中生代之交生物大滅絕與泛大陸聚合[J].中國科學(D輯:地球科學),2013,43(10):1539-1522.
[8]楊遵儀,吳順寶,殷鴻福,等.華南二疊-三疊紀過渡時期地質事件[M].北京:地質出版社,1991.
[9]Jin Y G,Wang Y,Wang W,et al.Pattern of marine mass extinction near the Permian Triassic boundary in South China[J]. Science,2000,289(5478):432-436.
[10]Lei Zhou,Frank T.Kyte.The Permian-Triassic boundary event:a geochemical study of three Chinese sections[J].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1988,90(4):411-421.
[11]Knoll A H,Bambach R H,CanfieⅠd D E,et al.Comparative Earth history and late Permian mass extinction[J].Science,1996, 273(5274):452-457.
[12]李玉成,周忠澤.華南二疊紀末缺氧海水中的有毒氣體與生物集群絕滅[J].地質地球化學,2002,30(1):57-63.
[13]Krull E S,Retallack G J.δ13C depth profiles from paleosols across the Permian-Triassic boundary:Evidence for methane release[J].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Bulletin,2000,112(9):1459-1472.
[14]Wignall P B,Twitchett R J.Oceanic anoxia and the end Permian mass extinction[J].Science,1996,272(5265):1155-1158.
[15]Kozur H W.Some aspects of the Permian-Triassic boundary(PTB)and of the possible causes for the biotic crisis around this boundary[J].Palaeogeography,Palaeoclimatology,Palaeoecology,1998,143(4):227-272.
[16]Hallam A.Mass Extinctions and Their Aftermath[M].US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17]Racki G.Silica-secreting biota and mass extinctions:Survival patterns and processes[J].Palaeogeography,Palaeoclimatology, Palaeoecology,1999,154(1):107-132.
[18]Flügel E.Triassic reef patterns[J].Special Publications,2002(72):391-463.
[19]Retallack G J,John J.Veevers and Ric Morante.Global coal gap between Permian-Triassic extinction and Middle Triassic recovery of peat-forming plants[J].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Bulletin,1996,108(2):195-207.
[20]趙小明,牛志軍,童金南,等.早三疊世生物復蘇期的特殊沉積-“錯時相”沉積[J].沉積學報,2010,28(2):314-323.
[21]Sepkoski J J,Bambach R K,Droser M L.Secular changes in Phanerozoic event bedding and the biological imprint[C].Ⅰn:Einsele G,Ricken W,Seilacher A(ed.),Cycles and Events in Stratigraphy.Berlin:Springer-Verlag,1991:298-312.
[22]Ⅰsozaki Y.Permo-Triassic Boundary Superanoxia and Stratified Superocean:Records from Lost Deep Sea[J].Science Magazine, 1997,276(5310):235-238.
[23]時志強,安紅艷,伊海生,等.上揚子地區早三疊世異常碳酸鹽巖的分類與特征[J].古地理學報,2011,13(1):1-10.
[24]羅茂,時國,龔一鳴.貴陽花溪早三疊世遺跡化石及其對二疊紀末生物大滅絕事件后生物復蘇的啟示[J].古地理學報,2007, 9(5):519-532.
[25]時志強,曾德勇,熊兆軍,等.三疊紀巨型季風在上揚子地區的沉積學記錄[J].礦物巖石地球化學通報,2010,29(2):164-172.
[26]張華.上揚子地區早三疊世錯時相沉積記錄:大滅絕后的Gaia效應[D].成都:成都理工大學,2011.
[27]時志強,伊海生,曾德勇,等.上揚子地區下三疊統飛仙關組一段:大滅絕后從停滯海洋到動蕩海洋的沉積記錄[J].地質論評, 2010,56(6):769-780.
[28]Wignall P B,Twitchett R J.Unusual intraclastic limestones in Lower Triassic carbonates and their bearing on the aftermath of the end-Permian mass extinction[J].Sedimentology,1999,46(2):303-316.
[29]章雨旭,萬渝生.北京西山竹葉狀灰巖的成因[A].中國地質科學院[C].北京:地質研究所,1990(22):56-64.
[30]Lenton T M,Schellnhuber H J,Szathmary E.Climbing the co-evolution ladder[J].Nature,2004,431(7011):913-913.
[31]Lovelocka J E.Gaia as seen through the atmosphere[J].Atmospheric Environment,1972,6(8):579-580.
[32]孫樞,王成善.Gaia理論與地球系統科學[J].地質學報,2008,82(1):1-9.
[33]錢守榮.蠕蟲狀灰巖成因新解[J].淮南礦業學院學報,1995,15(3):15-19.
[34]朱洪發,王恕一.蘇南、皖南三疊紀瘤狀灰巖、蠕蟲狀灰巖的成因[J].石油實驗地質,1992,14(4):454-460.
[35]趙小明,童金南,姚華舟,等.華南早三疊世錯時相沉積及其對復蘇期生態系的啟示[J].中國科學(D輯:地球科學),2008, 38(12):1564-1574.
[36]黃思靜.蠕蟲狀灰巖及其成因[J].成都地質學院學報,1984(3):60-69.
[37]錢守榮.蠕蟲狀灰巖中的同生變形構造及其成因[J].安徽地質,1996,6(1):38-41.
[38]姜月華,岳文浙,業治錚,等.蠕蟲狀灰巖特征和成因新探[J].礦物巖石,1992,12(1):1-12.
[39]張杰,童金南.下揚子地區下三疊統蠕蟲狀灰巖及其成因[J].古地理學報,2010,12(5):535-548.
[40]Burne R V,Moore L S.Microbialites:organosedimentary deposits of benthic microbial communities[J].Palaios,1987,2(3):241-254.
[41]戴永定,陳孟莪,王堯.微生物巖研究的發展與展望[J].地球科學進展,1996,11(2):209-216.
[42]吳亞生,姜紅霞.二疊紀-三疊紀之交缺氧環境的微生物和微生物巖[J].中國科學(D輯:地球科學),2007,37(5):618-628.
[43]Kershaw S,Zhang T,Lan G.A microbialite carbonate crust at the Permian-Triassic boundary in South China,and its palaeoenvironmental significance[J].Palaeogeography,Palaeoclimatology,Palaeoecology,1999,146(1):1-18.
[44]Ezaki Y,Liu J,Adachi N.Earliest Triassic Microbialite Micro-to Megastructures in the Huaying Area of Sichuan Province,South China:Ⅰmplications for the Nature of Oceanic Conditions after the End-Permian Extinction[J].Palaios,2003,18(4):388-402.
[45]謝樹成,Pancost R D,殷鴻福,等.二疊紀三疊紀之交微生物變化與動物集群滅絕的兩次耦合[J].自然雜志,2005,27(3):144.
[46]雷麗丹.微生物巖在地質歷史時期的研究[J].科技傳播,2011(21):104.
[47]Schubert J K,Bottjer D J.Early Triassic stromatolites as post-mass extinction disaster forms[J].Geology,1992,20(10):883-886.
[48]王永標,童金南,王家生,等.華南二疊紀末大絕滅后的鈣質微生物巖及古環境意義[J].科學通報,2005,50(6):552-558.
[49]劉建波,江崎洋一,楊守仁,等.貴州羅甸二疊紀末生物大滅絕事件后沉積的微生物巖的時代和沉積學特征[J].古地理學報, 2007,9(5):473-486.
[50]何磊,王永標,楊浩,等.華南二疊紀-三疊紀之交微生物巖的古地理背景及沉積微相特征[J].古地理學報,2010,12(2):151-163.
[51]Hagadon J W,Bottjer D J.Wrinkle structures:Microbially mediated sedimentary structures common in subtidal siliciclastic settings at the Proteroaoic-Phanerozoic transition[J].Geology,1997,25(11):1047-1050.
[52]王艷艷.川西北地區早三疊世早期錯時相灰巖特征及其意義[D].成都:成都理工大學,2012.
[53]Sandberg P A.Aragonite cements and their occurrence in ancient limestones[A].Edited by Schneidermann N,Harris P M.Carbonate Cements[C].SEPM,Tulsa,Okla.,Special Publication,Society for Sedimentary Geology,1985,36:33-57.
[54]Sumner D Y,Grotzinger J P.Late Archean aragonite precipitation:petrography,facies associations,and environmental significance[J].Carbonate Sedimentation and Diagenesis in the Evolving Precambrian World,2000,67:123-144.
[55]Woods A D,Bottjer D J,Mutti M,et al.Lower Triassic large sea floor carbonate cements;their origin and a mechanism for the prolonged biotic recovery from the end Permian mass extinction[J].Geology,1999,27(7):645-648.
[56]童金南,殷鴻福.早三疊世生物與環境研究進展[J].古生物學報,2009,48(3):497-508.
[57]張華,時志強,羅鳳姿,等.P-T事件后特提斯洋從停滯到動蕩的巖石學證據[J].成都理工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1, 38(2):175-184.
[編輯]辛長靜
TE121.34
A
1673-1409(2014)26-0024-07
2013-11-24
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項目(2011CB808901)。
何冰輝(1989-),男,碩士生,現主要從事含油氣盆地沉積學方面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