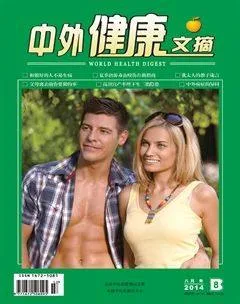不要在腫瘤患者身上做得太多
鐘烙
“永遠不要在病人身上做得太多。”這是古希臘醫圣希波克拉底留下的警世恒言。事實上,過度醫療不僅傷害了患者,對醫生職業的尊嚴和本應得到的社會尊重與信任也造成了重創,直接使患者對種種醫療行為產生“恐懼感”。他們在面臨尊嚴恐懼、社交恐懼、賬單恐懼之外,還存在另一種在死亡線上掙扎的“就醫恐懼”:他們知道自己將不久于人世,卻仍然不得不花費精力,執著地識別、規避現行落后的醫療理念可能給自己造成的身體傷害和精神損失。
人為刀俎,我為魚肉
一位患者臨終前在互聯網上說:“這些年,我算是找到‘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感覺了。每天,我都要和來自醫院內外的五花八門的忽悠‘斗智斗勇。就要走到盡頭了,這樣的生活卻不值得留戀。”
一位網友說:“從診斷為肺癌那天起,我壯碩的父親就沒過過一天好日子!先手術,后放療、化療。隨著一個個療程的推進,惡心、嘔吐、疼痛、失眠很快把父親折騰得脫了形。醫生卻總是告訴我們,瘤子有縮小,治療有效果,‘不要走開,下集更精彩。”
當然,如果把當前腫瘤治療的弊端完全歸結為醫生在利益驅動下不計后果地實施過度治療,也是對復雜現象簡單化的偏頗解讀。
要挑戰過度醫療太難
何謂過度醫療?美國心臟病學會給出的定義是:醫生違背醫學規范和倫理準則,脫離病情實際需求,實施不恰當、不規范、不道德的醫療行為。
當前醫學技術不分青紅皂白地被過度使用,帶來了很多負面影響。一位醫學院士曾舉例說明:“20年前,胃癌診斷只需440元,而現在基礎診斷就需要2830元,如果運用最高端診斷技術所需的花費則上升至8000~10000元;胃癌的化療從20年前的每人次平均100元提高到現在的15050元。”
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正式批準了一種腫瘤生物治療藥物,臨床應用的統計學結果顯示其只能延長患者4.1個月的生存壽命,卻要付出約合人民幣30萬元的高昂代價。難怪一個由世界衛生組織支持的國際研究小組警告說:“目前醫學的發展是在全世界創造供應不起的、不公正的醫學。”
衛生主管部門也曾指出,過度治療和不當治療極大地增加了全民醫療支出,普遍存在著“人生最后一年甚至一個月花掉一生80%醫藥費”的狀況。商業追求利潤的本能、廣大群眾對醫學的誤解、醫務人員對高科技的盲目崇拜,全方位地增強了過度醫療的吸引力。
對生命關懷遠遠不足
之所以提出腫瘤的“適宜治療”理念,還因為在對過度醫療一邊倒的詬病中,與過度治療同樣嚴重存在的“治療不足”和“治療缺位”被忽略了。目前腫瘤治療的現狀是:在抗癌過度的同時,對姑息支持、生命關懷遠遠不足;對“身”處置過度,對“心理治療”等關注不足。
腫瘤病因機體內外環境的多元性、癌基因的多樣性、腫瘤病理形態的異質性、手術和放療的局限性、藥物治療中的多藥耐藥性、患者心理素質和社會狀況及基礎疾病的復雜性、醫生觀念的片面性以至知識結構的單一性等,常使腫瘤治療顯得無定力、無層次——或者“一條道走到黑”,“生命不息,抗癌治療不止”;或者左顧右盼,拿捏不準患者是否獲益的“治療拐點”、治療重點應否轉移;或者干脆放任,將其邊緣化而無人問津。
顯然,要走出這種窘境,首先應當明確治療的目標,而患者的需要和期盼就是腫瘤醫生的努力目標和方向。
腫瘤治療的目標不能紊亂
對腫瘤進行“適宜治療”固然是一個醫學專業問題,但同時也是一個如何看待生命、如何看待患者的倫理道德問題,還是一個如何看待理論和實踐關系的哲學問題。對生命、對患者、對實踐的深刻認知和尊重,有助于我們從根本上堅定對所有腫瘤患者既不缺位也不過度,進行“適宜治療”的信念。
社會對腫瘤醫生的職業要求是:以善良憫人之心,給患者的生命注入新的活力,肩負起做幸福感的傳遞者和幸福夢的“圓夢人”的責任,鍛造并賦予一個生命以嶄新的面貌,哪怕這個生命將不久于人世。
對腫瘤“適宜治療”的追求就在于讓腫瘤患者即便行將辭世,也能不留遺憾地對這個世界和他們的親人說一聲:“我對自己的一生滿意,也對自己的醫生滿意。”
(摘自《健康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