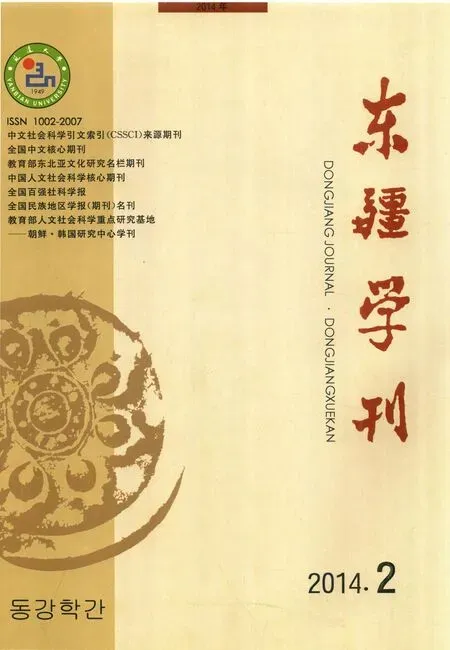論韓國與臺灣的福利體制發展
劉小暢
[責任編輯 全紅]
韓國與臺灣的福利體制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歷程,這其中發生的變化也一直與其經濟政策和政治制度的變遷密切相關。在威權體制時期,福利政策一直作為經濟生產的附屬物而存在,而在經歷民主化轉型之后,韓國與臺灣的福利政策已經慢慢成為人民捍衛自身權利需求的一種反映。本文結合韓國與臺灣發展歷程中的經濟政治環境對兩者福利體制的發展道路做一個梳理,進而說明這種福利政策從“選擇主義”向“普遍主義”轉變的發展路徑有其歷史必然性,而促成這種轉變的除了經濟政策的調整,更重要的是民主力量的作用。
一、經濟優先與“選擇主義”
韓國與臺灣有很多相似之處。在威權體制時期兩者都走向了勞動力密集型的、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也都在 20世紀 50年代開啟了福利制度的建設工作。但是,韓國與臺灣的社會福利政策在其形成初期,并不像西方那樣是通過各種社會力量的民主性參與和需求而產生的,而是為了在急速發展的產業化戰略中進行資本積累并取得威權主義政權支配的合法性而進行發展的雙面戰略。因此,二者的福利制度在威權主義時期就具有鮮明的“生產主義”特征,埃斯平-安德森在《轉型中的福利國家》一書中特別指出,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社會福利發展模式與西方經驗并不相同,其原則是一種圍繞國家建設的主要目標而采取的適應性學習與發展的戰略。[1](313)
的確,在 20世紀50年代到 80年代的威權體制下,韓國與臺灣奉行的是增長優先的原則。威權政府需要用經濟上的快速發展取得其統治的合法性,而當時無論領袖、官僚還是民眾都希望實現與西方同等的經濟發展,[2](11)經濟優先的發展思路自然體現在其社會政策的制定過程中。韓國社會福利制度的基本雛形是在 1960年張勉政權和樸正熙軍事政權時代形成的。1961年和1962年間制定了包括生活保護法在內的各種社會福利法。張勉政權時期,開始實行公務員年金法、軍事政權中的軍人年金法等特殊職業的年金制度。[2](11)1970年開始實施重工業化戰略,1973年的國民福利年金法便是在確保政權的合法性同時又能在短時期內募集年金資金以實現重工業化的內部動員目的的背景下制定出來的。[2](11)另一方面,急速推行的重工業化出現了技術人力的不足,醫療費的增加、工傷事故的頻發和勞動費用的上升迫使政府內部開始關心醫療保險。特別是作為國民年金實施失敗的替代品,醫療保險制度具有迫切的政治需要性。這些復雜的原因促成了 1976年醫療保險法的全面修訂以及 1977年醫療保險制度正式施行。醫療保險制定了由雇員和雇主平均負擔的繳費方式,國家只負擔行政費用并進行管理。這樣既不妨礙當時經濟增長的基礎,也把國家的財政干預降低到了最小限度。與韓國類似,臺灣這個時期的福利政策主要是根據經濟增長模式的需要和維護政治統治建立了一系列單一且分離的社會保險項目。[3](149)20世紀 50、60年代的臺灣社會保險特別突出了維護國民黨統治與保障社會穩定的功能,社會立法與方案主要集中于軍、公、教和勞工保險,形成了所謂的“軍公教福利國”。當臺灣邁入以出口為導向的工業化社會時,政府出于勞動力保障的需求,于 1970年修正并實施了“勞工保險條例”,提高了保險費率,疾病給付增加了項目,降低了納入投保的企業規模。與此同時,于1971年通過了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條例。這樣的舉動主要是因為在國家主導經濟發展時期的所有戰略型企業中,臺灣大型企業在整個經濟中所占的份額較小,經濟生產多由中小型或者小型企業實現,所以為了增加用工的靈活性,還修訂了勞工保險。即便如此,由于這些中小企業多由家族經營,企業的保障機制多由家庭私人內部承擔與消化,由政府負責的福利政策諸如健康保險仍然主要覆蓋對經濟政治穩定有特殊意義的國企職員、公務員和軍人等少數人口,社會福利支出也只占政府總支出的零頭。
由此可以看出,在經濟發展優先的發展戰略主導下,韓國與臺灣的社會福利政策具有鮮明的“選擇主義”特征。這種“選擇主義”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保障領域的選擇,政府主要是根據經濟發展中對勞動力和資金的需要對社會保險項目進行了頒布實施,社會救助和生活救濟方面鮮有作為,認為靠傳統的家庭關系和互助要比國家的救貧政策更加道德和優越;第二,保障人群的選擇,主要表現在韓國對財閥企業員工的工傷補貼和年金項目的首先實施,而臺灣的福利政策主要傾向于公務員、軍人和國企員工的保障。這種選擇帶有強烈的職業劃分,多半是一種職業福利,以工作場所為基礎且不能轉讓;第三,政府的職責有所選擇,韓國與臺灣在社會保障事業的實施和管理中,一個典型的做法是在不同的層次明確劃分政府的有限承擔,包括社會保險金的支付、法規條例的實施與監督等等,堅持除立法外盡量不直接干預社會福利的總思路。
這種“選擇主義”與韓國和臺灣當時的經濟社會狀況相聯,是一種隸屬于經濟發展的必然的政策選擇。韓國和臺灣的社會福利政策制定者大多是經濟學家,他們從西方國家福利政策的發展中得出結論,認為福利保障與經濟增長不可兼得。威權主義政權中福利政策的選擇主義傾向來源于對共產主義和對左派思想(朝鮮和中國大陸)的反對、抑制,在愛國主義的名義下,勞動運動被視為有共產主義色彩的舉動而被明令禁止,同時,威權政府通過與市場緊密的聯合,扼殺了市民社會,很多經濟決策都是在排除勞工大眾的基礎上制定和實行的。[4](169)這種對勞動勢力的排除和市民運動勢力的薄弱阻塞了福利政策產生和實施的完整渠道,福利體系僅僅淪為政府處理其政權合法性的工具。總之,經濟起飛時期的韓國與臺灣必須通過本地區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去完成經濟增長的目標,更為重要的是,威權體制下民主政治的缺位也使得勞工群眾根本無法沖破牢固的資本統治聯盟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所以無論從何種角度看,福利制度的發展在韓國與臺灣都不具備條件。
二、民主轉型中的“普遍主義”
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韓國與臺灣迎來了福利體制改革的新局面。一方面,韓國與臺灣的經濟在原來的體制下獲得了充分的發展,伴隨著經濟發展而來的勞動力成本的變動,就業市場不穩定和人口老齡化問題也逐步顯現,各種矛盾使政府不得不把精力轉移到對社會問題的處理上;另一方面,威權體制內部統治開始松動,政黨政治開始形成,勞工運動逐步興起,企業工會聯盟和公民團體的力量也在發展壯大中。在民主化的浪潮過程中,社會政策無疑成為各方政治勢力關注和爭論的焦點,政府再也無法繼續避開福利體制的發展。
韓國民主轉型和福利政策發展的轉折點是1987年。隨著盧泰愚在6月發布民主化宣言,廣大工人要求經濟民主繼而要求提高工資的呼聲越來越高,同時罷工運動激增,政府為了應對政治危機發表了包括最低工資制、國民年金、醫療保險覆蓋到農村地區在內的“三大保障政策宣言”。[1](12)1988年,最低工資制度和國民年金制度開始施行,醫療保險制度向農村擴展,1989年城市個體經營者的納入使得制度實現了全民覆蓋。這個過程是與政治民主化一起開始的,民眾第一次通過組織化的力量提出了福利制度改革的要求。[1](12)除此之外,這一時期還先后制定了《青少年培育法》(1987年)、《男女雇傭平等法》(1987年 )、《嬰幼兒保育法》 (1991年 )、《雇傭保險法》(1993年)等,且主要集中于社會福利服務制度建設方面。值得一提的是,《雇傭保險法》的制定彌補了韓國四大社會保險中雇用保險制度的缺位。由此,韓國實現了以年金保險、醫療保險、產災保險和雇傭保險為內涵的四大社會保險制度的建構。雇用保險的范圍比失業保險廣,包括預防失業、促進就業、改善雇傭結構和能力開發事業等。到了1995年7月,韓國除兒童津貼外,有關社會保障的核心制度已全部建立。[5](159)另一方面,1987年韓國對《醫療保險法》進行了全面修改,在保險對象中追加了農漁民、微型(單位)職工、城市自營業者,并且規定國家承擔其一部分醫療保險費。[6](24)這比起 1963年和 1976年的《醫療保險法》的保險對象限于大規模企業(單位)職工、由企業承擔保險費、國家承擔運營費和給付的一部分的規定有了很大進展,即彌補了《醫療保險法》的弱點,使得醫療保險制度更加具有普遍性。其后,韓國政府在1988年1月開始落實農漁村醫療保險,1989年7月開始落實自營者醫療保險等;到 1989年7月,將醫療保險擴大到城市與農村人口、公共部門與私營經濟部門人員、普通人與生活困難者。由此,即醫療保險實施12年之際,韓國迎來了全國民醫療保險時代,所有國民依靠健康保險和醫療給付得到了醫療保障。1998年,韓國政府實現了民主政治政權的交替,金大中政府完成了健康保險制度內部的合并調整,隨著《國民健康保險法》和《國民基礎生活保障法》的頒布實施(表一),韓國的福利體制開始由全面保障全體公民就業、健康和生活的各個層面,由威權時代的“選擇主義”向“普遍主義”發展,韓國政府開始強調福利政策中國家的責任,公民作為權益人的權利得以凸顯。

表一 金大中政府的福利政策進展
與此對應的,臺灣地區在 1987年解除了戒嚴。隨后,伴隨著民間團體和民進黨的成立,長期執政的國民黨受到嚴酷考驗。為了穩定人心繼續維持政權合法化,國民黨對于島內社會的福利制度采取了積極態度,在20世紀80年代末集中建立了新的社會保險制度,包括農民健康保險條例(1989)、少年福利法 (1989)、基層干部健康保險(1989)、低收入戶健康保險 (1990)等等,同時“行政院”也開始規劃全民健康保險。這一階段的社會政策有消音和安撫人民的作用,使得臺灣的社會福利立法初具雛形,也是首次將健康保險的福利項目向農民和低收入家庭延伸。隨著不斷的社會抗爭和民進黨的競爭,執政的國民黨已不再能夠單獨主導社會福利政策。從90年代開始,臺灣當局進行了社會保障制度的重大改革:一是建立了“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使臺灣地區的社會保障體系趨于完善;二是完善失業救濟制度,最終于1999年建立了失業保險制度;三是研擬“國民年金”制度,并已經完成規劃;四是完善養老保險制度。1995年,臺灣在全島實施“全民健康保險”制度,逐步減少或合并了既有的多種保險制度,建立起統一的醫療保障制度。該保險把面向勞工的各種醫療服務項目有效地組合起來,分別放置于勞工保險與公務人員保險之下,并為自雇者、非正式部門員工和農民提供了融資安排。1998年7月,內政部召開“第二次社會福利會議”,會議通過決議承諾提升社會福利行政層級以及逐步增加社會福利預算。[7](51)在 1990-1999年期間,臺灣經歷了社會福利發展的“黃金十年”,這十年新立的法和修正的社會立法比過去四十年還要多,其中包括關系到社會福利輸送體系的民營化走向。[7](52)2000年臺灣經歷首次政黨輪替時期,民進黨在處理失業率的同時建立起就業服務的多項法案,包括就業保險、大量解雇勞工保障、原住民就業保障以及兩性工作平等法。總體而言,臺灣的社會保障體制已經基本擺脫了之前“軍公教福利國”的“選擇主義”色彩,社會福利保障的領域從此前的社會保險向社會救助和公共服務全面發展,保障人口逐漸增多且越來越向勞工和弱勢群體傾斜,而且如表二所示,政府用于社會保障的經費也逐年增多,若以社會福利支出占國民生產額的比率來看,1981年是 1%,1986年提高到 1.5%,1991年升高到 2.5%,1996年達到 3.9%,2001年則突破了 4.1%,[7](411)福利體制在“普遍主義”趨向中得到逐步深入和完善。

表二 政府在各項事業中的支出百分比(1960-2001)
由上可知,韓國與臺灣在經歷民主化轉型之后,其福利制度由“選擇主義”逐步向“普遍主義”轉變。所謂的“普遍主義”,就是指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政治民主化過程的開展,政府更加注重福利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并更加全面地關注人民的生活質量。相較于威權時期的福利政策的“選擇”,“普遍”的含義就是向更多的領域保障,保障更多的人口以及政府在福利體制的運作中承擔更廣泛的責任。更重要的是,這種“普遍主義”融入了福利政策運作中公民權利的概念,使民眾的需求通過政治參與的形式表現出來,回歸于福利政策的社會本質,可以說,“普遍主義”體現了福利政策和體制的完善和成熟。
三、民主因素與福利體制的發展
在韓國與臺灣,政治民主化影響社會福利發展的途徑,主要通過下述三種方式進行:
第一,政黨政治的運作。反對黨以社會福利為訴求,借以爭取選民選票,執政黨必須在政策與福利實施上及時回應,以確保執政地位與政權的合法性。所以,政治民主化擴張了民眾的票選權利。[8](50)金泳三和金大中的政府與盧泰愚政府最大的不同點就在于,政府試圖改變國家和資本直接的統治聯盟而試圖建立一個包括勞工和平民在內的更加開放的聯盟。特別是金大中政府,無論從政策的引進還是實施過程都廣泛地獲得了社會的共識,從而迎來了一個全民福利的時代。[4](180)伴隨著一系列勞工保險范圍的擴大和健康醫療項目惠及所有國民,一個全面的福利體系建立起來,社會保障的范圍大大擴展,同時,政府還關注弱勢人群諸如老年人、殘疾者、單身母親等的生存狀況,改變了傳統福利思想中由家庭承擔的格局。而臺灣的民進黨也是由于其福利政策而受到關注和認可,[9](6~121)其推進社會福利建設的努力首先是通過自身制定福利政策,例如在 1991年由民進黨中央黨部組辦的“全國民間經濟會議”上,臺灣學者們融入歐洲的社會權觀念提出建設“福利國”的主張;其次便是通過政黨之間的競爭迫使執政的國民黨改變或者加速社會福利的發展,1995年國民黨比計劃中早五年引入了國民健康保險便是最好的說明。
第二,復雜多變的工會運動和對立抗爭的勞資關系,間接影響到政權的合法基礎,執政黨為此也必須在有關勞工福利政策上妥為回應,借以降低因工會運動和勞資關系而可能導致的對政權合法基礎的威脅。金大中政府設立了“勞資政委員會”,使得在民主化以后也仍然受到壓制的勞動勢力獲得合法的地位,在韓國政治領域得以作為一個重要的元素出場。尤其是設立于資政委員會中的“社會保障小委員會”與“雇傭失業對策小委員會”,討論了來自勞動者一方要求解決經濟危機所造成的大量失業現象的政策性要求,并將其反映到實際的福利改革中。臺灣自民主化以來,勞工組織聯盟在與民進黨的聯合中開始逐步要求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在此過程中,工人階層已經不再局限于過去對現有制度的“緘默”與“忠誠”,而開始選擇表達自己的“聲音”。這意味著工人開始意識到他們在社會生活中的不平等地位,并開始動員自身的力量來爭取更好的生活。1999年初,為了應付不斷惡化的長期失業問題,勞工委員會建立了一項失業和津貼的項目,并于 2002年使政府通過就業保險法案,把失業保險從勞工保險中獨立出來。
第三,民間各種團體和運動的興起。韓國方面,這些工人團體和倡導聯盟雖然不是改革的最初發起者,但也是其活躍的推動者。這些組織在威權時代無法將其訴求表達出來,但并不影響他們一直對福利體制普遍主義的堅持和倡導。民主化時期,這些常由工人代表和政策專家組成的聯盟有著連貫的政策理念和來自基層官僚的社會支持,他們于 1994年提出了國民健康保險的整合議案,包括將養老金覆蓋面擴大到城市自雇者,同時拒絕對現存方案的文過飾非。對處方權和配藥權的分離,將多個醫療保險協會整合為一,就業保險領取資格的放寬和覆蓋面擴大,進而通過一項新的社會援助法案。[10](115)1998年,這些組織成功地在金大中政府中獲得了關鍵的席位,從而在2000年有能力實現韓國國民健康保險的整合。臺灣地區由各種弱勢人口所組成的團體,如殘障聯盟、婦女救援協會,以及民意代表所組成的次級問政團體,都提出了對社會福利強有力的訴求,這一方面啟迪社會大眾關注弱勢人口,另一方面則形成對政府社會福利政策的壓力。另外,各種基金會和政策研究中心的興起,其研究關注的焦點之一即為社會福利,如二十一世紀基金會、張榮發基金會、國家政策研究中心、厚生基金會、民生基金會、臺灣研究基金會等[8](51),其所發表有關社會福利的研究報告或是政策建議,對政府制定社會福利政策發揮了很大影響。
如今,韓國與臺灣都完成了社會保險的普遍覆蓋,社會救助和生活保障項目也在持續制定和實施中,威權主義時代按職業分類的福利項目也已相當普遍,不同職業類別的群體之間的差別幾乎沒有實質意義。不能否認經濟結構的改革對這種發展起到的重要作用,但容許社會按照經濟發展的需要來進行制度設計卻離不開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那便是競爭政治的缺位。這一前提的轉變有著重要的含義,在韓國和臺灣的例子中,民主化進程及隨后的民主鞏固時期之所以關鍵,是因為這使得社會政策的制定過程更為公開、更加多樣化。民主轉型顯著地改變了“政治游戲的規則和利益相關者的范圍”,[11](74)從而顯著改變了韓國與臺灣的福利體制發展。
結 論
胡伯(Huber)和斯蒂芬斯(Stephens)曾指出,一個國家想要得到發展,就需要在其生產體制和福利體制之間建立起某種明確的連接。同時,不同生產制度的國家往往在應對經濟挑戰時會采取不同的社會政策改革。而且,這種連接不是自動生成的,而是依賴于其間的政治變遷。[12](45~107)在韓國與臺灣福利體制發展的過程中,經濟政策和結構的變化與社會政策的制定之間的聯系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經濟層面的調整對福利體制的影響是間接的,必須通過勞動力市場和就業體系發生作用。就韓國與臺灣而言,在威權體制下,經濟自由化給福利政策帶來的變化始終是初級且緩慢的,福利體制的發展主要得益于政治民主化。韓國與臺灣福利政策從“選擇主義”向“普遍主義”轉化的過程,一方面是經濟發展、生產結構、勞工老齡化以及后工業化時代帶來的后續影響所致,更為重要的是,社會政策的改革通過民主政治的途徑得以開展,將公民團體與組織的訴求融入到福利政策的制定之中,建立起一個廣泛的社會共識。這種影響是根本性的,因為經濟結構只會秉承經濟優先的傳統從而遏制國家的社會責任。而民主,即民眾政治參與一直是福利制度得以發展的關鍵因素,福利體制的成熟與穩定需要民主因素的配合,才能達到經濟發展、政治民主和社會包容互相權衡和共生的理想狀態。
[1][丹 ]考斯塔·埃斯平-安德森編:《轉型中的福利國家》,楊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
[2][韓 ]金源明主編:《韓國社會保障論爭》,(韓 )金炳徹,(中)陳倩譯,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10年。
[3]MichaelHilland Yuan- shie Hwang,“ Taiwan:wthat kind of social policy regime”,in Alan Walker and Chack- kie Wong(ed.),EastAsian Welfare Regimes in Transition:From Confucianism to globalization,Bristol:The Policy Press,2005.
[4]Sang-hoon Ahn and So-chung Lee,“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uth Korean welfare regime”,in Alan Walker and Chack-kie Wong(ed.),East Asian Welfare Regimes in Transition: From Confucianism to globalization,Bristol:The Policy Press,2005.
[5]鄭秉文,方定友,史寒冰主編:《當代東亞國家、地區社會保障制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
[6][韓 ]金鐘范:《韓國社會保障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7]林萬億:《臺灣全志 卷九社會志-社會福利篇》,臺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6年。
[8]臺灣省政府新聞處編印:《臺灣光復五十年:社會建設篇》,民國八十四年。
[9]Lu, A. Y.- L. `Political Opposition in Taiwa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in T.J.Cheng and S.Haggard(eds)Political Changes in Taiwan. London: Lynne Rienner.1992.
[10]Kim Y.M.Beyond EastAsian welfare productivism in Korea,Policy&Politic,36(1),2008.
[11]Peng I,Wong J,Institutions and institutional purpose: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East Asian social policy.Politics and Society,36(1),2008.
[12]Huber E.and J.Stephens,`Welfare State and Production Regimesin the Era of Retrenchment',in P.Pierson(ed.)The New Politics of the Welfare Stat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