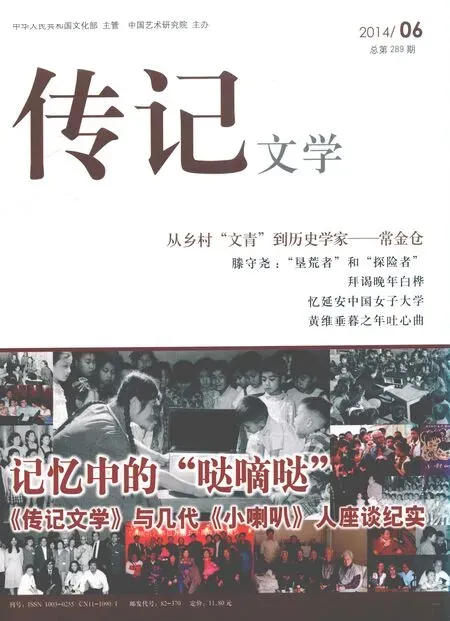拜謁晚年白樺
張夢陽
拜謁晚年白樺
張夢陽

2013年9月27日下午,本文作者張夢陽(左)拜謁白樺先生時合影
有人說,詩人不會老去。50年前我就讀北京二中時,在韓少華老師小書房里,見到一本署名白樺的敘事長詩集,是描述賀龍元帥的,激情洋溢,充溢詩性藝術。其內容雖沒有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但一個年輕詩人閃光的名字,卻永遠留在我心中,永遠不老。
上世紀80年代初,內部放映一部電影,片頭字幕上,赫然又出現了白樺的名字。那影片中反映出的“詩性精神”使我直感到:作者絕非是寫賀龍故事的白樺了!經過“十年浩劫”的反復淬火、錘煉,白樺已經變得思想超拔深刻,對歷史充滿了質疑與思辨。影片最后在雪地上劃的大問號,在我心中烙下深痕,30年來難以忘懷,越來越激起我的沉思。
電影票是協助劉再復先生為周揚起草紀念魯迅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報告時得到的。再復讓我前往和平里給李澤厚先生送去一張,因此有機會與澤厚先生一起觀看。電影結束后,我問他對影片感覺如何?他很謹慎,只說“導演很棒!”而導演彭寧恰恰是我的朋友,我們是在1966年8月他被打成反革命時結識的,那時候北京師范大學南邊不遠的北京電影學院墻上貼滿了批判彭寧的大字報。什么“彭寧是茁壯的修正主義苗子!”“徹底批判彭寧的成名成家思想!”甚至于“打倒彭寧!”“砸爛彭寧狗頭!”的話也上來了。我們在這些大字報下面長談了很久,以至電影學院表演系一些漂亮又天真爛漫的女大學生不斷投來警惕的眼光,以為我們是在搞“反革命串聯”。這樣,反倒使我們的友誼更加親密,不時面晤談天,他去長影之前,我和另一位朋友還在東單一家飯館請他吃飯。我把澤厚先生對電影的評價托人轉達給彭寧。據說彭寧知曉后非常高興!在人生低谷中聽到別人的贊揚,尤其是李澤厚這樣的大美學家的稱贊,其受到的鼓舞是不言而喻的。令人嘆惜的是彭寧這位天才的電影導演藝術家,身后唯留下這部影片,未公開放映,就遭到無情批判。
澤厚先生說“導演很棒”,其實也暗含著對編劇的肯定。白樺這個名字,也引我深深景仰。每當從報刊書籍或傳媒視頻上見到他,就格外注意。印象較深的是,一次他曾說歷史上無數帝王將相、富豪巨紳都成了冢中枯骨,無人記起;而那些真正的詩人、作家的優秀作品卻始終不朽,永垂青史。再一次是從電視上看到他的“粉絲”——日本女影星“真由美”,熱烈地擁抱他,親切地依偎在他的臉頰上,也令人覺得圣潔,絕無褻瀆之感。
而最使我震撼的是從2009年11月19日《文學報》上讀到他的驚世之作《從秋瑾到林昭》。我一遍又一遍地細讀著這部熱血和生命凝結成的詩篇,心潮起伏,難以自制,立即給《文學報》副總編輯陸梅女士發了一封郵件,說:“這是20世紀以來中國新詩史上的偉大篇章,也是中國人精神覺醒、理性發達的標志。白樺先生80歲時,因此詩,從優秀走向偉大。”陸總編將此話編入了2009年12月31日《文學報》第2版的《我們的獨家報道》。
在《從秋瑾到林昭》的激勵下,我終于在2013年早春,將醞釀近40年的敘事抒情長詩《謁無名思想家墓》寫出了。8月,詩作印出,托友人轉贈白樺先生一本,9月2日就收到他的回復:
夢陽先生:大作經建智先生轉寄,已收到,拜讀。先生多思,激情洋溢,十分可敬。我還要細讀。腰傷,三個月未寫一個字。九月如能粗安,一定歡迎舍下一敘,安好!
白樺 上2013.9.2
正好我9月22至25日到上海出席魯迅研究學術研討會,散會后特為拜謁白樺先生滯留兩天,27日中午后,即和友人一起去往白樺先生的江寧路居所。
這是上世紀60年代修建的老式宿舍樓,著名大導演謝晉也曾住在這里。進門上電梯到了七層,走到六號居室門口,門開了,白樺先生已經在等候,我躬身握住白先生伸來的手。啊,這是一雙蒼老而又溫暖的手!有一股熱流傳至我心中。這是一位真正的詩人才有的傳感,因有了它,人性的表現和對生命的最高認識,才成為可能。就在這瞬間,又抬頭注視那滿頭的白發,溫存的眼睛,無不蘊含哲人的深邃、睿智,又透發出一股純真的樂觀與天真!不禁驚嘆戴逸如先生的白樺畫像,真太像了!形神兼備,畫如見人,人如看畫!
進屋,是很普通的小三居室,簡樸而陳舊,沒有任何現代化設施。客廳是最大的一間,里面十分溫馨,布置盡顯主人的性格、愛好與修養。
迎面映入眼簾的,就是白樺夫人著名電影演員王蓓年輕時的銀幕照片:《幸福》《飛刀華》《馬蘭花》……她在其中比當下最秀美的女星還秀美,最清純的少女還清純。這些照片一幅幅亭亭玉立地站在櫥柜迎門處,以美麗的微笑迎接客人。這表明詩人白樺一生始終不渝的追求與默默不停寫了一年求愛信的癡情,經久不衰,愈老愈是熾熱。
往中間望去,是《鏡頭里的巴金》攝影集的封面,巴老的側影顯示出“巨匠的風采”,也展示了主人心中的楷模。
靠近巴老的是詩人白樺的黑白照片,依在《魯迅全集》書脊前。照片上的白樺已是老年,銀絲飄逸,有如他奔放的詩章。有魯迅和巴金作后盾,怎能不堅實而韌長?
朝上一格望去,是一尊青年白樺的銅像,長發后披,激情澎湃,富有浪漫色彩。見到這尊銅像,就想見青年詩人給他心愛的姑娘持續寫信時的模樣。

白樺先生
視線移到墻角,見書柜玻璃上插著一個孩子稚嫩、拙真的字:“我愛爺爺。”旁邊緊挨著一幅童畫:站著的大豬和身前的小豬。
白樺先生看到我在注意孩子的字、畫,開心地笑道:“是我小孫女寫的,畫的。”立時盡顯詩人爺爺對小孫女的無限深情,這爺倆是互相愛著啊!
甫坐定后,我站起身將簽好名的新書:長篇小說體魯迅傳《苦魂三部曲》之一《會稽恥》《中國當代文學百家·張夢陽散文精品集》《中國魯迅研究名家精選集·魯海夢游(張夢陽卷)》和敘事抒情長詩《謁無名思想家墓》一一送到白先生手中。白先生點著頭,鄭重地一一接過,小心翼翼地放在書柜上。
我又拿起刊登《從秋瑾到林昭》的2009年11月19日《文學報》,詩句間密密麻麻劃著紅線,報頭上寫著讀后感:“驚天地、泣鬼神之作!” 白先生看見后不禁驚嘆。我知道,他是為有這樣認真的讀者而感到由衷的高興!我為受到他的驚嘆而興奮不已!感奮地說:“我不知讀了多少遍。臨來前又讀了一遍,一遍有一遍的感受,越來越深入,百讀不厭。臨來的一遍是對林昭的驚人發現深有所感,她發現‘大多數中國人的眼眶里都沒有眼珠’。‘沒有眼珠’,就是盲目,看不到事物的真相,對眾多的奴化現象熟視無睹。這真是入木三分!如魯迅先生所說中國人常常‘不悟自己之為奴’。”白先生傾耳細聽,點著頭。
我又拿出2009年12月31日的《文學報》,大聲朗誦稱他“從優秀走向偉大”的話。他謙虛地擺擺手,像在說“不敢當”,但又為自己的詩得到人們的理解而喜悅,走到外屋,拿進兩本嶄新的書:《長歌和短歌》與《藍鈴姑娘》。坐在書桌前簽好字,遞給我。我鄭重地接過,說:“我從刊登《從秋瑾到林昭》的同期《文學報》上知道這兩本書后,跑遍了北京各大書店,都沒有見到,又在當當網上查尋,還沒結果,這下在您作者本人這里得到了贈書,欣喜至極!”
白先生笑笑說:“這兩本書是不進書店的,所以買不到。但已經再版了兩次,重印了三次。別人出詩,都須付費,出版社不僅不用我付錢,還付給我稿費。”
我說:“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詩不用吆喝,自然有人搶讀。那些趨炎附勢的‘馬屁詩’,倒給錢,像侯躍華和郭達的小品說的:‘聽一句給十塊錢’,我也不屑一哂。”
大家都笑了。
我扶他在書桌前的椅上坐下,自己也坐在旁邊的沙發上,一下子就成了無話不說的老朋友了。我開門見山,提起了上世紀80年代他編劇的那部電影,說影片的導演彭寧是我的朋友,并講了李澤厚先生看過電影后稱贊“導演很棒”的話,嘆惜彭寧僅留下這一部影片就英年早逝了。白先生沉默了一會兒,看出他內心的悲痛。好一會兒,他才嘆口氣說:“彭寧后來又導了一部電影,可惜仍然不能公映。”
“您編劇的那部電影,現在看來并沒有什么,完全可以重新上映嘛!”有朋友說。
白先生笑笑,卻說:“這由不了我們。”
我領悟了白先生的深意:他已經不只是一個浪漫的詩人,而是在滄桑風雨的反復吹打、磨練中成熟了,鑄煉成一位老練、深刻、明了世情的智者加詩人。
是的。白樺是哲性的詩人,詩性的哲人。他將經過漫長摔打、錘煉、磨礪而形成的歷史叩問與哲學反思滲入詩,又將詩性融進電影、話劇、小說、散文等各種文體,以詩性精神來表現歷史叩問與哲學反思。這種獨特的風骨在20世紀80年代那部電影中肇始,由21世紀前十年奉獻的《從秋瑾到林昭》推向高峰,使白樺成為中國當代文壇孤絕綻放的空谷幽蘭。
話歸本行。又談起那部電影,白先生像是沉浸在詩性的回憶中,動情地說:“那是部詩電影。劇本全是分行的詩。”
我說:“即使不能公映。劇本總會有出版的機會,我盼望看到詩人所寫的‘詩電影’腳本。”
白先生會意地笑了。
此時,有朋友送給白先生一本日記體新書。于是我們又轉到日記體的話題。
我說:“寫《小兵張嘎》的老作家,河北人民出版社要出他從40年代到現在的日記,足有上千萬字。那作家叫徐什么……”忽然想不起這位作家的名字了。
白先生敏銳地說:“徐光耀。”
我立即點頭稱是,驚道:“白先生84歲了,記憶力還這么好!”
白先生說:“徐光耀曾是我在總參創作組時的同事。”又說,“日記可能比創作更有價值,因為反映了歷史的真實。可惜我從1954年批判胡風起就不敢再寫日記了。因為那時的‘小人’,會偷看你的日記,抓住幾句話就可以把你打成反革命,置于死地。‘小人’于是去邀功請賞。人世也變得越來越險惡。”
聽了白先生這段憂憤深廣的話,大家又陷入深深的沉默……
這時,白先生夫人王蓓來了,她坐在靠門的椅子上。我觀察著王蓓的氣色,見她雖已年過八旬,仍然清瘦、俊朗,欣慰地說:“您當初清純、美麗,現在依然美麗。”
王蓓聽了很高興,連說:“謝謝!謝謝!”
不覺兩個多小時過去了。白先生起身催促:“走,吃飯去!”說著,戴起一頂淺黃色的鴨舌帽。我好奇地問帽子是什么料的,他笑笑說:“是藤編的。”
我走近細看,見確實是藤編,是很細的藤子,有如細細的銀絲,和白先生的銀發融為一體,也許更為光燦。一路走去,望著身旁這樣的一位詩人,我總覺得,我們應該引他為驕傲,因為他筆下噴出的真實的詩,是生命不息的火焰。
責任編輯/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