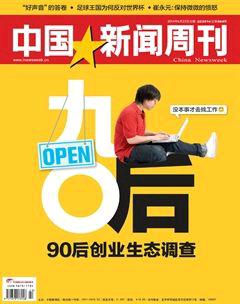亞洲地緣政治與美國再平衡戰略
何亞非

美國2009年宣布“轉向”亞洲,2011年公布亞洲再平衡戰略,并采取了一系列行動和戰略部署。這不僅打破了亞太戰略均衡,更是給中國的安全環境增添了復雜因素,成為中國在制定對外戰略尤其是建設自身安全能力時不得不考慮的重要因素。
美國學者對亞洲再平衡戰略做過這樣的解讀:“(美國)再平衡戰略意味著調動各種資源和伙伴關系來抵消任何可能的挑戰”;“今天美國對華政策的首要目標是維持美國在亞洲的優勢地位”。無論是維持優勢地位還是抵消挑戰,奧巴馬總統日前訪問亞洲四國、美國防部長哈格爾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上就釣魚島和南海問題針對中國咄咄逼人的表態,都表明美國將堅持推行以中國為主要目標的亞洲再平衡戰略,并不惜為此動用各種資源,包括在西太平洋聚集美60%的海空軍戰略力量。
當然,也有不少專家包括美國學者認為,美國現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中東、歐洲和亞洲是美三大戰略投入重點,前兩者依然局勢錯綜復雜,尤其是中東地區的“阿拉伯之春”已經演變為“阿拉伯之冬”,美國沒法也不愿就此脫身。
但是美國亞洲再平衡的客觀結果是,東盟國家陷入“經濟上依賴中國、安全上拉住美國”的怪圈;日本政府借此極度右轉,在釣魚島等問題上不斷挑戰中國的底線;中國的個別鄰國也乘機在海洋權益上肇事生非;美國則走入“經濟上與中國發展關系,安全上牽制、遏制中國”的雙軌,軟硬兩手并使。亞洲形勢負面因素增多與美國的亞洲再平衡戰略有密切的關聯。
美國作為一個利益遍布全球、希望維系世界霸權的守成大國,需要考慮如何與其他大國尤其是中國打交道,調整和改革全球治理體系,包括安全治理體系,使之適應地緣政治和經濟變化的現實。其他國家也有一個逐步適應不斷發展壯大的中國的過程。而作為一個全球利益不斷拓展的新興大國,中國在被國際體系接納、認可的同時,必然會遭到一些成員的猜疑和恐懼。對此不必大驚小怪。中國應該考慮如何提高自身全球安全治理能力、突破上述“安全困境”、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這才是中國面臨的緊迫課題。
這就是說國際社會成員大家都需要“安全感”,必須根據形勢的變化做出相應的調整,彼此適應。只找自己的安全感,而不顧別人是不是安全,甚至以損害他人的安全來換取自己的安全空間,其結果往往適得其反。
從中國與世界的聯系看,中國已經從各個方面緊密地融入國際體系,在過去幾十年里完成了從革命者、批判者到認同者、融入者的“華麗轉身”。
2013年,中國約有9000萬人次出境,已有2萬多家企業遍布近200個國家。當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27.76%,對亞洲經濟增長貢獻超50%。中國還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派出維和部隊人數最多的國家,是發展中國家維和經費攤款最多的國家。為支持非洲的和平與安全,中國向馬里派出成建制的維和部隊。為幫助非洲“重建更加公正、平衡、團結和道義的全球治理體系”(前非盟秘書長讓·平語),中國發起中非和平安全合作伙伴倡議,援助非洲整體維和能力。目前經常接受中國援助的國家超過123個,亞洲和非洲占中國對外援助的80%。1993年中國與巴西建立首個戰略合作伙伴關系,迄今已與50多個國家和地區組織建立了類似關系。
這些例子充分說明,中國在全球安全治理及其機制建設中扮演著積極和引領的作用,是全球安全體系的參與者、建設者和維護者。中國這樣積極、進取的安全維護者角色顯然與身陷上述“安全困境”是矛盾的。這樣的矛盾雖然說是特定歷史階段所特有的,但對中國確實也是不公平的。
中國在全球尤其在周邊地區有自己合情、合理、合法的安全利益和訴求,中國不會把自己的要求強加給他人,也不接受別國強加給中國的要求。要實現國際、地區和平與安全的目標,就必須兼顧中國和其他國家合理的安全訴求,減少乃至完全排除造成“安全困境”的種種現實和潛在的問題。這道難題現在已經擺在各國面前,無法回避、無法推遲了。
不妨可以考慮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一、認清亞洲地緣政治利益的現實與未來,逐步構建兼顧各方利益的亞洲安全框架。
亞洲地緣政治的近代歷史,簡而言之是西方列強以戰爭、殖民、結盟等方式逐步取代以中國為中心、自然生成的“朝貢體系”,最后形成美國控制的地緣政治大格局。
近年來,亞洲地緣政治與全球同步出現多極化趨勢,其中突出的是中國和其他新興國家的崛起、俄羅斯的復興、日本強硬推行“國家正常化”、美國實力和控制力的相對下降。
目前亞洲沒有切實的安全框架,或者說安全秩序是混亂、無序的。除了美國與日本、菲律賓、澳大利亞、韓國等雙邊軍事同盟,尚無涵蓋亞洲的地區安全平臺和機制。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主要是經濟論壇;東亞峰會也是論壇,雖然討論的問題范圍較廣;東盟地區論壇以討論安全議題為主,沾了一些安全的邊,但依然是論壇,而且級別不夠高。目前,迫切需要地區主要國家和東盟等區域組織在照顧各方利益基礎上,探討建立亞洲安全機制和框架的現實方案與路徑。由易及難,由小及大,“摸著石頭過河”逐步建立信任,搭建命運共同體。
美國的亞洲再平衡戰略是亞洲安全框架的最大變數。雖然美國學者曼寧等認為,這個戰略是防御性的,主要是應對中國崛起后地區安全格局的變化,并非著眼于遏制中國,但是它本身極具進攻性,就是想把美全球軍事資源調集到亞洲,并通過加強美與日本、澳大利亞、菲律賓、新加坡等盟友關系以及與越南等國的軍事聯系,來“抵消”中國在地區日益增長的經濟、政治、軍事影響力。
美國亞洲再平衡戰略起碼存在四點負面影響:1.增大中美的戰略猜疑;2.削弱中美在全球性問題上合作的積極性;3.美國的手伸得越長,安全義務就越多,將不堪重負;4.增加中美直接軍事對抗的幾率。
澳大利亞學者懷特最近撰文指出,美國要學會在亞洲與崛起的中國分享權力,因為美國想長期維持在亞洲的優勢地位既不現實,代價也太大。中國的發展是阻擋不住的。但是美國國內新保守主義的能量依然很大,其對崛起大國的本能反應就是加大競爭與遏制,防止后者的強大。這種沖動很難遏制。這從美國對中國領導人提出的“建立新型大國關系”反應冷淡可見一斑。
二、繼續做大經濟合作的“蛋糕”,結成亞洲經濟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
雖然說國家間經濟高度相互依賴未必一定會導致和平、安全的局面,但是要實現亞洲的長治久安,沒有經濟高度融合的利益共同體做基礎,那就一定是空中樓閣。
這方面亞洲已經走在世界前面。東亞是全球經濟活力最強的地區,21世紀是亞洲的世紀。亞洲內部貿易目前已超亞洲外貿總額的50%,中國與東盟新的鉆石十年已經起航。中國領導人去年提出與周邊國家共同建設海上絲綢之路和絲綢之路經濟帶,是建設區域治理的頂層設計和加強區域合作的綜合性舉措。正在籌建的亞洲基礎設施銀行就是其中一項重要措施。對于亞洲的經濟合作,也需要美國、俄羅斯、歐洲等域外國家的積極支持、深度參與,因為亞洲經濟是開放的、與全球經濟緊密聯系的。
三、擱置爭議,穩妥處理主權和海洋權益爭端,走出一條“非冷戰、非熱戰”的和平競爭、和平共處之道。
習近平主席最近訪問歐洲時多次公開表示,中國沒有國強必霸的基因。中國歷來愛好和平,也十分希望有一個穩定、和平、安全的周邊環境,以更好地發展自己。中國的發展成果將惠及周邊各國。中美經濟“你中有我、我只有你”,中國的發展是美國的福音,正如中國衷心希望美國經濟迅速復蘇一樣。光中國對美國國債的投資就超過2萬億美元。中美之間無疑是利益共同體。
由于歷史的原因,亞洲存在一些主權、海洋權益、島礁權益爭端。這是事實,無法回避,也不需要回避。過去幾十年大家大多相安無事,現在矛盾卻集中爆發。為什么?這需要深入思考。
日本想打破現狀,推翻二戰確立的全球和地區秩序,不僅做不到,反而可能重蹈覆轍。安倍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會上稱,新日本人與其父輩、祖父輩毫無二致。這話就很危險,說明安倍及其政府根本沒有認識到日本在二戰中給亞洲各國人民特別是中國人民帶來的巨大浩劫。不反省歷史、汲取歷史教訓,那一定會犯錯誤。
中國領導人多次強調,中國無意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霸權。中國的發展及其利益的拓展是互利、和平的,中國希望和平發展,也希望別國和平地發展。新興大國的崛起是會對現存大國構成挑戰,但顯然中美沒有地緣政治利益的直接沖突,沒有理由不和平共處、和平競爭。
只要各國能充分考慮和照顧對方的地緣政治利益,充分尊重歷史,沒有什么問題是解決不了的。暫時不能找到解決辦法,也可以將爭議擱置起來,留待以后再議。現在可選擇一起商量,共同開發有關資源。說到底,亞洲的和平取決于,地區各國和域外大國對各自的地緣政治利益有恰如其分的認知,并做出相應的調整。
(作者系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