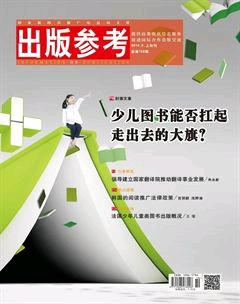倡導建立國家翻譯院推動翻譯事業發展
朱永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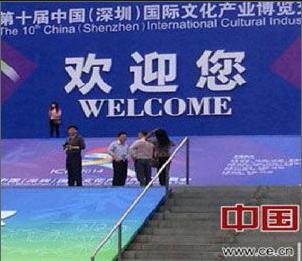
自1978年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翻譯在我國政治經濟文化建設中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及時積極翻譯引進的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社會科學以及人文學科的研究成果,在我國30多年的迅猛發展中,居功至偉。毫無疑問,在今后中國進一步強大、發展的過程中,翻譯上的“文化輸入”將會起到更多更大的作用。
而站在國家戰略的高度,將中國最新的學術成果傳播出去,不僅關乎中國的國際形象,提高我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還能增進外界對我國歷史和現狀的深入了解,從而消除西方主流話語中存在的誤會甚至敵視的聲音。2012年初,《國家“十二五”時期文化改革發展規劃綱要》對翻譯人才培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也體現了站在國家戰略上對翻譯的高度重視。然而,三個因素嚴重制約了我國翻譯事業的進一步發展:
第一,我國尚無以翻譯的“文化輸出”和“文化輸入”為使命的國家級機構。雖然國家高度重視翻譯,也成立有諸如中央編譯局這樣的機構,但其主要任務是編譯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翻譯黨和國家重要文獻和領導人的著作。
第二,目前我國的翻譯態勢主要以市場為導向。從“輸入”來說,在引進上主要以國外流行的熱點為翻譯依據,有時候忽略了在科學技術、社會科學以及人文學科領域中成果的經典性與當代價值。從“輸出”來說,在中國文化傳播上雖然進行了一些努力,但十分零散,后繼乏力。比如這些年國家社科基金設立了中華學術外譯項目,支持力度也很大,可是無論從規模、整體思路以及推薦內容的選擇上,都還未能發揮重要的作用,而且受到研究課題的形式局限,在未來也較難發揮更大作用。
第三,全社會對翻譯事業的宣傳不多,理解不夠,重視不足。在我國,由于“重原創、輕翻譯”,致使翻譯地位較低,翻譯稿費與翻譯付出的勞動相去甚遠,導致翻譯家難以獲得獨立的生存能力,因此,除了以翻譯流行作品為主的翻譯家外,像已故的傅雷那樣高水平的專職翻譯家已近乎絕跡。由此造成的翻譯上的空缺,是由很多水平不高的翻譯人員來填補的,導致翻譯質量下降,粗制濫造的翻譯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可謂屢見不鮮。
與此同時,國外對翻譯及其研究、文化及其傳播卻極為重視。法國一向以重視翻譯而著稱。2009年,法國駐中國大使館專門設立了以我國著名翻譯家傅雷為名的傅雷翻譯出版獎,震驚了國內翻譯界、出版界。德國的歌德學院繼翻譯資助項目之后,也在2013年啟動了翻譯工作坊,分別以哲學、文學、歷史、藝術、音樂等學科類著作的德譯中工作為研討主題,為熱愛翻譯的年輕學子提供學習和溝通的平臺。同時,愛爾蘭、瑞士等國家還有專供譯者入住的翻譯基地,讓譯者可以在一段時間內全身心投入工作,不受其他事務的打擾。美國筆會組織PEN每年資助多位譯者從事文學翻譯,該基金成立10年來,已經資助了70多位譯者。
由此可見,我國成立兼具翻譯與研究功能為一體的“國家翻譯院”,迫在眉睫。
1.成立國家翻譯院,便于統籌完成以下三大使命:一是將國外最新最好的科技成果、人文社科方面的成果及時地引進來;二是把我國最新最有價值的學術成果、文化產品有意識地及時翻譯介紹出去;三是兼具翻譯研究和培養翻譯人才的功能。
在人才儲備上,短期而言,可采取全球招聘的方式,吸引世界上相關頂尖翻譯人才,保證翻譯作品的質量與水平。團結海外的翻譯家和漢學家,為他們提供學術支持和服務,也拓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渠道和范圍。長期而言,整合國內的翻譯人才隊伍,進行專業培養。
在學校建設上,短期可以現有優秀高校為依托,將其設立在高校中,利用現有高校的學術資源為相關工作提供先期的充分準備,及時有效地促進此項工作盡早啟動并快速進入運作狀態。長期可規劃興建為獨立院校。
除此之外,國家翻譯院還應統領全國翻譯事業,收集、整理、提供真實、權威的翻譯人才信息,提供第三方查詢認證,為國家重大對外項目、國際交流與合作、國際貿易等提供高質量的翻譯人才支持;為國家相關職能部門提供翻譯人才隊伍動態、供需等基礎信息;適時開展面向社會的商業化人才供需對接和人才政策咨詢服務。
2.提高翻譯人才的社會地位和生活待遇。在中國的學術評價機制中,有一種約定俗成的慣例,那就是在考量學術成果時只認可原創作品,“翻譯不算成果”成了學術評價慣例。其實,優秀的翻譯,是一種再創造。翻譯工作也是一項原創性很強的活動,好的譯作融入了譯者在該領域內的研究成果,體現了其專業素養。因此,重要名著及學術理論著作的翻譯,應當作為學術成果,尤其在人文領域這種必要性更加凸顯。
(作者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