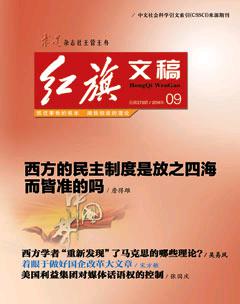“王偉光:遵守黨的紀律是無條件的” 等7則
王偉光:遵守黨的紀律是無條件的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的講話中強調,遵守黨的紀律是無條件的,要說到做到,有紀必執,有違必查,不能把紀律作為一個軟約束或是束之高閣的一紙空文。一是嚴明的紀律是黨的生命線。中國共產黨是靠革命理想和鐵的紀律組織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紀律嚴明是黨的光榮傳統和獨特優勢,是她同一切非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根本區別之一。嚴明的紀律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重要標志 ,是鞏固黨的團結統一、增強凝聚力戰斗力的重要保證,也是新形勢下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的重要舉措。二是嚴明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財經紀律是重中之重。遵守黨的政治紀律,是遵守黨的一切紀律的基礎,是遵守黨的一切紀律的保證,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條件下具有特殊重要性。三是使黨的紀律真正成為帶電的高壓線。要著力提高黨性修養,激發遵守黨的紀律的內在動力,特別是領導干部要率先垂范,做遵守黨的紀律的表率,同時堅持完善民主集中制,強化嚴明紀律的制度保證, 進一步加大對違紀行為的查處力度,增強黨紀的剛性約束。
(來源:《光明日報》2014年4月18日)
胡鞍鋼:社會主義是中國成功的制度優勢
縱觀新中國60多年的發展歷史,中國之路的開創者和領導者們一直都在試圖回答這個問題。毛澤東指出:“照抄別國的經驗是要吃虧的,照抄是一定會上當的。這是一條重要的國際經驗。”鄧小平在1987年10月再次強調指出:“我們既不能照搬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做法,更不能丟掉我們制度的優越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之路的發展包括三個基本因素:一是不斷增加現代化因素,最大限度擴大生產、創造財富,最大限度利用現代知識、科技、教育、文化和信息要素。二是不斷增加社會主義因素,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和政治優勢,共同發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三是不斷增加中國文化因素,對構建中國特色的理想社會有重大創新,比如建立小康社會、和諧社會、學習型社會等。社會主義因素是實現現代化追趕的“加速器”。影響世界需要中國自覺、中國自信和中國標準。“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國真正的主流。共同富裕是十幾億中國人民的民心所向,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目標、執政綱領和政策的基點。
(來源:《經濟導刊》2014年第4期)
習驊:立場決定命運
李肇星有一次在國際航班上,邂逅了早已失去蘇共和蘇聯的原蘇共中央總書記、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問了一個全世界都想問的問題:為什么結局會是這樣?戈爾巴喬夫想了想說:因為我們沒有鄧小平!的確,從1977年復出,到1997年去世的20年間,鄧小平領導實施了改變中國和世界的兩大政治行動,一是改革開放,二是錘煉黨風。兩件大事竟發端于同一次會議: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舉起改革大旗的同時,恢復成立了中央紀委。人們很少注意到這兩者之間的邏輯聯系:改革開放順應天下大勢,是民族復興的必由之路;端正黨風提高了黨的先進性,是改革開放的政治保障。只有改革開放,社會主義才有吸引力;只有風清氣正,共產黨才有凝聚力。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這兩大決策是最好的詮釋。作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鄧小平偉大戰略的邏輯起點,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基石——人民主體論。人民是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力量,是共產黨存在的全部理由,是一切工作的起點、終點和標準——這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核心理念,也是鄧小平始終堅守的根本政治立場。站在這個立場看問題,中國為什么繁榮穩定?蘇共為什么走向末路?答案一目了然。角度決定高度,立場決定命運。蘇共背叛人民在先,人民唾棄蘇共在后,印證了“物必先腐,而后蟲生”的道理,重演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老劇本,完全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別人。對于最后只剩下“共產黨”招牌的假共產黨的倒臺,我們不但沒有半滴眼淚,還要歡呼人民主體論的勝利,否則,就偏離了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政治立場。毫無疑問,研究蘇共興亡、吸取經驗教訓,關鍵詞不是“權位”,而是“人民”!中國不僅有鄧小平,這是中國和中國人民的幸運,是中國共產黨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結果,也是蘇共的悲哀所在。
(來源:《中國紀檢檢察報》2014年4月22日)
舒剛:中國特色與中華文化
中國特色與中華文化密不可分。中華文化沉淀在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歷史發展之中,沉淀在中華民族心理之中。為什么中國走出了一條與西方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從根本上說是中華文化使然,是中華民族內生性演化的結果。為什么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被中國人民所接受?就在于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與中華文化具有高度契合性。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與中華大地完全融合,是經過毛澤東同志那一代共產黨人的不懈努力,使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使社會主義具有中國特點、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一句話,使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帶有了中國特色。把握中國特色必須了解中華文化,因為許多基本概念都來自中華文化。比如,我們用“中國夢”描繪中華民族的美好理想,這里面有濃厚的中華文化。我們用“實事求是”概括黨的思想路線,這是來自中華文化;我們用“小康”作為奮斗目標,這是來自中華文化。正由于中華文化對于中國特色十分重要,所以,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過程中,我們要十分強調傳承和弘揚中華文化的重要作用。
(來源:《時事報告》2014年第4期)
朱安東:我國公有經濟已退無可退?
蘭州自來水苯超標事件再次把法國威立雅水務集團推到了輿論風口浪尖。據估計,外資水務占國內水務市場總體比重在10%左右,國有水務公司占60%以上,其余份額由私營水務公司和上市的國有水務公司占有。而在全世界水務中,公有企業的占比在90%以上,美國的水務中91.4%是由公有制企業提供的。我國可能已經成為私營企業在水務領域比重最高的國家之一。事件發生后,出現了國企負責掌控自來水業務的呼聲。這并非偶然。事實上,全球私有化浪潮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已經開始停滯甚至逆轉。一方面,在許多國家,最有價值的國有企業已經賣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已經不再那么有利可圖,如果要賣,政府需要給私企提供補貼,這面臨更多政治和經濟問題。另一方面,前期的私有化引起大量社會矛盾。由于私有化的種種弊端,一些國家開始了再國有化,其中比較典型的是委內瑞拉、阿根廷、玻利維亞和俄羅斯。金融危機進一步推動世界范圍內的國有化浪潮。這對中國的國企改革有重大借鑒意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決不能被動搖。從總量上看,我國公有經濟已經退無可退,否則基本經濟制度被動搖,黨的執政基礎被削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將功虧一簣,中華民族將再一次跌倒在現代化的門檻上。
(來源:《環球時報》2014年4月17日)
劉東民:金融自由化,不是萬能藥
金融自由化理論實際上就是新自由主義思想在金融學領域的展現,一度受到了西方學術界和政府的普遍歡迎。1973年美國斯坦福大學的兩位學者羅納德·麥金農和愛德華·肖分別完成了《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和《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兩本著作,奠定了金融自由化的理論基礎。正如肖本人所說:“自由化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用市場去代替官僚機構”。從20世紀70年代拉美地區開始推動金融自由化,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再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近40年來的全球實踐,人們對于金融自由化、金融創新與金融風險的關系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首先,金融自由化同時具有增長效應和波動效應。實踐表明,一方面,實行金融自由化的大多數國家確實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增長效應,但另一方面,幾乎所有實施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國家都經歷了明顯的波動效應,多數國家還遭遇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其次,金融自由化的成效與制度變遷的初始條件、次序和速度有關。但這僅僅是原則上的共識,在對初始條件、次序和速度的具體判斷上,意見分歧巨大。再次,政府的適度監管與干預必不可少。
(來源:《 人民日報 》 2014年4月18日)
劉奇:農地問題,不在所有制而在二元制
一個時期以來,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加速推進,建設用地的剛性需求與日俱增,農地問題更加凸顯。農民的財產權等諸多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農民增收困難,土地流轉的市場平臺難以建立,亂圈亂占耕地現象不斷發生,征地強拆引發的群體性事件逐年增多,土地資源浪費嚴重等一系列社會矛盾和問題頻發。據此,不少人把問題歸結為土地的公有制所致,認為只要推行農地私有化,一切問題就會迎刃而解。這顯然是高昂著頭顱叫賣西方的教條,卻沒能低下頭來看一看腳下的土地。中國農村土地制度,問題不在“公”與“私”的所有制,而在“城”與“鄉”的二元制。縱觀中國歷史上的土地制度和當今世界各國土地制度可以看出,那種認為只有私有制才能解決農地問題的觀點是一種認識誤區。相反,土地私有制更易于豪強兼并,一旦土地被過度兼并,農民成為流民,這種制度即成了引發朝代更替的火藥桶。當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土地所有制都不完全是私有制。美國是土地私有制的典型國家,但其土地并非全部私有,有59%為私人所有;39%為公有,其中聯邦政府所有的為32%,州及地方政府所有的為7%;另有2%為印第安人保留地,即專門辟給原來美洲的土著居民的。從法理上說,農地諸多問題的根源不在“公有”“私有”,而在“公權”“私權”。農地問題的關鍵是公權力失控。一些人往往把公權濫用的問題統統歸結為公有制上,把私權不受侵害的希望全部寄托于私有制上,這是認識上的誤區。解決農地問題的根本不在于改變所有制,而在于規范公權力。
(來源:《中國發展觀察》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