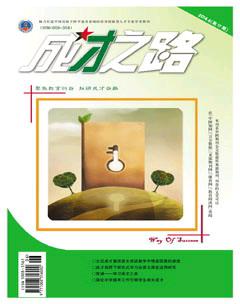對現行教材的一點看法
李立新+馮兆海
最近,我又重讀《戰國策·秦策五》“甘羅十二為上卿”一段,感慨良多。
甘羅,胸有成竹,說服張唐寥寥數語;周旋諸侯間,為秦得16座城池而不費一兵一卒。智慧勇略,令人嘆服。然而,我在想:一個相當于今天小學剛畢業年齡的少年,何以建此奇功?何以有此非凡膽識?何以洞徹列國、熟諳歷史、曉知人事、才辯如此?難道除了其天賦超群之外,不得歸功于當時的早期教育嗎?但是,那時的蒙學,文史、政治不會分得很細吧。而就是那短短的幾年,就能如此,不發人深思嗎?王勃十四朝散郎,劉晏七歲舉翰林,白居易六歲能作詩……我們今天即使到了初中乃至高中,人文底蘊又如何呢?那么,傳統的國學教育不值得借鑒嗎?小學語文與“品社”就不可以合而為一嗎?而且,一些文言的,尤其是韻文的精品,就不可以取代一些淺淡如水的白話嗎?學生文化素養的缺失,是我們教育工作者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
我國唐代學校開設的課程,如經科就有《尚書》《論語》《孝經》《左氏春秋》等,這相當于現代的語文和“品社”吧,還有歷史的成分呢。而史科則有《史記》《漢書》《三國志》等,也都是完整的著作,也有算科的。宋元時期所開設的蒙學課程有《三字經》《千字文》《童蒙訓》《訓蒙詩》等。明清蒙學則多以《三字經》《千字文》《神童詩》《弟子規》等為教材。
翻開我們現行的語文課本,深得文言滋養的魯迅的作品也在漸漸淡出,還有人嫌文言文選多了,大抵因之深而難學或許還有無用論的緣故吧。搞科學不容易,難道就不學科學了嗎?任何一門學問的學習,都不會輕而易舉。無原則地迎合或趨眾的傾向,也是不負責任的,最終往往也會誤人。我們堅信:文言于學文有效。從前學幾年私塾,國學水平就不一般。從前的國學中,就包含著理學、哲學、或“品社”之類的內容,現在講整合回歸,可以考慮把“品社”整到語文中。文章本來就可兼具“品社”的一些功能嘛,語文固然不是政治,但它僅僅是語文嗎?任何學科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現代高等教育分科的細密是為了科學的研究,自然無可非議,但作為基礎教育,尤其小學階段,作為人文的教育,實在不應太過割裂,整合而一舉多得,經濟劃算,文學、理學是為同學嘛。
學生人文素養的提高,是當前需要重視的問題之一。我們要通過多種形式,為學生提供優良的精神食糧,促進學生成長。
(吉林省蛟河市漂河九年制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