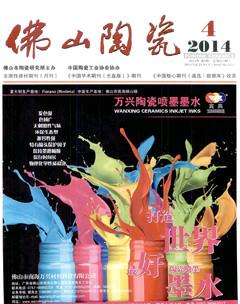“石窟造像”對觀音題材陶瓷藝術創(chuàng)作的影響
沈霞平
摘 要:觀音題材在陶瓷藝術上的表現(xiàn)由來已久,是一個不斷發(fā)展、不斷超越的過程,在不同的表現(xiàn)工藝中均有所表現(xiàn),青花、粉彩、新彩、顏色釉,釉上、釉下都能很好地將觀音題材得到完美的表現(xiàn)。本文以石窟造像藝術為切入點,探討石窟造像對當代陶瓷藝術觀音題材創(chuàng)作的影響,有助于在陶瓷藝術創(chuàng)作過程中借鑒和吸收“石窟造像”中的精妙技法。
關鍵詞:石窟造像;觀音;佛教;藝術;技法
1 前言
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黃金時代,社會安定,經(jīng)濟繁榮、文化昌盛,外交頻繁。大唐文化深深地影響著周邊國家,東有朝鮮、日本;西有印度等國家。在這一時期,佛教傳入中國并扎根于大唐土地,佛教在中國已經(jīng)本土化、世俗化,禪宗興起并迅速風行,甚至一度取代了印度佛教的地位。佛教的基本教義為自我心靈凈化為核心,主張心凈自然成佛,這對于盛唐時期石窟造像營造了濃厚的氛圍。
唐代,石窟遍及全國,主要有敦煌石窟、龍門石窟、炳靈寺石窟、天龍山石窟、四川巴中石窟、夾江千佛崖、大足石窟、樂山大佛及相當于晚唐時期的云南劍川石窟等。這些石窟藝術達到極盛,數(shù)量之大空前絕后,且技藝精湛,富有獨特的時代風格。
2 “石窟造像”對觀音題材陶瓷藝術創(chuàng)作的影響
2.1 敦煌石窟造像對觀音題材陶瓷藝術創(chuàng)作的影響
敦煌唐代壁畫,從內(nèi)容到形式,都是最輝煌、最豐富的,題材范圍大致包含了神話故事、農(nóng)耕、畜牧、庖廚、打場等;內(nèi)容上重點反映現(xiàn)實生活和表達人們對現(xiàn)實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壁畫創(chuàng)作過程中,畫師們形式手法多種多樣,有的以色彩斑斕,變化豐富取勝;有的以線描功夫扎實見長;有的以場面宏偉、繁縟熱烈感人;有的以人物心理刻畫細微而達到了真切傳神的絕佳效果。在造型方面,他們嚴格按照人體比例進行塑造,菩薩面相方面,唐代菩薩已進一步女性化,在一些石窟中一些佛像尚留有蝌蚪式的小胡子,這種小胡子在視覺集性別區(qū)分上與今天男人的胡子不一樣,缺乏男性應有的陽剛之氣。
敦煌石窟造像藝術與當代觀音題材陶瓷藝術盡管是兩個不同的藝術形式,但這兩者之間卻有著某種必然的聯(lián)系。比如,敦煌石窟中的壁畫構圖上不斷創(chuàng)新,打破了北朝“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格局,以鳥瞰式或散點式的透視經(jīng)營了多種多樣氣勢磅礴的巨型經(jīng)變化,開拓了意境創(chuàng)造的新領域。這對于觀音題材的陶瓷藝術作品創(chuàng)作給予了很好的借鑒藍本。在陶瓷藝術作品中,觀音題材是較為常見的題材,觀音相貌端莊慈祥,心性柔和,儀態(tài)莊重,世事洞明,永保平安,消災解難,遠離禍害,經(jīng)常手持凈瓶楊柳,具有無量的智慧和神通,大慈大悲,普救人間疾苦。當人們遇到災難時,只要念其名號,便前往救度,所以稱觀世音。在中國古典神話傳說中,觀音是西方極樂世界教主阿彌陀佛座下的上首菩薩,同大勢至菩薩一起,是阿彌陀佛身邊的脅侍菩薩,并稱“西方三圣”。明晰觀音這種文化內(nèi)涵與神話傳說中極其“唯美”的寓意,給了陶瓷藝術家十足的靈感,似乎“筆下畫觀音,心中有神明”的精神寄托。陶瓷藝術中的“觀音”不僅僅是一尊菩薩的臨摹,還要充分發(fā)揮陶瓷材質(zhì)美、泥性美、釉色美,將觀音題材融入到藝術意境之中,創(chuàng)造出另一尊“看不見”的觀音。
2.2 龍門石窟造像對觀音題材陶瓷藝術創(chuàng)作的影響
龍門石窟的鑿建,北魏曾盛極一時,此后沉寂了一百多年,到了唐朝又重新活躍了起來,從唐太宗到唐玄宗的一百多年間,造像活動一直不斷,形成了龍門石窟開鑿史上的第二個高潮。龍門石窟的整體設計獨具匠心,首先環(huán)境選擇在半山腰中,群像居高臨下,朝拜、瞻仰的人們需要爬上一段山坡才能一睹大像的尊容,這可以增加人們對于“山不在高,有仙則名”的敬畏。
在龍門石窟中的九尊大像中,初主尊頭與身體比例接近真人外,其他八尊均頭大身小,初看似乎不和比例、甚至越看越顯得別扭。其實這種設計暗藏玄機:唐代匠師們考慮到需要保證主尊的中心地位則需要將其他佛像形象設計得變得矮小,如果頭與身的比例要合乎真人的比例,則主尊以外的八尊像就要做得很小。單個看合乎比例,整體布局卻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壞,看上去就像一群小兒圍觀一個大佛,顯得滑稽可笑,嚴重地削弱了佛教的莊嚴肅穆。
因此,石窟造像中比例協(xié)調(diào)已然成為藝術創(chuàng)作中的金規(guī)玉律,成為藝術審美標準中的一大重要標尺。其實,比例協(xié)調(diào)作為美學視角,在評判藝術、藝術創(chuàng)作中同樣適用于觀音題材的陶瓷藝術創(chuàng)作。如在瓷上繪畫觀音時,觀音往往與蓮花形成一幅完整的畫面的。一方面是因為蓮花在佛教以及佛教藝術中占有特殊地位,因為蓮花在佛教中是一種圣潔物,被奉為“佛門圣花”。蓮花是最早用來裝飾瓷器的花紋之一,從南朝開始在陶、瓷器紋飾中一直盛行不衰。至今仍多在大器件如梅瓶、壺、罐等下部采用重復排列多個蓮瓣紋環(huán)繞器身的裝飾技法。另一方面,多個蓮瓣紋安排在器件底部,既起了彌補畫面過于空洞的缺陷又在視覺上起到使得觀音與蓮花之間的主次明晰、比例協(xié)調(diào)。蓮花之于觀音,就像拂塵至于道士,都是相互搭配的。
2.3 巴中南龕佛像對觀音題材陶瓷藝術創(chuàng)作的影響
巴中南龕是位于四川省巴中縣城南古化成山,南龕石刻多用簡練、概括分層次的手法表現(xiàn)形象體積,各個平面內(nèi)又使用精美多變陰線刻、陽線雕。使得佛像作品顯得豐富飽滿,線刻陰陽交迭、主從揖讓、剛柔相濟。直線剛勁挺拔,曲線柔韌有力,表現(xiàn)出唐代匠師的高超雕刻技法以及大唐工藝美術發(fā)展的盛況。基于這些表現(xiàn)技法,匠師們能將某種情懷融入到藝術創(chuàng)作中,使得藝術作品“活”起來。
據(jù)張靖敏《從希臘女神到東方圣母訶利帝母——藝術形象在絲綢之路上的演變》介紹,巴中南龕坡云屏石68號石窟龕前的浮雕是一個頭梳圓形狀發(fā)髻的婦女,長藍色裙衣,盤腿而坐,懷中抱一小孩,左右各坐四個光頭小孩。在當?shù)厝藗儼堰@位女神是作為兒童保護神,女神面慈神和,表現(xiàn)為多子多福的世俗慈母的形象,有一點送子觀音的特點。這里形象地刻畫了一個圣母的形象,昭示著母愛的偉大。唐代時期的巴中是一片荒夷之地,文明進程相對而言要落后好多,那里的人們并不關心佛是什么,道是什么,但在藝術表現(xiàn)上卻能將慈母的形象刻畫得如此仔細入微,實屬難得。這種佛像盡管與觀音有一些差異,但一種源自他方的佛徒、佛圣,究竟對蕓蕓信徒拯救、普度,成為他們內(nèi)心深處的渴望。
也許當下許多陶瓷藝術家并未對佛學加以深入研究,甚至某些基本的教義都不能講個所以然,只能依葫蘆畫瓢,在佛教題材藝術創(chuàng)作過程中略帶諺語所說“小和尚念經(jīng)有口無心”那樣,在用畫筆勾勒起他心中不明晰的世界,那么這種藝術作品也很難打動其他欣賞者。因為對于其他欣賞者而言,很難讀懂藝術家的情懷。也就是說,他們不關心佛、道本身,他們更不關心的是“佛”這個不知哪兒來的東西,是否能達我所愿,是否能解我所難。所以,所以他們對自我意愿達成的信仰程度,遠遠超過了對“佛”本身信仰程度。
3 結語
綜觀以上敦煌石窟、龍門石窟、巴中南龕中造像藝術的特點,給陶瓷藝術創(chuàng)作者提供了參考和借鑒,特別是針對觀音題材的陶瓷藝術創(chuàng)作,從營造意境、比例協(xié)調(diào)、情感交融等方面進行了闡述。觀音題材在陶瓷藝術上的表現(xiàn)由來已久,是一個不斷發(fā)展、不斷超越的過程,在不同的表現(xiàn)工藝中均有所表現(xiàn),青花、粉彩、新彩、顏色釉,釉上、釉下都能很好地將觀音題材得到完美的表現(xiàn)。藝術是人類表達和交流思想的一種語言,陶瓷藝術創(chuàng)作活動是借助陶瓷這一獨特的媒介將藝術家的情感得以表現(xiàn)的一種實踐,是一種融觀念情感于物態(tài)化的意象的實踐活動。只有在不同的藝術形式中互相滲透、互相借鑒,在傳承的基礎上不斷創(chuàng)新,不斷融入陶瓷藝術創(chuàng)作者的情感于思想,觀音題材在陶瓷藝術中才能有效抵御人們的審美疲勞,才能散發(fā)出新意,才能有持久的生命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