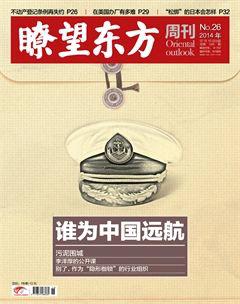李澤厚的公開課
楊天

2014年5月21日,上午9點不到,華東師范大學(以下簡稱“華師大”)的百人報告廳已滿滿當當。
50多歲的楊斌是蘇州一中高級語文教師,早上6點半,乘坐高鐵來到上海,到了華師大報告廳,他發現自己只能坐在墻角的地上了。
9點半,一位老人緩步走上講臺,人們安靜下來,少頃,掌聲長時間地響起——84歲的李澤厚登場了。
滿頭銀發,鄉音未改,他招手示意管理人員讓門外的人們進來,接著說,“也許有人是想過來看看猴子表演。你們可以進來,(不想聽了)也可以自由地出去。”
這是李澤厚此次上海之行的最后一課,完全公開。此前10天,他已在華師大連開四場倫理學討論課,從“回應桑德爾”出發,主題圍繞著“道德、倫理與人性”和“市場與道德”展開。
以這樣公開授課的方式和國內學術界、特別是年輕學子們交流,于在國外多年的李澤厚還是第一次。各方聚焦之下,公開課似乎演變為文化事件。有媒體稱,思想者李澤厚“沒有過時,未被超越”。
“作為20世紀下半葉以來少見的原創型哲學家,李澤厚的現實感一直很強。多年來雖然人在美國,目光卻從來沒有離開故國的土地和人民。”華師大哲學系主任郁振華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為什么瞄準桑德爾
此次開講,李澤厚樹了一個理論“靶子”——“全球學術明星”桑德爾。
桑德爾是美國著名政治哲學家。作為當代西方社群主義理論的代表人物,其在哈佛大學開設的本科通識課程——公正課(Justice),30年來有超過14000名學生選修,創下哈佛大學的歷史紀錄。最近幾年,他的講課視頻借助互聯網廣泛傳播。
有學者認為,李澤厚此次扯著桑德爾的衣襟來國內開講,“這種‘反主為客的逆轉,充滿了戲劇性和歷史荒誕感。”
報告中得知,上世紀90年代,李澤厚就讀過一批社群主義的書,其中包括桑德爾的《民主的不滿》。而桑德爾在近兩年的暢銷書《公正》和《錢不能買什么》中提出的“市場社會”的嚴重問題,李澤厚認為值得參考和深思。
“這個時代用桑德爾的話說,已經進入了一個全面的‘市場時代,對于市場和道德之間的關系,李先生可能覺得非常重要。”華師大哲學系教授付長珍對本刊記者說,“和桑德爾提倡的‘公共的善不同,李澤厚強調‘和諧高于正義。在李澤厚看來,中國社會是個情理交融的社會,基于此基礎上的倫理理念,可以為救治由市場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提供一個思想資源。”
企業家鄧德隆是李澤厚口中最熟悉他理論的人之一。他透露,或許因為桑德爾目前在中國學生和年輕人中影響力很大,李澤厚覺得有必要來回應一下桑德爾。
“在西方,像桑德爾這樣以社群主義反抗自由主義以及現代化,有一種解毒作用,能促進其資本主義社會的完善。但李先生認為,在目前的中國,如果桑德爾的東西太多,恰恰會阻礙現代化的發展。”鄧德隆說。
“公平”還是“正義”
桑德爾的“正義”課程是哈佛的一個傳奇。他善于通過案例來引出一些重要話題,引導和鼓勵學生參與討論。
對桑德爾以非學院化的語言講述倫理學的方法,李澤厚比較欣賞:“能深入淺出地觸及要害,雖然在理論上并無原創。”
因此,李澤厚選擇了以桑德爾式的討論課方式與他隔空對話。
“不做答辯會,不做記者招待會,最初設想是十幾個人一起交流。希望明確提出幾個問題,提示大家,也包括我,一起思考。”李澤厚如此定義這次討論課。
但十幾個人的交流最終擴充至百人,后因參與人數太多,校方又另外開設了一間視頻教室。
討論開放而平等。每次兩小時的課程,李澤厚不停地拋出問題,再追問。
華師大哲學系研究生黃家光第一個回答了李澤厚的問題——桑德爾的“Justice”應翻譯為“公平”還是“正義”。
“第一場剛開始有些拘謹,以為李先生會多講一些,沒想到他上來就拋出了問題。”黃家光回憶。在他眼中,李澤厚像一位武學已臻化境的宗師,完全掌控著局面。“他不會對每個問題都立即回應,而是一直在鼓勵和啟發我們,不斷將討論引向深入。”
一輛失控的火車面前有兩條軌道,一條站著一個胖子,另一條站著五個人,作為司機的你選擇犧牲哪一方?四名船員在海上漂流,因為饑餓,其中三人吃掉了最羸弱的少年,活了下來。在這樣的情況下,吃人是合理的還是一種犯罪?
桑德爾經常引用的兩個經典案例,被李澤厚拿來說明他與桑德爾的不同。
漫長而開放的討論后,李澤厚亮出了自己的看法——應該在西方的倫理學之外加上“情”的因素。
第一場討論,李澤厚準備了10個問題,因為時間關系,“天賦人權”、“代孕問題”、“先養90歲父親還是10個饑餓瀕臨死亡的孩子”等問題都未及討論。
期待和失望
從探討自己與桑德爾倫理理念的異同,談到作為人性的“文化-心理結構”;又以9·11事件中恐怖分子之死與救火隊員犧牲為例,討論了兩種道德(社會性道德和宗教性道德)的區分;最后談到如何看待作為哲學的倫理學。李澤厚的四次討論課,用《文匯報》“筆會”主編劉緒源的話說,“漸入佳境”。
第四課的最后,李澤厚回答了中國到底有沒有哲學的問題。他認為,中國的哲學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倫理學。
“最近幾年,李先生特別著力于他的倫理學思想的發展。”郁振華說,“倫理學是一門實踐品格特別強的學問。關于公平、正義、道德等問題的討論,不僅是理論問題,也是中國當下面臨的現實問題。”
作為本次課程的結語,李澤厚再次提出了“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換”問題,期待中國的知識分子抱有一種歷史責任感,去思考中國如何走出一條屬于自己的現代化的道路。
但多位參與討論課的人士表示,今天的中國學界對李澤厚思想的了解程度已遠不如前。
黃家光說,自己哲學系的同學雖然都知道李澤厚的名字,但沒讀過他著作的大有人在。
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白彤東感覺“有些人可能是‘追星去的,沒有真正針對李澤厚的思想討論起來。”劉緒源認為整場討論“熱烈有余,深度不足”。
“李先生本來希望學界能對他的思想提出些不一樣的看法,但在這一點上他可能會比較失望。”鄧德隆說。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