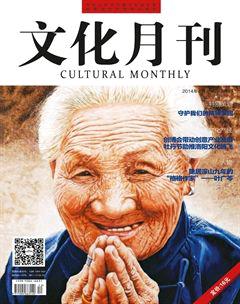商山中飛出的金鳳凰
2014-07-16 12:24:08
文化月刊·下旬刊
2014年4期
關鍵詞:藝術
商洛位于鄂豫陜三省交匯之地,以商山洛水而得名。這里風景秀麗、氣候宜人、物產豐富、能人輩出,山水間滿含靈秀之氣,藝術氛圍濃烈。關于商洛戲曲的確切記載見于明萬歷四十五年,由商洛知州王邦俊所撰寫的《商州志續輯》。后雖歷經朝代更替、風云變幻,商洛地方戲劇卻在不斷地發展壯大,至今形成了“二黃”“花鼓”“道情”“迷胡”“花燈”“木偶”等門類齊全、體系完整、頗具影響的地方戲劇藝術。
商洛花鼓在商洛地方戲曲中是最具代表性的劇種之一,它以鮮蹦活跳的生活情趣、樸實通俗的藝術風格、清新抒情的唱腔曲調、靈活多樣的表現形式,躋身于全國地方戲曲的大舞臺,成為陜西戲曲界的璀璨明珠。
商洛花鼓的發展源流
商洛花鼓又名“花鼓子”,流傳于商洛地區七個縣(區),尤以商州、丹鳳、鎮安、柞水四地最為盛行,且以偏僻山村為甚。據著名花鼓老藝人劉全興、趙老二等人介紹,清光緒三年(1877),湖北鄖陽遭水災,大批災民從丹鳳縣竹林關和山陽縣漫川關進入商洛地區,借助打花鼓賣唱的形式到處漂流,靠“化谷物”來維持生計。因此,人們起初將其所唱之調稱為“化谷調”,以后逐漸衍化,遂稱作“花鼓調”,“花鼓”之名方露端倪。其調式最初僅由移民演唱,后來當地人也學唱起來,并采用了當地的方言和語音,吸收了許多商洛的民歌小調,慢慢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商洛花鼓戲。現今,一些地方在演唱《扎錐子》等部分劇目時仍沿用下河話(即鄂西北語言)。由此可知,來自湖北的小調經過與本地民歌、秧歌等藝術形式長期的互相融和,最終才形成了具有自身獨立風格,樸實、委婉的新劇種。……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家教世界(2022年13期)2022-06-03 09:07:18
家教世界(2022年7期)2022-04-12 02:49:34
中外文摘(2021年23期)2021-12-29 03:54:02
兒童繪本(2018年22期)2018-12-13 23:14:52
藝術啟蒙(2018年7期)2018-08-23 09:14:06
讀者·校園版(2018年13期)2018-06-19 06:20:12
英語學習(2016年2期)2016-09-10 07:22:44
Coco薇(2016年2期)2016-03-22 16:58:59
讀者(2016年7期)2016-03-11 12:14:36
爆笑show(2014年10期)2014-12-18 22:2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