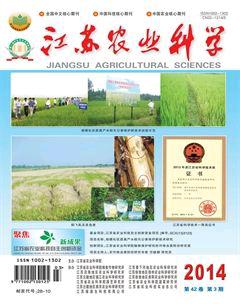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的經(jīng)濟(jì)機(jī)制分析
鐘國輝 郭忠興
摘要:通過構(gòu)建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理論模型,從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過程中的直接參與者農(nóng)民、地方政府以及土地需求者來分析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的經(jīng)濟(jì)機(jī)制,結(jié)果發(fā)現(xiàn),農(nóng)民將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的意愿由農(nóng)產(chǎn)品價(jià)格和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技術(shù)決定,誘致地方政府將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的因素包括土地出讓金和土地補(bǔ)償費(fèi)等,驅(qū)動土地需求者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的因素有房屋銷售價(jià)格和企業(yè)生產(chǎn)技術(shù)。因此,為防止農(nóng)地過度非農(nóng)化,應(yīng)調(diào)整現(xiàn)有土地補(bǔ)償方式及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后的土地收益分配機(jī)制,明晰土地產(chǎn)權(quán),提高農(nóng)產(chǎn)品價(jià)格。
關(guān)鍵詞:土地經(jīng)濟(jì);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參與者;經(jīng)濟(jì)機(jī)制
中圖分類號: F301.2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 A 文章編號:1002-1302(2014)03-0368-03
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是一個(gè)全球性現(xiàn)象,全世界建設(shè)用地(建成區(qū)和基礎(chǔ)設(shè)施區(qū))大致以每年1.2%的速度增加[1]。改革開放以來,伴隨經(jīng)濟(jì)增長和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調(diào)整,我國土地利用結(jié)構(gòu)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大量土地從農(nóng)業(yè)部門轉(zhuǎn)移到非農(nóng)產(chǎn)業(yè)部門,造成耕地資源的大量損失,即所謂的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趨勢[2],因此,我國實(shí)行了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對耕地實(shí)施特殊保護(hù),管控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的進(jìn)程,以抑制農(nóng)地過速非農(nóng)化。據(jù)《中國國土資源統(tǒng)計(jì)年鑒》記載,從1999年至2008年10年間我國約210萬hm2耕地被轉(zhuǎn)為建設(shè)用地。這期間,我國經(jīng)濟(jì)增長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但緊張的人均耕地資源已經(jīng)成為經(jīng)濟(jì)低質(zhì)量高速增長的一個(gè)危險(xiǎn)信號[3]。我國要以占世界10%以上的耕地養(yǎng)活占世界22%的人口,人地矛盾特別突出。隨著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和人口的增加,耕地還將大量減少,糧食問題將越來越嚴(yán)重[4]。
農(nóng)地作為人類不可代替的自然資源,其數(shù)量和質(zhì)量的特性決定著一個(gè)國家或地區(qū)社會經(jīng)濟(jì)的可持續(xù)發(fā)展[5]。如今,協(xié)調(diào)好經(jīng)濟(jì)發(fā)展和農(nóng)地保護(hù)的矛盾是實(shí)現(xiàn)我國可持續(xù)發(fā)展戰(zhàn)略的重要基礎(chǔ),而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又是這一矛盾的焦點(diǎn)。本研究將從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過程中的市場直接參與者農(nóng)民、地方政府和土地需求者來分析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的經(jīng)濟(jì)機(jī)制,深入理解經(jīng)濟(jì)增長與農(nóng)地部門之間配置的規(guī)律,辨別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過程中起主導(dǎo)作用的因素[2],以期為防止農(nóng)地過度非農(nóng)化提供有益的思路。
1 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與過度非農(nóng)化
隨著經(jīng)濟(jì)發(fā)展和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是一個(gè)必然趨勢,是土地資源配置的結(jié)果,因此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的進(jìn)程是不可逆轉(zhuǎn)的。吳次芳等認(rèn)為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是土地利用結(jié)構(gòu)動態(tài)變化過程的組成部分,是土地這種稀缺性資源在社會化大生產(chǎn)各部門間競爭配置的結(jié)果[6]。曲福田等認(rèn)為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是由供給影響因素、需求影響因素和制度影響因素推動的[2]。土地作為一種稀缺資源,無法同時(shí)滿足社會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所有需要[7]。農(nóng)地的邊際收益要小于建設(shè)用地的邊際收益,邊際收益較低的土地利用必然向邊際收益較高的土地利用轉(zhuǎn)化,當(dāng)城市現(xiàn)有土地供給不能滿足新增建設(shè)用地需求時(shí),就只能通過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來新增建設(shè)用地。因此,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是由于土地資源的稀缺性,在參與者的作用下由農(nóng)地資源轉(zhuǎn)變?yōu)榉寝r(nóng)建設(shè)用地。
經(jīng)濟(jì)當(dāng)事人的行為不反映在市場交易之中的某種方式影響到另一個(gè)當(dāng)事人行為時(shí),就會產(chǎn)生外部性[7]。農(nóng)地利用的效益不僅包括土地產(chǎn)品的直接性生產(chǎn)效益,還包括糧食安全、生態(tài)保護(hù)、空氣清潔、水資源涵養(yǎng)及優(yōu)美景觀等外部性效益。我國人均耕地少,人口多,土地利用的外部性十分明顯[8]。由圖1可見,如果農(nóng)地與非農(nóng)用地之間可以自由轉(zhuǎn)換,那么在只考慮農(nóng)產(chǎn)品直接收益、農(nóng)地利用沒有外部性的前提下,即當(dāng)MR=MR2時(shí),兩者相互轉(zhuǎn)換在K2點(diǎn)達(dá)動態(tài)平衡;在考慮土地利用外部性的前提下,當(dāng)MR=MR1時(shí),兩者的相互轉(zhuǎn)換在K1點(diǎn)達(dá)動態(tài)平衡。進(jìn)而推斷,當(dāng)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數(shù)量超過Q0時(shí),意味著在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過程中沒有考慮農(nóng)地利用的外部性,此時(shí)存在農(nóng)地過度非農(nóng)化現(xiàn)象。
2 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驅(qū)動因素分析
2.1 農(nóng)民
農(nóng)地具有生態(tài)及糧食安全等有利的外部性,但農(nóng)民利用土地僅僅是從事農(nóng)產(chǎn)品生產(chǎn),并沒有因農(nóng)地有利的外部性而獲得其他經(jīng)濟(jì)收益,因此,當(dāng)農(nóng)地轉(zhuǎn)為建設(shè)用地時(shí),農(nóng)民損失的成本等同于利用土地所獲得的農(nóng)產(chǎn)品凈收益。依據(jù)土地使用權(quán)永久不變,農(nóng)民凈收益Rf為:Rf=(p·q-c)/i,式中:p為農(nóng)產(chǎn)品價(jià)格;q為年生產(chǎn)農(nóng)產(chǎn)品數(shù)量;c為年投入成本;i為折現(xiàn)率。由于q、c的大小直接取決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技術(shù),假設(shè)i不變,農(nóng)產(chǎn)品凈收益則由農(nóng)產(chǎn)品價(jià)格與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技術(shù)決定。由于農(nóng)民的邊際成本等于農(nóng)產(chǎn)品的邊際凈收益,因此,農(nóng)地非
農(nóng)化過程中農(nóng)民的邊際成本由農(nóng)產(chǎn)品價(jià)格與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技術(shù)決定。從農(nóng)產(chǎn)品價(jià)格看,我國農(nóng)產(chǎn)品價(jià)格在持續(xù)提高,但相對于工業(yè)產(chǎn)品而言,價(jià)格仍相對較低,農(nóng)民從自身經(jīng)濟(jì)利益考慮,較低的農(nóng)產(chǎn)品價(jià)格會激勵(lì)農(nóng)民將農(nóng)地轉(zhuǎn)為建設(shè)用地。從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技術(shù)看,較高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技術(shù)會提高農(nóng)產(chǎn)品生產(chǎn)產(chǎn)量、降低投入成本,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土地相對密集型作物的勞動投入減少了40%~53%,機(jī)械投入增加了3~6倍,勞動相對密集型作物的生產(chǎn)在保持較多勞動投入的基礎(chǔ)上,生產(chǎn)技術(shù)向提高產(chǎn)量、質(zhì)量與收益的方向發(fā)展,因此,無論是土地密集型作物還是勞動密集型作物,其生產(chǎn)技術(shù)均朝著提高單位面積產(chǎn)量與收益的方向發(fā)展[9],生產(chǎn)技術(shù)的提高會減弱農(nóng)民將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的意愿。
農(nóng)產(chǎn)品價(jià)格與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技術(shù)提高都會增加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成本而降低非農(nóng)化,但與建設(shè)用地邊際收益比較,農(nóng)地邊際收益相對較低,只要土地市場對建設(shè)用地的需求價(jià)格高于P1,農(nóng)民就有意愿將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從而MPC
《土地管理法》規(guī)定,國家實(shí)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嚴(yán)格限制農(nóng)用地轉(zhuǎn)為建設(shè)用地,控制建設(shè)用地總量,對耕地實(shí)行特殊保護(hù)。使用土地的單位和個(gè)人必須嚴(yán)格按照土地利用總體規(guī)劃確定的用途使用土地。擅自將農(nóng)民集體所有土地的使用權(quán)出讓、轉(zhuǎn)讓或者出租用于非農(nóng)業(yè)建設(shè)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門責(zé)令限期改正,沒收違法所得,并處罰款。因此,雖然相對較低的農(nóng)地邊際收益會激勵(lì)農(nóng)民將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但在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過程中,農(nóng)民幾乎沒有發(fā)言權(quán)。在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過程中,農(nóng)民只起促進(jìn)作用,并不起決定作用。
2.2 地方政府
我國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不是由土地所有者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與土地使用者直接進(jìn)行交易的,而是由地方政府首先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征收土地,然后由地方政府作為唯一的土地供給者在土地一級市場通過招標(biāo)、拍賣、掛牌等方式,將國有土地使用權(quán)出讓并獲得土地出讓金。分稅制改革以來,土地出讓金已成為地方政府的一個(gè)重要收人來源。2007年,我國土地出讓金總額約1.2萬億元,占地方財(cái)政收人的51%[10]。在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過程中,地方政府依據(jù)《土地管理法》規(guī)定,征收土地僅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給予補(bǔ)償,包括土地補(bǔ)償費(fèi)、安置補(bǔ)助費(fèi)以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bǔ)償費(fèi),補(bǔ)償依據(jù)為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產(chǎn)值的倍數(shù)進(jìn)行計(jì)算,并且補(bǔ)償倍數(shù)最高不得超過30倍。在整個(gè)過程中,地方政府成為農(nóng)地的唯一購買者和土地一級市場的唯一供給者,合法占有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過程所帶來的收益,并直接控制著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的進(jìn)程[6]。王小映等通過對江蘇省昆山市、安徽省桐城市、四川省新都區(qū)調(diào)查研究發(fā)現(xiàn),農(nóng)地在非農(nóng)化過程中,征地補(bǔ)償?shù)木唧w執(zhí)行標(biāo)準(zhǔn)過低,政府可取得的土地增值收益空間過大[11]。地方政府相對獨(dú)立的區(qū)域經(jīng)濟(jì)利益決定了其在農(nóng)地保護(hù)行為上具有“經(jīng)濟(jì)人”理性的特征,即在農(nóng)地保護(hù)這個(gè)具有公共產(chǎn)品特性的行為上也存在搭便車的動機(jī),為發(fā)展地方經(jīng)濟(jì)具有使農(nóng)地過度非農(nóng)化的意愿[2]。趙翠薇等在分析我國經(jīng)濟(jì)成熟區(qū)、經(jīng)濟(jì)成長區(qū)和經(jīng)濟(jì)欠發(fā)達(dá)區(qū)經(jīng)濟(jì)差異特征的基礎(chǔ)上,以1999—2002年耕地面積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為基礎(chǔ),采用相對指標(biāo)(耕地減少率、耕地非農(nóng)化率)與絕對指標(biāo)(耕地建設(shè)占用總量和人均占用量)考察耕地減少狀況,認(rèn)為耕地非農(nóng)化率與經(jīng)濟(jì)發(fā)展之間存在著良好的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12]。因此,地方政府從經(jīng)濟(jì)利益出發(fā),具有將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的傾向。由于在土地一級市場的壟斷地位以及依據(jù)《土地管理法》規(guī)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對土地實(shí)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bǔ)償,農(nóng)民不得擅自將農(nóng)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使用權(quán)出讓、轉(zhuǎn)讓或者出租用于非農(nóng)業(yè)建設(shè),這也使得地方政府在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過程中起決定作用。
地方政府在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過程中,支付的成本除土地補(bǔ)償?shù)荣M(fèi)用之外,還包括土地前期開發(fā)所支付的成本。因此,地方政府的邊際成本主要由土地前期開發(fā)成本與土地補(bǔ)償費(fèi)用等決定,但二者都只是在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過程中產(chǎn)生的經(jīng)濟(jì)成本,并不比包含農(nóng)地利用過程中有利的外部效應(yīng),因此,MSC>MGC,一旦土地市場對建設(shè)用地的市場需求價(jià)格高于P2(圖3),必然會誘致地方政府征收土地以獲得收益,從而可能導(dǎo)致農(nóng)地的過度非農(nóng)化。
2.3 土地需求者
土地不僅是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不可或缺的投入要素之一,也是人類生存和發(fā)展的基礎(chǔ)。不同土地利用類型之間競租能力的變動會引起土地資源配置的變動。土地資源將優(yōu)先配置給承租力強(qiáng)、收益較高的產(chǎn)業(yè)和部門[13]。由圖3可見,當(dāng)農(nóng)地的邊
際收益低于建設(shè)用地的邊際收益時(shí),更多的土地資源將會配置給建設(shè)用地,導(dǎo)致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假設(shè)土地需求者利用建設(shè)用地進(jìn)行生產(chǎn)的生產(chǎn)函數(shù)為:q=f(m,x),其中q、m、x分別為總產(chǎn)量、建設(shè)用地、其他生產(chǎn)要素,如果產(chǎn)品價(jià)格為p0,在市場競爭性條件下,土地需求者的邊際收益將等于產(chǎn)品價(jià)格,即MR=p0;土地需求者的成本函數(shù)為:c=p·m+w,其中p、w分別為土地市場價(jià)格、其他要素成本,則邊際成本MC=p+w′,在競爭性市場條件下,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即w′+p= p0。
由于其他生產(chǎn)要素成本與生產(chǎn)率有關(guān),因此產(chǎn)品價(jià)格和生產(chǎn)技術(shù)越高,土地需求者能承受的土地市場價(jià)格也越高,而企業(yè)所能承受的土地市場價(jià)格越高,越可能導(dǎo)致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當(dāng)P
3 小結(jié)與討論
從市場直接參與者的角度分析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的經(jīng)濟(jì)機(jī)制,認(rèn)為農(nóng)民在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過程只起促進(jìn)作用,地方政府與土地需求者起決定作用(圖5)。隨著生產(chǎn)技術(shù)的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技術(shù)的提高會降低農(nóng)民的邊際成本,從而降低農(nóng)民將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的意愿,而企業(yè)生產(chǎn)技術(shù)的提高,也會降低企業(yè)的投入成本,使得企業(yè)有能力承受較高的土地市場價(jià)格,導(dǎo)致農(nóng)地有非農(nóng)化的傾向。由于土地的有限性及我國城市化進(jìn)程的不斷加快,農(nóng)產(chǎn)品價(jià)格與房屋銷售價(jià)格必然呈上升趨勢,農(nóng)產(chǎn)品價(jià)格上升會減緩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趨勢,而房屋銷售價(jià)格上升會加快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的腳步。對地方政府而言,高額的土地出讓金與較低的補(bǔ)償費(fèi)會提高政府的凈收益,從而可能誘致地方政府將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總體而言,當(dāng)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的促進(jìn)因素強(qiáng)于阻礙因素時(shí),意味著農(nóng)地具有非農(nóng)化的趨勢。
在實(shí)踐中,追求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同時(shí)忽略了資源成本,導(dǎo)致了農(nóng)地資源的大量流失[14],尤其我國農(nóng)地利用存在社會保障等有利的外部效益,一旦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因農(nóng)地所承載的這些有利外部效益將消失。盡管說土地資源是可更新資源,但是,土地資源一旦投入非農(nóng)用途,其可逆性較差,要恢復(fù)為農(nóng)業(yè)用途,需要花費(fèi)較大的轉(zhuǎn)換成本[7]。因此,為保護(hù)我國土地資源的動態(tài)平衡,應(yīng)防止農(nóng)地的過度非農(nóng)化。
首先,從農(nóng)民角度講,一方面應(yīng)保障農(nóng)民利益,提高征地補(bǔ)償費(fèi)用。目前以土地年均產(chǎn)值的補(bǔ)償方式,導(dǎo)致農(nóng)民補(bǔ)償費(fèi)用偏低,而提高了地方政府在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過程中的凈收益。政府作為在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過程中具有決定作用的主體,將可能導(dǎo)致農(nóng)地過速非農(nóng)化。因此,在征地補(bǔ)償過程中不僅要考慮土地利用的直接經(jīng)濟(jì)利益,還應(yīng)考慮與農(nóng)民有關(guān)的土地利用的外部性,例如農(nóng)地對農(nóng)民的保障性作用、農(nóng)地維持農(nóng)民現(xiàn)有生活方式的作用等。另一方面,應(yīng)提高農(nóng)產(chǎn)品價(jià)格。我國農(nóng)產(chǎn)品價(jià)格較低,長期存在剪刀差現(xiàn)象,導(dǎo)致農(nóng)地邊際效益低于建設(shè)用地邊際效益,農(nóng)民從自身經(jīng)濟(jì)利益出發(fā),也會存在將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的意愿。
其次,從地方政府角度講,一是土地征收、出讓應(yīng)符合法律法規(guī);二是應(yīng)公示土地出讓金的使用,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三是地方政府應(yīng)弱化在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過程中的作用,只起監(jiān)督作用,不直接參與。
最后,從制度層面講,一方面應(yīng)明晰土地產(chǎn)權(quán),將土地利用的外部性內(nèi)部化;另一方面應(yīng)探索合理的稅收體制,調(diào)整因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而產(chǎn)生的土地收益分配關(guān)系。
參考文獻(xiàn):
[1]Meyer W B,Turner B L. Changes in land use and land cover:a global perspective[M]. New York and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2]曲福田,陳江龍,陳 雯. 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經(jīng)濟(jì)驅(qū)動機(jī)制的理論分析與實(shí)證研究[J]. 自然資源學(xué)報(bào),2005,20(2):231-241.
[3]譚 榮,曲福田. 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的空間配置效率與農(nóng)地?fù)p失[J]. 中國軟科學(xué),2006(5):49-57.
[4]曲福田,馮淑怡. 中國農(nóng)地保護(hù)及其制度研究[J]. 南京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bào),1998,21(3):110-115.
[5]曲福田,吳麗梅. 經(jīng)濟(jì)增長與耕地非農(nóng)化的庫茲涅茨曲線假說及驗(yàn)證[J]. 資源科學(xué),2004,26(5):61-67.
[6]吳次芳,楊志榮. 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地區(qū)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的驅(qū)動因素比較研究:理論與實(shí)證[J]. 浙江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社會科學(xué)版,2008,38(2):29-37.
[7]沃爾特. 微觀經(jīng)濟(jì)理論基本原理與擴(kuò)展[M]. 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1.
[8]錢忠好. 中國農(nóng)地保護(hù):理論與政策分析[J]. 管理世界,2003(10):60-70.
[9]胡瑞法,黃季焜. 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投入要素結(jié)構(gòu)變化與農(nóng)業(yè)技術(shù)發(fā)展方向[J]. 經(jīng)濟(jì)研究參考,2002(15):29-30.
[10]杜雪君,黃忠華,吳次芳. 中國土地財(cái)政與經(jīng)濟(jì)增長-基于省際面板數(shù)據(jù)的分析[J]. 財(cái)貿(mào)經(jīng)濟(jì),2009(1):60-64.
[11]王小映,賀明玉,高 永. 我國農(nóng)地轉(zhuǎn)用中的土地收益分配實(shí)證研究——基于昆山、桐城、新都三地的抽樣調(diào)查分析[J]. 管理世界,2006(5):1-12.
[12]趙翠薇,濮勵(lì)杰. 基于省域數(shù)據(jù)的我國耕地非農(nóng)化與經(jīng)濟(jì)發(fā)展研究[J]. 江西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7,29(4):644-649.
[13]張基凱,吳 群,黃秀欣. 耕地非農(nóng)化對經(jīng)濟(jì)增長貢獻(xiàn)的區(qū)域差異研究-基于山東省17個(gè)地級市面板數(shù)據(jù)的分析[J]. 資源科學(xué),2010,32(5):959-969.
[14]黃烈佳,張安錄. 農(nóng)地城市流轉(zhuǎn)驅(qū)動力與農(nóng)地保護(hù)研究[J]. 中國農(nóng)學(xué)通報(bào),2006,22(1):387-3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