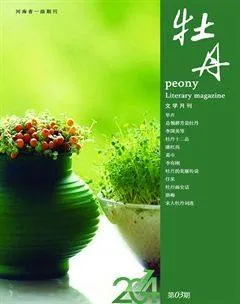浮生難改是鄉(xiāng)音
劉鍇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xiāng)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shí),笑問客從何處來。”讀小學(xué)時(shí)我就能背誦賀知章的這首詩,其時(shí)只是覺得它瑯瑯上口,全然沒能悟透其中的玄妙。長大后離開了故鄉(xiāng),才知道這首詩中蘊(yùn)藏著對(duì)鄉(xiāng)音的一份執(zhí)著、懷念與呼喚。是的,鄉(xiāng)音難改,它奔流在我們血管里,種子一樣發(fā)芽、扎根。
我出生于遼河平原上的一個(gè)小村里。身處窮鄉(xiāng)僻壤使我呱呱墜地就擁有了一口土得掉渣的方言,以至于后來離鄉(xiāng)讀書時(shí),常常因自己操著一腔“土話”而招致同學(xué)們的訕笑。那一刻,我覺得鄉(xiāng)音是那么的羞澀、卑微和無助。為了融入群體,也為了心底不被人譏笑的那點(diǎn)虛榮心,我就偷偷地學(xué)城里人的“洋腔洋調(diào)”。但鄉(xiāng)音極其頑強(qiáng)地扎根于我的腦海中,以至于“洋話”學(xué)得丟三落四,像“郊區(qū)音”一樣不倫不類,最后竟落得個(gè)邯鄲學(xué)步的地步。大學(xué)畢業(yè)后,我因工作關(guān)系,經(jīng)常天南海北地跑,于是各地的方言相繼闖進(jìn)耳畔,我學(xué)來學(xué)去,終于“四六不靠”,一嘴的南腔北調(diào)!
年齡的增長,閱歷的增多,使我越來越感到自己的幼稚與可笑——為何要把鄉(xiāng)音改掉,而去應(yīng)和別人的生活呢?干嘛為難千百年來流傳下來的鄉(xiāng)音?每到一個(gè)新地方,盡管我嘴上說著一兩句方言俚語,內(nèi)心深處卻充滿了愧疚和鄉(xiāng)愁,“客里清愁無可奈,臥聽檐溜瀉秋聲”,深為鄉(xiāng)音鳴不平,內(nèi)心深處承受著良心的拷問和靈魂的鞭撻。
有一次,我出差到呼和浩特。走在大街上,聽著滿街的“鳥語”,看著一張張陌生的面孔,心里真有一種客居他鄉(xiāng)、孤苦伶仃的凄涼、寂寞感,自己猶如來到了另一個(gè)星球,竟然與這個(gè)空間格格不入!在市中心廣場(chǎng)歇息時(shí),驀然,一句熟稔的遼南話傳入耳畔!驚喜地舉目四望,見一位中年婦女正在給身邊的小姑娘講解廣場(chǎng)奔馬雕塑的含義!我三步兩步跑過去,像大海中的落難者突然間看到了舢板一樣與她們興奮地攀談起來!熟悉的鄉(xiāng)音瞬間驅(qū)散了我心頭久淤的凄涼與孤獨(dú),一縷陽光暖暖地照亮了我的心房!真是“老鄉(xiāng)見老鄉(xiāng),兩眼淚汪汪”,那位大嫂也高興得不得了,打機(jī)關(guān)槍似的問這問那——她隨夫從鞍山市遷居呼市已五年有余,在這塞外邊陲很少能碰上老鄉(xiāng)——她興奮得竟忘了介紹自己,但我從她的眼眶中,分明看到了一種晶瑩的液體在閃動(dòng)!這是對(duì)鄉(xiāng)音的追憶和渴望啊!還有一次,我到內(nèi)蒙草原去收購皮張,15天的差期,我像是被判了15年徒刑:聽不到一句漢語,喝不到一口開水,吃不到一個(gè)水果——這絕非夸張!巧的是,當(dāng)我深入一個(gè)叫“烏蘭奧都”的小鎮(zhèn)子時(shí),竟在那里遇到了一位鞍山籍的皮毛商!久違的鄉(xiāng)音重又響徹耳畔,猶如天籟之音在遼闊的草原上奏響!那位大哥說死也不放我走,拉著我進(jìn)了蒙古包。馬奶酒,抓羊肉,奶酪,酸奶湯,喝得是天高地闊,吃得是山高水長,“酒酣胸膽尚開張”,紅光滿面,一腔豪情,大有“會(huì)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的威武豪氣!——當(dāng)然,不為這酒,不為這肉,而純粹是為了這一腔難以割舍的鄉(xiāng)音!
那一刻,我真真切切地懂得了在這個(gè)世界上,真有比金子還要貴上幾千倍、幾萬倍的東西……
鄉(xiāng)音,這種帶著銅質(zhì)的聲音經(jīng)過了歷史和歲月的打磨,愈發(fā)鮮亮而青蔥,它滲進(jìn)了每一個(gè)游子的血脈,為游子在異地他鄉(xiāng)撐起了一方晴空和大寫的人生!“美不美,家鄉(xiāng)水;親不親,故鄉(xiāng)人”,鄉(xiāng)音,不正是滋養(yǎng)故鄉(xiāng)的一腔熱血嗎?不正是故鄉(xiāng)人用祖祖輩輩的鄉(xiāng)情滋養(yǎng)出來的一種刻骨銘心的鄉(xiāng)土文化嗎?
人事倥傯,鄉(xiāng)音難改!
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