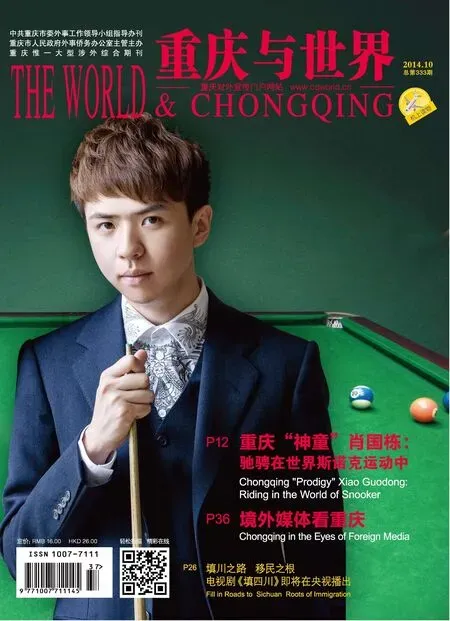德國醫生和德國使館
——浪漫故事下鮮為人知的歷史
□ 文、圖/見習記者 吳俊琰
德國醫生和德國使館
——浪漫故事下鮮為人知的歷史
The Germany Doctors and the Embassy
□ 文、圖/見習記者 吳俊琰

古色古香的德國大使館舊址
德國醫生的“浪漫愛情故事”
一個是楚楚動人的白家千金小姐,一個是宅心仁厚、頗有名望的德國醫生,在日光慵懶的清晨,攜手漫步在青石鋪就的山路上,一邊享受和煦的山風,一邊聆聽鳥獸清吟。這樣一對郎才女貌、門當戶對的神仙眷侶本應當白頭偕老、幸福一生,最后“他們在德國過著幸福的生活”……
只可惜他們生錯了時代,在20世紀初葉,西方世界帝國主義擴張的野心是籠罩在中國人心中的陰云。白家小姐的父母都是極傳統的中國人,怎么能眼睜睜看著自家女兒跟“蠻夷之人”談情說愛呢?他們甚至為此鬧到了德國使館。迫于雙方壓力和難以割舍的真摯感情,這對苦命鴛鴦雙雙殉情自殺。不過,他們的死也讓雙方理解了他們的愛情并抱有負罪感,最終將二人合葬。
——這種現代版的《孔雀東南飛》當然只存在于小說家美好的想象中。在重慶本土作家莫懷戚的小說中也曾提到過在20世紀初有一位德國醫生來到重慶行醫濟世、聲名遠播。不過這些想象也并非毫無根據。據好事者考證,南山上面還真曾住著一位德國醫生:保羅·阿斯米(Paul· Assmy)。而他確實有一位來自中國武漢的妻子。
不過保羅醫生名留后世倒并非是因為對當地老百姓有什么驚天地泣鬼神的功績,也并非是因為一段讓人津津樂道的愛情故事。所有和保羅醫生有關的風流韻事不過是“一塊墓碑引發的猜想”罷了。
從墓碑到使館——德國大使館的前世今生
從現今重慶郵電大學往廣益中學方向走,在大路的盡頭有一座古雅別致的雙層別墅——單從建筑藝術的角度講的話,確實算得上是別墅。大概沒有人會想到,在這人跡罕至的大山深處竟會有如此典雅的建筑,更不會想到這里曾是抗戰時期德國駐華大使館的舊址。在大使館后面的路邊上,有一塊簡樸的墓碑,墓碑的主人正是德國醫生保羅·阿斯米。
這位保羅醫生究竟是何方神圣?他的墓碑為什么竟可以立在德國使館的后面呢?難道他是死在任上的德國大使?其實,德國正式將駐華使館遷往重慶是1938年的事,而保羅醫生在1935年就去世了。
1981年,中日《馬關條約》的簽訂使重慶成為開埠港。德國也隨后在重慶設立領事館,辦公地址在今天的七星崗附近。保羅醫生也應德國公使之邀到重慶開設診所并籌辦、主持醫學院校。一開始,醫生辦公、居住都在診所里。后來,他在南山上修筑別墅以安頓妻兒。至于為什么選在南山就不得而知了,后來公開的他的日記里也并未提及。不過,當時甚至有英國人在上面修建教會學校(廣益中學前身),想來當時的山上并不像現在這樣冷清,而是相當熱鬧吧。
至于別墅變使館,那是保羅醫生死后3年的事了。
保羅醫生于1935年在這個他曾經相遇、相知的城市辭世,只留下孤獨的墳墓和別墅。1938年,由于堅持全面抗戰的需要,當時的國民政府內遷重慶,德國大使館也隨之遷來。不過,主城大部分地區都在日軍轟炸的威脅之下,德國大使館便向保羅醫生的后人租用別墅作為新的辦公地址,畢竟當時很多國民黨政要在南山上建有別業。不過,這可能也是中國歷史上最短命的大使館駐地之一了:1941年,中國正式對德宣戰,德國使領館撤出重慶后就再也沒回來過……
德國大使館——保羅醫生的故居從此破敗了。即使在重慶,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廣益中學的深處,在南山文峰塔附近,在楊家山步道的盡頭,曾有一國大使在此辦公。
這座不為人所知的大使館數十年如一日地靜靜佇立在群山之中,好像在靜候我們來訪。我和友人沿著幾十年前的人們留下的大道,趁著清晨的薄霧和偶爾透過樹枝傾瀉下的斑駁晨光,聆聽著默默的呼喚,尋訪那曾經熙來攘往的地方。走到盡頭,我們看到一幢中西結合的單體式建筑:青磚、青瓦、飛檐、木戶、至今依然通透的巨大玻璃窗、青苔覆蓋的青石板臺階……起承轉合自然流暢,木石搭配渾然一體,從設計到建造都一絲不茍,充分體現出德國人的務實、嚴謹。拾階而上,踏在二樓的木地板上,給人一種懷舊的感覺。目之所及,一個巨大的壁爐又仿佛讓整個屋子溫暖不少。你很難想象這棟房子有百年左右的歷史,也很難想象它看起來弱不禁風,卻從來沒有經歷過太大檢修。1991年,重慶南岸區政府才把大使館定為“區級文物保護單位”,并委托專人進行看護。
我和友人漫步在鋪著厚厚山泥和枯枝的路上,感受著夏日山腳下感受不到的清涼、愜意,不由得陶醉了。腳下隱約可見山石鋪就的路基,仿佛訴說著當年的熱鬧和重慶在抗戰時的輝煌歷史。走到山路邊上,透過林蔭和霧靄,隱約可見朝天門碼頭和渝中半島,更可以看見滾滾東流的長江水和溯江而上的輪船。讓人不由得思緒翻飛,回到那個戰火連天、人民艱苦奮戰的豪壯年代!

在德國大使館的瞭望塔,透過樹蔭,可以看見渝中半島和滾滾長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