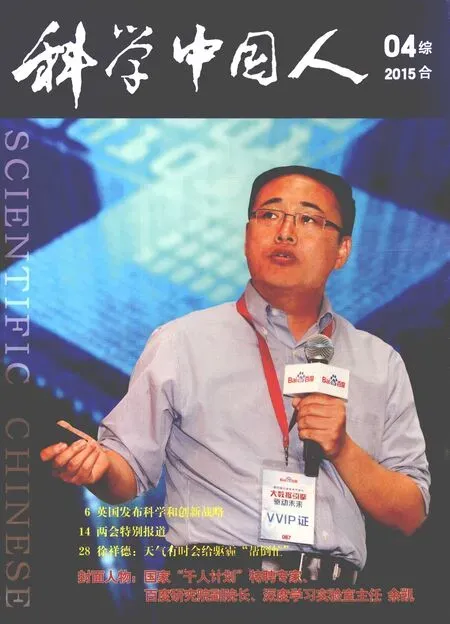《剪燈新話》中《翠翠傳》蘊含的喪葬習俗
陳奕彤
(長春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吉林長春130022)
《翠翠傳》講述的金定和劉翠翠,本是自主擇婚、過著美滿生活的恩愛夫妻,但戰亂卻拆散了他們,使得劉翠翠成了李將軍的寵妾。金定為了訪妻,倍經險阻,夜行露宿,到了李將軍處,還只能以兄妹相稱,最后雙雙殉情而死。《翠翠傳》中共有三處描寫了有關喪葬的習俗:
“生得詩,知其以死相許,無復致望,愈加抑郁,遂感沉痼。翠翠請于將軍,始得一至床前問候,而生病已亟矣。翠翠以臂扶生而起,生引首側視,凝淚滿眶,長吁一聲,奄然命盡。將軍憐之,葬于道場山麓。“
“一旦,告于將軍曰:妾棄家相從,已得八載;流離外境,舉目無親,止有一兄,今又死矣。妾病必不起,乞埋骨兄側,黃泉之下,庶有依托,免于他鄉作孤魂也。言盡而卒。將軍不違其志,竟附葬于生之墳左,宛然東西二丘焉。”
“父曰:我之來此,本欲取汝還家,以奉我耳。今汝已矣,將取汝骨遷于先垅,亦不虛行一遭也。”
研讀文本段落,我們發現喪葬儀式和觀念是通過鬼神信仰的文化心理浸染,經過幾千年的時間演化而來的。首先要強調的是死亡現象與喪葬習俗不是同步出現的。彝族的神話《勒俄特衣?居子猴系譜》中說,彝族是“不設靈”、“不待客”、“不做帛”、“不送鬼”的。只是到了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社會過渡的時代,才開始供奉神靈,實行喪葬儀式。《周易?系辭傳》也說:“古之葬者,厚衣之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由此可見,人類從來就有死亡,但尚無任何喪葬習俗存在。據考古學、民族學的資料來看,原始人類對尸體的處理,最早很可能是將尸體吃掉。在更新世葉晚期的猿人階段,便是以這種方式處理尸體的。就北京猿人來說,許多學者都認為確實存在“同類殘食”的現象。《馬可波羅游記》也談到,福建沿海的土著居民很喜歡吃人肉,認為人肉比其他肉類更鮮美。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呢?生物學研究表明,早期人類食人現象的產生很可能與生物的生存斗爭有關。原始人類處理尸體的另一種做法是將尸體棄之野外用樹枝之類的東西覆蓋起來。它的出現估計在食尸體之后,即在生產力水平發展到足以維持人的最起碼生存需要之后。其實在動物界,許多動物都有埋葬同類的行為。比如,大象就用樹林、花卉埋葬同類。生態學家分析,這是為了去除尸體的惡臭氣味,凈化環境,以利于生存。
鬼魂觀念出現以后,原始初民認為人死后以另外一種方式繼續活著。山頂洞人將死人埋在活人居住的洞穴中,就是很好的證明。但對原始人來說,死去的人即鬼是神秘莫測的,鬼魂總是在“冥冥“之中對活人降福降禍,活著的人只能任由鬼魂擺布。如此一來,在鬼魂觀念出現以前的那些不尊重尸體的做法,就不可能在繼續下去了。否則,將招致鬼魂的報復、懲罰。對尸體做認真處理便成了歷史發展的必然。像納騷所說,當原始先民深情地哀號時,祈求死者返生時,他們當然希望他完完全全地返生;然而,差不多就在號叫的同時,他們也產生了一種恐懼,害怕死者真的返生,而又不是他平時的助人而合群的有肉體的靈魂返回,卻是他看不見的生疏的和可能懷著敵意的沒有肉體的靈魂返回。原始初民對死者的矛盾情感,在以后的喪葬習俗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從邏輯上說,無論戀慕還是恐懼,都有可能導致對尸體進行特殊處理,從而使喪葬習俗得以生成。而喪葬產生的時間,就現今而言,最早的喪葬習俗出現在舊石器時代后期。如周口店的山頂洞人遺址就留有早期人類的三個頭骨和軀干骨,人骨附近撒有鐵礦粒粉,身旁還有作為隨葬用的裝飾品,據此可推測當時的人類已經有簡單的喪葬儀式了。
從考古資料來看,遠古時代的喪葬習俗進入新石器時代之后有很大的發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氏族公共墓地的產生。如西安遺址村和河南裴李崗新石器時代遺址,都有集中的公共墓地,均反映出當時的人們相信鬼與活人一樣過著氏族體制的團體生活。可以說古人是根據他們的現實生活來安排鬼魂生活的。同時靈魂返祖的觀念也影響著公墓的建立。他們相信人死之后靈魂要回到祖先所在地,和他們繼續生活,于是就出現了文中“將取汝骨遷于先垅”和“乞埋骨兄側,黃泉之下,庶有依托,免于他鄉作孤魂也”這樣的觀念想法了。喪葬習俗發展到周代,由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統政治需要,進行了一番整肅、規范,納入到“禮”的范疇里,加以制度化、法律化。對墓葬大小、棺槨層數、隨葬品種類以及喪期等都作了明確規定。至此,作為中國喪葬習俗的基本模式,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綜觀整個文本,其實講述喪葬的細節并不多,因為在人們的腦海中這些已經是再平常不過的事實,出現這種的現象的原因恰恰就是因為人們對喪葬的變式太熟悉了,我們長久以來生活在鬼神信仰的土地上,始終被影響著,被支配著,被宏大、濃重的中國民俗籠罩著。似乎每個人都能說出來應該怎么為死者超度、入葬,而且條縷明確,入情入理。這就是我們研究文學作品中民俗的意義。我們不僅要懂民俗,更要知道民俗是怎么來的,經過了怎樣的流變,有著怎樣的社會功能,這樣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心理。為深入探討中國文化做鋪墊。
[1](明),瞿佑,《剪燈新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馬可波羅游記》,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1981.
[3](法)列維?布留爾,《原始思維》,商務印書館,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