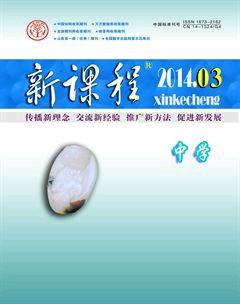“悵惘—暢想—暢快”
鄒先雄
優秀的散文作品所呈現出來的結構形態,總是主觀和客觀的結合、外部和內部的圓融、規范和獨創的和諧。好的詩歌作品也是如此。筆者執教高中語文多年,發現有一類抒情散文(詩),結構是圓形的,情感也是回到原點的,下面就以高中教材的三篇傳統篇目(《荷塘月色》《再別康橋》《夢游天姥吟留別》)為例,談談這類抒情散文(詩)的結構模式。
一、從外到內的圓形結構
《荷塘月色》是現代抒情散文的名篇。文章寫了荷塘月色美麗的景象,含蓄而又委婉地抒發了作者不滿現實,渴望自由,想超脫現實而又不能的復雜的思想感情。它的結構是圓形的,外結構、內結構均如此。從外結構看,這篇作品從作者出門經小徑到荷塘復又歸來,依空間順序描繪了一次夏夜游。從內結構看,情感思緒從不靜、求靜、得靜到出靜,也呈一個圓形。內外結構的一致性,恰到好處地適應了作者展現一段心路歷程的需要。
《再別康橋》是一首優美的抒情詩,宛如一曲優雅動聽的輕音樂。全詩從“輕輕的”“走”“來”“招手”“作別云彩”起筆,看“河畔的金柳”,賞“軟泥上的青荇”,觀“榆蔭下的一潭”,“尋夢”,“沉默”,最后“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云彩”,回到空間和思緒的原點,也是一種圓形結構。
《夢游天姥吟留別》既是一首記夢詩,也是一首送別詩。這首詩的內部結構也是圓形的。詩人于天寶三年被賜金放還,因不滿權貴當道,社會黑暗而成夢,夢里富麗堂皇、其樂融融的神仙世界暗含著對現實世界的否定,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忽魂悸以魄動,恍驚起而長嗟,唯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夢醒時分,詩人又回到了苦悶的現實世界。
二、“悵惘—暢想—暢快”的情感結構
這類抒情性作品蘊含的情感變化有一些共同點,我們可以歸納為“悵惘—暢想—暢快”的情感結構。
行文伊始,作者的情感或憤懣,或傷感,或悵惘,總之是一種負面的、消極的、陰郁的情緒。如,《荷塘月色》文首的“這幾天心里頗不寧靜”,《再別康橋》詩歌首節輕煙似的、淡淡的離情別緒,《夢游天姥吟留別》中隱含的作者對黑暗現實的不滿等。
接著,作者為走出這種情感去親近自然,或賞月,或觀花,或登山,或探景,景到深處,情到濃時,作者的筆觸會由實入虛,情感上進入暢想狀態,或回憶,或遙想,或成夢,進而達成精神的愉悅。如,《荷塘月色》一文中,“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帶上門出去”,沿荷塘四周,觀月下荷塘,賞荷塘月色,“忽然想起采蓮的事情”,“惦著江南了”。心里由不靜到求靜到得靜,完成了一次情感的升華。在《再別康橋》里,徐志摩以一幅幅流動的畫面完成對康橋自然風光的描寫后,靈魂進入了冥想狀態,“尋夢,撐一支長篙,向青草更青處漫溯,滿載一船星輝,在星輝斑斕里放歌。”詩人在這里的夢應不是一般意義的夢,而是人生的夢、藝術的夢、愛情的夢,他遠離了束縛他的一切,在這夢一般的世外桃源里,擁抱生活,擁抱美。他已然為夢陶醉。浪漫主義大詩人李白,在《夢游天姥吟留別》中,更是暢想仙境,花大量的筆墨記夢,感受夢想的美好。
作品最后,作者由美好的幻想世界回到了苦悶的現實世界,回到了情感的原點,但在這里,面對依舊未變的客觀世界,作者的情感卻是正面的、積極的、陽光的。在淡淡的喜悅之中,朱自清獲得了一種暫時的超然,徐自摩“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云河彩”,輕輕地來,瀟灑地走去。李白更是表現出一種與黑暗現實決裂,決不屈服于權貴的態度,吶喊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反抗的呼聲。
誠如所述,我們剖析了一種抒情散文(詩)結構,這對我們今后創作抒情性的文學作品會有所借鑒,但文無定法,抒情性文學作品的結構更應自然而然,因情而定,因人而異,切不可畫地為牢,東施效顰,失去靈性之美。
(作者單位 湖北省公安縣第二高級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