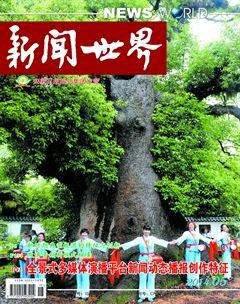電影跟組紀錄片的概念界定以及產生的原因
徐曉雪
【摘 要】電影跟組紀錄片這種類型的紀錄片在國外已經發展成熟,但在我國它的發展還不是很成熟,關于它的界定在學術界也并未形成統一的認識,因而對電影跟組紀錄片進行界定,并對它的產生原因進行分析,對電影跟組紀錄片在實際中的運用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關鍵詞】電影跟組紀錄片 概念 原因
一、電影跟組紀錄片的概念
電影跟組紀錄片這樣的稱謂,最早見于《新京報》在2011年12月下旬的一篇娛樂新聞《拍部紀錄片,幫電影“促銷”》①,隨后被其他網站轉載。雖然在這之前已有文章論述過此類紀錄片,但是均未以“跟組紀錄片”這樣的提法出現。首次以跟組紀錄片的提法作為研究對象的是蘭琳2013年的學士論文《跟組紀錄片的特征和功能分析》,文中對跟組紀錄片這樣定義“跟組紀錄片是一種能夠通過全程跟隨影片攝制組,現場記錄影視作品的整個籌備、拍攝直至后期制作完成始末的紀錄片,它的誕生靈感來源于電影尾聲附帶的‘花絮”。②同樣,這不是對此類紀錄片的第一次定義,只是明確使用了“跟組紀錄片”這樣的字樣。在2008年第四期的《電視研究》中史雪云一篇名為《電影套拍紀錄片現象初探》的文章中就已經對此類紀錄片進行過定義,“以跟蹤拍攝電影制作過程為主線,而且常常以導演創作為中心,講述影片幕后的真實故事,揭示影人創作的心路歷程。”③根據對他人的論述分析,本文提出一個質疑點,就是并不是所有的依附電影母體拍攝而成的紀錄片都叫做電影跟組紀錄片。例如電影套拍紀錄片、電影宣傳片、花絮集錦等容易與之混淆的概念,這些類型均與電影母體的拍攝過程相關,但它們卻不能算做電影跟組紀錄片,現對這三者與電影跟組紀錄片的區別做詳細闡述。
1、電影套拍紀錄片和電影跟組紀錄片
正如史雪云所述,電影套拍紀錄片這一做法雖然在國內剛剛興起,但在國外卻早已有之,并發展為兩種主要類型。
一種是以跟蹤拍攝電影制作過程為主線,而且常常以導演創作為中心,講述影片幕后的真實故事,揭示影人創作的心路歷程。這種類型的紀錄片也是目前國內套拍紀錄片的主要類型,《緣起》、《如花》等就是這樣一些為大腕拍攝的工作紀錄片。本文所提的電影跟組紀錄片所指的就是這種類型。比如《緣起》,這是一部采用紀實手法跟蹤張藝謀電影《英雄》劇組,歷時四年拍攝,從四百多個小時素材精挑細選而成。
另一種套拍紀錄片在創作上更為獨立。它拋開電影創作本身,深入到真實的社會生活中,通過活生生的歷史見證人與真實的社會歷史影像的呈現,拓展影片所表現的內容,對電影主題進行更深層次的發掘,其現實意義與人文深度遠遠超出前一種工作紀錄片。④《最愛》套拍的紀錄片《在一起》雖然在社會現實意義上有較大的成就,它能讓更多的人了解艾滋病患者的生存狀態,了解這種病的傳播方式,并包容艾滋病患者,給予他們更多的關懷和幫助。同時紀錄片真實記錄了劇組通過網絡聊天進行全國尋訪,征集人選,到選定感染者進入劇組參與拍攝的全過程。經過電影劇組選擇和感染者本人的同意,最終有三名感染者參與了電影拍攝,并在拍攝過程中,自愿去除遮擋,成為反歧視宣傳的志愿者,《在一起》記錄了劇組的拍攝狀況,因而,《在一起》也屬于本文所指的電影跟組紀錄片。
電影套拍紀錄片和電影跟組紀錄片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區分兩者最主要看這部紀錄片是否以電影母體的制作過程為中心。聯系在于電影套拍紀錄片的種類中包含電影跟組紀錄片,電影跟組紀錄片又是目前電影套拍紀錄片的主要表現形式。
2、電影宣傳片、花絮集錦和電影跟組紀錄片
電影跟組紀錄片的一個很重要的功能是宣傳,它具有較強的商業性,一方面會被制片方作為獨立的紀錄片發行,賣給電視臺或者音像出版社。另一方面,它還以花絮的片段形式,被媒體的娛樂節目所消化,成為電影電視劇作品的宣傳工具。雖然它具有很高的宣傳價值,但是本質上區別于宣傳片。宣傳片是正式放映電影以前,制片方制作的預告促銷短片,這一短片包含了電影的亮點,同時也會有一些專訪材料,長度一般不會超過3分鐘。⑤大多數宣傳預告片中不會出現大量的關于電影幕后的鏡頭,而是電影本身的精彩鏡頭形成懸念,同時被大家認同的電影跟組紀錄片,如《緣起》、《如花》、《地獄之旅》、《張藝謀和他的金陵十三釵》、《在一起》等,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宣傳意味。電影宣傳片形式多種多樣,沒有局限性,目的是為電影的上映造勢,以此來提高票房,達到一定的商業價值。而電影跟組紀錄片,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即“跟組”,這就要求此類紀錄片是紀實的,當然紀實并非指簡單化、膚淺化和非審美化的對拍攝過程進行無意義的堆砌,紀實不是目的,而是“創造性地進行敘述”,最終產生感染觀眾的藝術效果,在此基礎上才會產生相應的商業價值,它一定有區別于電影宣傳片的獨特魅力和生命力,才會在激烈的電影市場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
電影花絮一般指短小、輕松、活潑、風趣的電影片段或者電影拍攝片場的搞笑橋段,電影花絮的播放可以烘托電影氛圍、強化觀眾對電影的接收效果、滿足受眾新需求。從定義上便可區分出它與電影跟組紀錄片的異同。首先,它們都取材于電影母體本身,依附于電影母體,是電影的衍生品;其次,他們對電影有一定的宣傳價值。二者相互聯系,花絮是電影跟組紀錄片的雛形,電影花絮是零散的,短小的,無序的,不完整的片段,而電影跟組紀錄片有自己的主題,是敘事完整的紀錄片形式。從敘事學角度分析,電影花絮是由一段一段的電影片段組接而成,本身沒有完整的敘事性。而電影跟組紀錄片是有自己獨立的思想主題和敘事方式,它是一部完整的作品。
綜上所述,電影跟組紀錄片是一種新型的紀錄片形式,并非傳統意義的完全服務于電影宣傳的花絮集錦和電影宣傳片,它有自己獨立的思想和完整的敘事,出于紀實的本質,有更多記錄的成分,因而生命力更長久。
通過其他學者對電影跟組紀錄片的明確定義以及相關現象描述的文章,本文對電影跟組紀錄片做如下定義:
電影跟組紀錄片是指獨立的拍攝主體跟隨電影主創人員如實記錄電影產生和制作過程,并采用紀實手法進行表達的新型紀錄片。在這個定義中有三個要素:①獨立的拍攝主體;②電影的產生和制作;③紀實手法。現就三個要素進行具體闡述。endprint
首先獨立的拍攝主體,主要是用來區分它與花絮和電影宣傳片。拍攝電影跟組紀錄片一定是有一個獨立于電影拍攝者之外的拍攝團隊或個人。以前所看到的花絮,很多是電影拍攝過程中,拍攝電影的攝像機所記錄的滑稽搞笑或者被掐掉的片段。而電影跟組紀錄片的中心詞之一“跟組”,便要求紀錄片拍攝者是與電影拍攝者有區別的。其次是“電影的產生和制作”,把電影的產生單獨列出來是因為它涉及到導演或者制片方萌生電影拍攝的念頭方面,這一部分不包括在電影的制作中。所謂的電影制作本身包括前期制作、制作和和后期制作,展現了電影從劇本、演員選定、制作團隊、服裝道具、拍攝過程以及后期的剪輯制作的全過程。當然,電影跟組紀錄片并不是機械地呈現這些內容,而是有一定線索和思路,創造性對這些內容或者其中部分內容進行融合,這也就是最后一點所強調的紀實手法。紀實式的記錄是有主體投入的一種實錄,是主體的感情與現實的一種契合,它要求記錄者在現實和觀眾審美中找到一定平衡點。這種形態強調行為空間的原始面貌,強調紀錄形聲一體化的行為活動。
二、電影跟組紀錄片產生的原因
1997年導演甘露被張藝謀選中開始為電影《幸福時光》拍攝紀錄片,那時她發現張藝謀以前的電影大多都拍了紀錄片,只不過這些作品缺乏與觀眾見面的渠道,因此僅保存起來留作資料。由于當時國內電影產業剛剛起步,甘露為《幸福時光》拍攝的紀錄片《留住時光》,這是電影跟組紀錄片在國內公認的最早的作品。雖在業內引發關注,但在外界卻默默無聞,直到2002年,隨著電影營銷的需求,紀錄片才從幕后走到臺前。電影跟組紀錄片的產生有它的必然性。總結起來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1、電影市場發展的需求
21世紀初,國內的電影市場發展迅猛,商業電影開始吞噬電影市場,評判一部電影的好壞,首先就是票房。華納兄弟的市場總監羅伯特·格德曼在《紐約時報》上說到:“銷售電影就像火山噴發,在首映周盡你所能積聚壓力,吸引每一個人來看某一部電影從基礎開始就該造大聲勢。”⑥電影跟組紀錄片對電影的始末記錄,有助于電影在不同階段的宣傳工作,順應了電影市場的需求,因而在一定的外部環境的催化下,電影跟組紀錄片的產生便能夠被理解了。
2、受眾對電影攝制的好奇心理
在如今的大眾傳播時代,對于那些早已經熟悉報紙、廣播、電視平臺和網絡等媒體上八卦新聞滿天飛的受眾而言,關于電影制作以及電影明星幕后生活的好奇以及窺視早已成了他們的一個心理訴求。電影跟組紀錄片將受眾的目光,從電影的奇觀世界中接續過來,讓其聚焦到這部電影的生成過程上。他們窺探了這部電影生產過程中的一些秘密,滿足了他們窺探電影如何產生的需求。⑦
3、電影制作方的需求
一部電影的制作凝聚了眾多電影人的心血,對電影制作過程的記錄,其實是對電影制作者的回報和尊重。電影的上映是短暫的,而對于電影制作的回憶是長久的,正如電影跟組紀錄片導演甘露所說“想要拍留得住的紀錄片”,電影跟組紀錄片對于電影制作團隊的意義是非凡的,它是一個看得見聽得著的“過程”。□
參考文獻
①《拍部紀錄片,幫電影“促銷”》[N].《新京報》,2011-11-28
②蘭琳,《跟組紀錄片的特征與功能分析》[D].天津師范大學,2013
③④史雪云,《電影套拍紀錄片現象初探》[J].《電視研究》,2008(4)
⑤歐陽宏生:《紀錄片概論》[M].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
⑥雷·古德爾 著,高福安、王雪松 等譯:《獨立制片——從構思到發行的全程指導》[M].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4
⑦屈高翔、林榮林,《新紀錄片類型——影視幕后紀錄片研究》[J].《聲屏世界》,2013(1)
(作者:天津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研究生)
責編:周蕾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