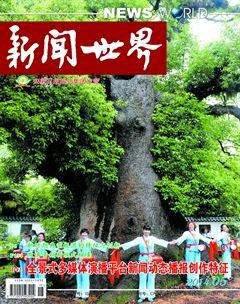淺談不具名新聞侵權的表現與規(guī)制
鄧詩如
【摘 要】陸幽訴黃健翔案,范冰冰訴黔訊網及畢成功案使得不具名新聞侵權受到人們關注。不具名新聞侵權報道是指在文中雖未指名道姓,卻以影射的方式侵害了特定對象權益的報道。不具名侵權報道一般通過典型描述或排他性描述、背景事實聯(lián)系、縮小范圍等方式影射受害人,其對被影射的受害人的傷害并不亞于指名道姓的報道,卻由于其報道對象有表面上的隱匿性,給受害人維權帶來困難。當務之急是通過明確影射的認定標準、完善舉證規(guī)則來規(guī)制不具名新聞侵權。
【關鍵詞】不具名 新聞侵權 表現 規(guī)制
一、不具名新聞侵權
新聞,即對新近發(fā)生或正在發(fā)生的事實的報道。新聞侵權,即新聞報道故意或者過失地刊登虛假新聞、侮辱、誹謗他人的新聞或者不正當地曝光事件,造成受害人人格或財產權利受到損害的行為。①
不具名新聞侵權,是指在新聞報道中,報道者雖未明確指出報道對象的姓名、身份,但其表述足以使公眾認定報道對象為某人②,從而侵犯了報道對象特定權利,如名譽權、隱私權、財產權的行為。
按照大陸法系民法,一般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包括損害事實的存在、引起損害的行為具有違法性、導致?lián)p害之人主觀上有過錯、違法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但是,不具名新聞侵權的構成要件具有以下特點:
1、侵權指向具有隱匿性
損害事實的存在就要求侵權對象必須是特定的人。由于在不指名道姓的新聞報道中,報道對象的名字被隱去,侵權的指向就具有表面的隱匿性,能否認定不指名道姓報道的侵權指向,成為了能否認定此類新聞報道侵權的關鍵。
2、損害事實證明困難
盡管不指名道姓的新聞報道沒有明確寫出被報道人的姓名,但依據其相關的表述,讀者可以推斷出其所指的對象時,仍然有可能對特定的人產生負面的影響。然而吊詭的是,受害者為了證明損害事實存在,必須首先證明文中影射的被侵權人就是自己,在這個證明過程中,受害人往往要公開更多的個人信息和隱私,受到二次傷害。
網絡環(huán)境下,不具名新聞侵權影響較大。與過去信息的單向傳遞不同,網絡時代,一篇不具名的侵權報道,通過互聯(lián)網傳播,以及網絡用戶的信息聯(lián)系、反饋和補充,其傳播范圍更廣,影響更大。尤其應當警惕個別媒體故意捏造、歪曲事實以奪人眼球,并企圖通過不指名道姓規(guī)避法律責任。
二、不具名新聞侵權報道的表現形式
不具名侵權報道隱去了報道對象的姓名,卻采用了其他影射的方式使得其侵權對象仍然可以被公眾辨認,從而侵犯報道對象的合法權益,構成侵權。
影射,意思是指用一種事物暗示或說明另一種事物。影射有兩種作用:一是起暗示、引導和提示的作用;二是借喻的作用。在不指名道姓的新聞報道中,如果可以通過文中具體的描述而使報道對象直接指向某一個特定的人,這種行為實際上就是一種影射。盡管隱去了報道對象的真實姓名,卻提供了確定其現實身份足夠的線索,因此可以構成對特定對象人格權的損害。
最早使不具名新聞侵權進入公眾視野的案件是1992年李谷一訴《聲屏周報》案,而后又有2009年陸幽訴黃健翔案與2013年范冰冰訴黔訊網及畢成功案,分析這些案例可以發(fā)現,不具名新聞侵權報道的影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種:
1、用具有典型代表性或排他性的特征描述
影射行為的一種形式是用具有典型代表性或排他性的特征來描述報道對象,如描述某人的相貌特征、語言特征、行為特征及生活和工作環(huán)境等,使得大眾可以容易地得出報道對象就是特定人的結論。
例如李谷一案中,湯生午隱去李谷一的名字而采用“十年前以一曲《鄉(xiāng)戀》而名噪大陸的某位樂團領導”這樣的描述,就是具有代表性和排他性的特征描述。《鄉(xiāng)戀》是李谷一的代表作和成名作,并且李谷一是中國輕音樂團的團長,這些特征都是顯而易見的。因此,盡管沒有出現李谷一的名字,但依據這兩個特征描述,讀者可以很容易地排除其他懷疑,而得出文中的“該領導”就是李谷一的結論。
2、結合特定的眾所周知的背景事實
還有一種影射行為是通過在特定的時間空間條件下,聯(lián)系特定的背景事實來影射特定人,使大眾可以容易地得出報道對象就是特定人的結論。這種影射較前一種而言更為隱蔽,但在信息傳播快速且互動性極強的網絡時代,大眾一旦達成初步共識,這個共識就會迅速地被散播和認定,對受害人的傷害仍然非常大。
以范冰冰訴黔訊網及畢成功名譽侵權案為例,內地編劇畢成功在3月31日發(fā)表了一條英文微博,其中并未提及任何有關范冰冰的特征,而只是使用了“Miss F”的字眼,稱“Miss F”只會靠恐嚇、撒謊,打壓比自己演技好的女演員。5月30日畢成功轉發(fā)該微博時又稱“關于‘情婦說的誣陷計劃,在3月已知,當時發(fā)了一句吐槽。某人也真是,往死里整比自己強的,卻忘了讓自己變強是王道。故今日當此留言擴散實施,反覺搞笑”。
由于5月30日剛好是《蘋果日報》刊出章子怡“情婦說”的第二天,因此畢成功的微博發(fā)出之后,立刻有網友在評論中直接將“Miss F”當做范冰冰。此后的評論、轉發(fā)者皆以“Miss F”就是范冰冰的態(tài)度散播該消息,黔訊網更是直接將該微博作為消息來源,刊發(fā)了題為《編劇曝章子怡被黑內幕:主謀范冰冰已無戲可拍》的文章,使此事的負面影響一再擴大。最終法院判定畢成功和黔訊網構成對范冰冰的名譽侵權。
3、過度縮小范圍
有些時候,盡管報道并沒有指名道姓,也沒有給出足以直接指認特定人的代表性特征,但通過不斷地給出限定性條件,將滿足條件的人縮小在一個極小的范圍內,對這些人中的一個或幾個造成權利的損害,筆者認為這也應該屬于對特定人的侵權。
比較典型的是陸幽訴黃健翔案。在黃健翔發(fā)表的《丑話說在前邊》的文章中,黃健翔“批評”了國奧隊的洋帥杜伊,并牽扯了“某女足球記者”,文中寫道:“你呢? 把人家搞成了宮外孕,回到單位里弄成丑聞,你卻縮頭烏龜了。人家也被撤了國家隊首席跟隊記者的身份了,落得個雞飛蛋打。搞得很多粉絲還十分納悶,十分想念,因為很久在國家隊的報道里看不見她的倩影了。”endprint
這段表述中,對報道對象的描述并不能達到排他性的效果,但憑借“國家隊首席跟隊記者”的描述,在國內,報道足球的著名女記者不超過6個,黃健翔在法庭上提交了另外3個女記者的名字作為證據③,但這些記者中,有過“宮外孕”的只有陸幽,陸幽成了最可能的懷疑。筆者認為,這樣小的范圍事實上已經造成了對陸幽的傷害。
遺憾的是,盡管陸幽為了維護權益,證明自己是被影射的受害人,不得不提交證據證明自己宮外孕,公開放棄自己的隱私,甚至被《遼沈晚報》公開發(fā)表見報。最終還是因為不能證明自己是該不具名報道的所指而敗訴。
三、不具名新聞侵權的規(guī)制建議
1、明確人格特定化的標準
所謂人格特定化,即是將不指名道姓報道中的隱名的報道對象確定為現實中具體特定人的過程。④
盡管目前學界與業(yè)界都普遍達成共識,侵權行為要求有特定的被侵權人,但不一定是指名道姓,只要綜合考慮足以認定被侵權人為某人,即被侵權人的人格可以特定化,就可以認為侵權。如王利明老師所說:“侵害人指名道姓地指出某某因為特定,即使未明確指出某某,而只是以其他方式或符合使其周圍的人一看即明白侵害人所指者,亦不失為特定。”⑤
但在我國的法律中,還沒有確立明確的人格特定化的標準。
首先,人格特定化需要誰來指認被侵害人?這在我國現行的《民法通則》、《侵權責任法》及相關司法解釋中都沒有明確的規(guī)定。但在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起草的《〈中國民法典·侵權行為法〉草案建議稿》中認為人格特定化的標準是“社會一般人”指認。但筆者認為,由于有的事實并不是公眾知悉的而是只有認識了解被侵權人的周邊人才知曉的。因此,筆者認為,人格特定化應以“社會一般人或被侵權人周邊的其他人足以認定”作為標準。
其次,人格特定化是唯一還是一定范圍?有學者認為被侵權人的特定必須是可以指認為某一個確定的人。王澤鑒老師認為,特定之人除個人外,尚包括一定范圍之人,例如誣指坐落某處教會牧師有不法行為,而該教會牧師有三人時,該三人皆屬特定之人⑥。筆者認為,特定應當包括一定范圍的人,當侵權行為的表述已經將被侵權人限定在極小的范圍內時,對該范圍內的人都會產生權利損害,應當認定為侵權,但范圍如何界定,還需要通過法律來明確。
2、完善舉證責任
在新聞侵權訴訟中,應當由原告承擔證明責任還是由被告承擔證明責任,或者雙方舉證責任如何分配,一直是一個備受關注和爭議的問題。
我國對侵權行為舉證責任的規(guī)定一般遵循“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目前法律中規(guī)定的舉證責任倒置情形并不包括新聞侵權。因此,原則上新聞侵權訴訟應該由原告,即由侵權行為的受害人承擔全部舉證責任。但在司法實踐中,法官多數認為真實報道是媒體的義務,原告只需證明被告確已進行關于他的新聞報道,被告有義務證明其報道真實合法⑦。
筆者認為,在關于不具名新聞侵權的案件中應當采用如下的原則:
首先,在法律仍無特殊規(guī)定的情況下,新聞侵權訴訟應當以“誰主張,誰舉證”為原則。即使采用過錯推定原則,推定被告主觀有過錯,也仍然應由原告承擔對損害事實、違法行為及因果關系的舉證。也就是說,在不指名道姓的新聞訴訟中,原告毫無疑問應當負有證明新聞報道對象與本人具有一致性,并且新聞報道確實造成本人權利損害的舉證責任。
但是,在新聞報道隱去了報道對象姓名的情況下,如果要求原告的舉證必須達到絕對真實和排他是幾乎不可能的,甚至有時候難以達到高度蓋然性。例如在陸幽案中,陸幽證明了自己是當時國家足球隊的跟隊女記者,并且是這些女記者中唯一一個有宮外孕史的。按照嚴格的證據規(guī)則,這樣的證據不能說達到了高度蓋然性,但陸幽的舉證責任應當是已經完成了的,即使不是充分的也是具有證明力的。如果被告不用承擔任何舉證,就認定原告證據不足,顯然有失公平。因此,應當在這類訴訟中引入舉證責任的緩和規(guī)則,即原告承擔有限的舉證責任,當原告的證明達到一定程度時,實行有條件的事實推定,轉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被告能夠證明的,推翻其推定; 不能證明的,推定的事實成立。
結語
不具名的新聞侵權不僅侵害了受害人的權益,也嚴重傷害新聞媒體的公信力。應當盡早對不具名新聞侵權作出明確而嚴格的規(guī)制,避免某些媒體存在僥幸心理,以影射的方式創(chuàng)造奪人眼球的新聞而逃避法律責任。□
參考文獻
①王軍,《我國新聞侵權糾紛現狀、對策及研究回顧》[J].《法學雜志》,2006(3):56
②楊立新:《人格權法》[M].法律出版社,2011:515
③程冷西,《如果那個人不是陸幽,那是誰?》,《人物周刊》,2009(22):62
④吳鵬,《姓名權的“映射”侵權研究》[D].中國政法大學,2001:6
⑤利明:《民法·侵權行為法》[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283
⑥王澤鑒:《人格權法》[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153
⑦黃罕奭,《論新聞侵權中媒體的舉證責任》[J].《政治與法律》,2005(1):117
(作者:中國傳媒大學碩士研究生)
責編:姚少寶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