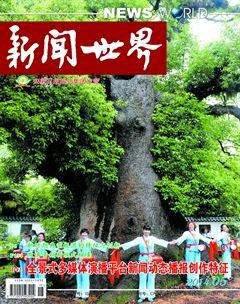解放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影像主體構(gòu)成探究
卜云
【摘 要】影像主體,即影像畫面中的視覺主體,影像主體的構(gòu)成與作品主題表達(dá)密切相關(guān),又與其它造型藝術(shù)有所區(qū)別。它是形成于一定的環(huán)境之中,并受制于照相機(jī)工具性的特點(diǎn),受制于攝影現(xiàn)場(chǎng)性的特點(diǎn),受制于影像創(chuàng)作主體的表達(dá)理念。本文以解放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的攝影作品為例,分析這一時(shí)期的影像主體的構(gòu)成方式。
【關(guān)鍵詞】解放戰(zhàn)爭(zhēng) 影像 構(gòu)成
一、物像的選擇
物像世界是由物而生像的世界,它是現(xiàn)實(shí)世界在取景框中的反映。因此,物像世界并不完全等同于現(xiàn)實(shí)世界,而是影像作者眼中的“世界”,是對(duì)固有物有所取舍的世界,又意味著作者表達(dá)的“世界”。作者會(huì)以形式和意象把它們(內(nèi)容、主題)現(xiàn)實(shí)化和吸引在一起。在構(gòu)建影像時(shí)作者所使用物像元素的涵義取決于這些元素在作者所處社會(huì)文化中的地位。
由裴植拍攝于1946年的《劉伯承打靶》,表現(xiàn)的是晉冀魯豫野戰(zhàn)部隊(duì)劉伯承司令員,在練兵會(huì)議上親自為指戰(zhàn)員們做射擊示范的情景。畫面中的主體是劉伯承,他的形象占據(jù)畫面中央。他旁邊蹲著兩個(gè)指戰(zhàn)員,他們的目光注視著劉伯承,這樣就引導(dǎo)讀者的目光注視劉司令。背景中整齊地站著一排指戰(zhàn)員,防止他們的形象會(huì)分散讀者的注意力,作者特地只拍下他們局部形象,這樣就確立了主體的中心地位。
通常來(lái)說(shuō),圖像的作者首先利用眼睛對(duì)現(xiàn)實(shí)世界進(jìn)行“有限”的觀察,并形成“潛構(gòu)圖”。在這一環(huán)節(jié)就有必要再精簡(jiǎn)物像,使得表現(xiàn)的主體確立。這一階段的官能感受非常重要,它會(huì)使作者面對(duì)物像有一種感覺,這種感覺能力體現(xiàn)了作者關(guān)于圖像創(chuàng)作的基本修養(yǎng)。只有深入到生活實(shí)際當(dāng)中,并不斷進(jìn)行思考、概括和抽象的作者才能具備這種能力。
《蔣家胡子娃娃兵》由李棫拍攝于1946年12月易滿戰(zhàn)役。作者在國(guó)民黨俘虜群中發(fā)現(xiàn)了一老(67歲)一少(13歲)兩個(gè)士兵,立刻拍攝下來(lái)。作者在眾多俘虜中,以這一老一少為主體,其他俘虜虛化成背景,意在揭露國(guó)民黨驅(qū)趕人民打內(nèi)戰(zhàn),連老人、小孩也抓來(lái)當(dāng)兵的罪行。作者在拍攝前腦海中已經(jīng)形成了這樣的觀念和情感,所以拍攝主體時(shí)有針對(duì)性和目的性。
由多幅作品組成的報(bào)道性的紀(jì)實(shí)專題攝影,在物象的選擇上有哪些技巧呢?這要根據(jù)對(duì)象自身的特點(diǎn),要根據(jù)需要達(dá)到的效果,要屈從于拍攝現(xiàn)場(chǎng)的條件。劉克己1945年拍攝了《龍關(guān)減租增資斗爭(zhēng)》組照四幅。減租減息是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在抗日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的十大政策之一,是團(tuán)結(jié)農(nóng)村各階層堅(jiān)持對(duì)日抗戰(zhàn)的一項(xiàng)基本政策,起到重大歷史作用。作品通過(guò)四幅組照的形式,反映了龍關(guān)人民熱烈擁護(hù)減租增資斗爭(zhēng)的情景。這組專題組照采用了平實(shí)的表達(dá)方式記錄事件。第一幅圖利用中景表現(xiàn)的是農(nóng)民們圍在一起計(jì)算每個(gè)人應(yīng)該拿到的退租,背景中農(nóng)民手上舉著的標(biāo)語(yǔ)上醒目地寫著“減租減息”,突出了作品的主題,表達(dá)了農(nóng)民衷心擁護(hù)減租增資政策和熱切盼望早點(diǎn)拿到該分得的退租的急切心情。下面三幅圖都是以這個(gè)主題為中心展開,第二幅圖表現(xiàn)的是民主政府代表向群眾揭發(fā)奸特分子陰謀,號(hào)召群眾檢舉揭發(fā)。第三幅圖是一位農(nóng)民婦女在控訴大會(huì)上激動(dòng)地控訴著地主的罪行,農(nóng)民痛楚激憤的表情,間接揭示了她的內(nèi)心世界。這張圖成功地抓住了被控訴地主的表情,烘托出畫面的氛圍,使畫面凝聚的感情達(dá)到高潮。第四幅圖作為結(jié)尾,農(nóng)民們一一將退租扛回家去。縱觀組照,四幅圖緊密圍繞中心,從多個(gè)角度選擇物象,表現(xiàn)主題。
對(duì)于視覺傳播而言,只有存在視覺上的主體,才有視覺傳播主題(意義)的可能。傳播的主題應(yīng)附著于視覺主體,并在眾多元素的共同作用下而產(chǎn)生。因此,圖像要在傳播中獲得有效的意義,就應(yīng)該把表達(dá)實(shí)體的媒介物放在重要的位置。這當(dāng)然要取決于作者對(duì)客觀世界的觀察能力和選擇能力。
二、形象的確立
影像作者在確立影像的主體時(shí),往往是根據(jù)所要表達(dá)的主題,使用心中之像去觀照物像,這時(shí)會(huì)在腦海中形成許多不同的視像,但此時(shí)還不是形象,作者還要顧及到主體的可表現(xiàn)性物質(zhì)材料的特性,決定從視像中確立具體的形象,這個(gè)形象就會(huì)變成主體去承載主題的涵義、完成對(duì)故事的敘述。
鄒健東1948年在淮海戰(zhàn)役新解放的淮海農(nóng)村拍攝了作品《訪貧問(wèn)苦》 。作者抓拍了部隊(duì)指揮員與兩名老大娘、一位老大爺傾心交談的鏡頭。作品形象選取得當(dāng),三位老人在向解放軍親人訴說(shuō)國(guó)民黨罪行和給人民帶來(lái)的苦難。他們痛楚滿面的情態(tài),間接地揭示了背向照相機(jī)鏡頭的指揮員的內(nèi)心世界,使畫面凝聚的感情起伏跌宕,在人物間交融、傳遞,給人以激勵(lì)和戰(zhàn)斗力量。
在現(xiàn)實(shí)的影像建構(gòu)中,形象選取得當(dāng)與否,直接關(guān)系到影像建構(gòu)的成敗,形象確立得成功,畫面的主體也就明確起來(lái),傳播的主題也就被確定;如果形象確立得不成功,其圖像主體必然會(huì)受到損害,傳播主題也同樣會(huì)受到損傷,其傳播的意義也要受到削減。
郝世保1949年1月拍攝了作品《淮海戰(zhàn)場(chǎng)一角》。郝世保閃到一門大炮后面,用被擊毀的敵人大炮作前景,表現(xiàn)了淮海戰(zhàn)役氣勢(shì)磅礴的場(chǎng)景。作者成功地運(yùn)用“大炮”這一特征式前景,并恰恰指向列隊(duì)走來(lái)的俘虜,而炮筒則高過(guò)俘虜們的頭頂,對(duì)俘虜形成一種壓迫感,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作品中,尚未散盡的大火和硝煙做背景,顯示了大戰(zhàn)剛剛結(jié)束這一時(shí)間特征和戰(zhàn)場(chǎng)這一空間特征,中景則是我軍戰(zhàn)士押著長(zhǎng)長(zhǎng)的一個(gè)俘虜隊(duì)伍走下戰(zhàn)場(chǎng),作為前景的這幅照片之所以能夠充分表現(xiàn)戰(zhàn)爭(zhēng)氣氛和淮海戰(zhàn)役的偉大勝利,成為反映解放戰(zhàn)爭(zhēng)的一幅杰作,特征式前景的成效功不可沒(méi)。
當(dāng)然,一幅圖像不光有主體,還有前景、背景、陪體等客體。主體與客體是相比較而言。哪個(gè)形象能更好地承載主題思想,更有利于意義傳播,哪個(gè)形象就更容易成為主體。當(dāng)然,主體的選擇有一定的主觀性,因?yàn)樾蜗蟛坏珌?lái)自于物像世界,也來(lái)自于作者的心像世界對(duì)物像世界的觀照、認(rèn)知和選擇。
1949年4月鄒健東拍攝了《渡江登岸》。作品表現(xiàn)的是渡江戰(zhàn)士跳下帆船沖上江岸的一剎那。作品中作為形象主體的四個(gè)戰(zhàn)士,只有一個(gè)有完整的形象,有兩個(gè)互相攙扶,形象有重疊,第四個(gè)戰(zhàn)士只露出上半身。作者有意識(shí)地讓后面的戰(zhàn)士形象外貌不完整,為了說(shuō)明渡江的戰(zhàn)士不只四個(gè),畫面以外還有很多。個(gè)別最具特征的戰(zhàn)士龍騰虎躍、健身如飛的形象,讓讀者聯(lián)想到整個(gè)渡江部隊(duì)雷霆萬(wàn)鈞、勢(shì)不可擋的威力。endprint
在專題攝影創(chuàng)作中,創(chuàng)作者要注意對(duì)主體、前景、背景、陪體等各個(gè)要素關(guān)系的把握,各要素之間要配合起來(lái),共同為確立形象服務(wù)。1947年1月,人民解放軍華東野戰(zhàn)軍發(fā)動(dòng)了魯南戰(zhàn)役,全殲國(guó)民黨軍整編26師和由美械裝備的第一快速縱隊(duì)于棗莊地區(qū)。在這場(chǎng)歷時(shí)數(shù)日的惡戰(zhàn)中,鄒健東在戰(zhàn)場(chǎng)上拍攝了一組優(yōu)秀作品《快速縱隊(duì)的快速殲滅》。第一幅照片上作者有意以幾門尚未脫去炮衣的大炮為主體,給畫面增添了幽默感和諷刺力量。第二幅照片的畫面上展現(xiàn)出大量軍車中彈起火,背景濃煙四起。第三張照片中主體為一名國(guó)民黨年輕的士兵的尸體,尸體旁被炸毀的士兵武器作為陪體展示出悲慘的戰(zhàn)爭(zhēng)場(chǎng)景。背景中燃燒的汽車輪胎,象征著國(guó)民黨損失慘重。
形象越清晰和完整,其承載主題(內(nèi)容)的能力就越強(qiáng),這一點(diǎn)毋庸置疑,但在影像的實(shí)際構(gòu)建中,為了取得視覺上的感染力和完成一種特別的印象,往往讓主體的形體外貌有意識(shí)地不完整,這種不完整性不是缺少深思熟慮的結(jié)果,恰恰相反,它應(yīng)是作者深思熟慮之后謹(jǐn)慎處理的結(jié)果。這是一種主觀有意而為之,不是客觀如實(shí)呈現(xiàn)而造成的。
縱觀這一時(shí)代的影像創(chuàng)作,影像作者已經(jīng)意識(shí)到:應(yīng)努力使主題在形象上得到自由的閃耀,而不是在形象上的僵硬。形象要因主題而有靈性,超逸飄然。形象的確立既是一種理性的決定,也是一種感性的選擇。他們自覺地意識(shí)到形象的一切要根據(jù)主題的內(nèi)容而確定。
三、主體的形成
攝影家裴植在1948年拍攝的《親密交談》反映的是中原、華東兩大野戰(zhàn)軍會(huì)師豫西,兩軍將領(lǐng)晤面親切交談的場(chǎng)景。這幅作品是在人物眾多的場(chǎng)合中拍攝的,但作者集中表現(xiàn)了鄧小平與陳毅親切交談的情景,突出了他們兩人在交談中的情態(tài)。良好的角度使其在構(gòu)圖上突出主題而不破壞畫面上特定的環(huán)境,恰當(dāng)?shù)亟栌眯鄙涞墓饩€豐富了畫面的影調(diào)。鄧小平邊談邊打著手勢(shì)的動(dòng)作,陳毅專注傾聽的神情,都極具感染力,表明了他們之間深厚的革命情誼,也道出了兩軍會(huì)師的勝利意義,內(nèi)涵豐富而深沉。這張照片抓住了這次兩軍會(huì)師的特點(diǎn),并利用當(dāng)?shù)靥赜芯拔锛磅r明標(biāo)志來(lái)作背景、作襯托,這樣就能使照片的紀(jì)實(shí)性、表現(xiàn)力和生動(dòng)感增強(qiáng)。
《對(duì)敵大爆破》這幅作品是由攝影師高帆于1948年在臨汾戰(zhàn)役中拍攝的。用大爆破攻堅(jiān),是臨汾戰(zhàn)役的最大特點(diǎn),創(chuàng)造了解放戰(zhàn)爭(zhēng)攻堅(jiān)戰(zhàn)的光輝范例。用畫面上大片空間表現(xiàn)爆破后揚(yáng)起的濃烈煙塵。一名爆破手奮不顧身、連續(xù)進(jìn)行爆破作業(yè)的英姿,畫龍點(diǎn)睛,使整個(gè)畫面斑斕流彩。作品戰(zhàn)爭(zhēng)氣氛濃郁,情思舒卷,游刃有余,給人以美的享受。戰(zhàn)斗性與藝術(shù)性高度統(tǒng)一,緊密結(jié)合。
通過(guò)對(duì)上述影像作品的觀察,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在這個(gè)時(shí)代的影像創(chuàng)作中的主體的構(gòu)成其實(shí)很簡(jiǎn)單,無(wú)非就是一些視覺元素的配置。但就是這些簡(jiǎn)單的元素,構(gòu)成了承載主題意義的主體形象,也形成了特定圖像的特殊形式。這就說(shuō)明關(guān)于影像主體的建構(gòu),影像作者們從十分樸素的自然辯證法出發(fā),意識(shí)到影像作品的主體,就是影像描繪形式的主要內(nèi)容。
主體的構(gòu)成實(shí)際上就是形式描繪的視覺化。視覺有其自身的歷史,但這一歷史的必然性受到自然法則的制約,在這個(gè)時(shí)期的某一特定主題下,主體的選擇既有歷史風(fēng)格的必然界定,也有主題風(fēng)格的時(shí)代要求。歷史和時(shí)代構(gòu)成了主體的明顯的視覺形式特征。當(dāng)然,構(gòu)成一幅畫像的風(fēng)格是極其復(fù)雜的,既有個(gè)人風(fēng)格、民族風(fēng)格又有時(shí)代風(fēng)格。因此影像主體的選擇是一種綜合的選擇,影像主體的構(gòu)成是一種意義的構(gòu)成。□
【本文系江蘇省2013年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創(chuàng)新計(jì)劃項(xiàng)目(CXLX13_930)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xiàn)
①顧棣:《中國(guó)紅色攝影史錄(上)》,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
(作者:揚(yáng)州大學(xué)新聞與傳媒學(xué)院戲劇與影視學(xué)專業(yè)研究生)
責(zé)編:姚少寶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