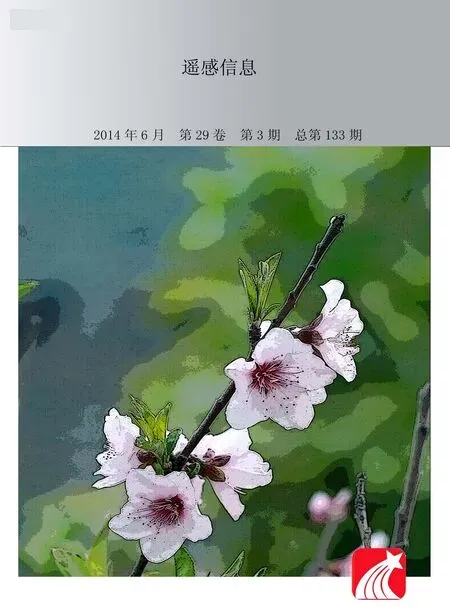基于適宜性分析的城市遺產廊道網絡構建研究
——以古都洛陽為例
袁艷華,徐建剛,張翔
(1.南京大學 地理與海洋科學學院,南京 210093;2.南京大學 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南京 210093)
1 引 言
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城市規模擴張以及生態環境的變化,遺址用地與城市建設用地關系緊張、遺址本體的破壞與遺址環境整體性地破壞等問題日趨嚴重,我國大量的遺產面臨著消失和破碎化的威脅,遺產的保護和展示困難重重。為了改變保護單個遺產點的思路,許多學者提出走出“單體保護”之圍[1]和改變“孤島式保護”[2]的構想。因此,從單個自然或文化遺產點或遺產地走向一種跨越邊界的、連續完整的保護空間格局,來最大限度地實現對自然文化遺產的整體保護成為一種新的視角和發展趨勢。然而,在古都洛陽城市化快速進程中,人地關系日益緊張的現實背景下,大遺址區用地規模巨大,對中心城區、周邊城市所產生的文化、生態、環境、休閑旅游效益卻遠遠沒有釋放出來。城市建設用地在洛河北岸的隋唐城和周王城遺址上高密度重疊發展,給遺址保護和集中展示洛陽輝煌的地下文化遺產造成巨大困難。因此,本文提出遺產廊道網絡(heritage corridor network)構建,能夠高效地保護城市遺產資源,維護遺產體驗過程的連續性和完整性以及自然和文化景觀共生關系,為探索洛陽遺產的保護模式和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提供新的視角,進而最大程度地為城市未來建設自然文化遺產資源保護區提供科學依據。
2 遺產廊道相關研究進展
遺產廊道是世界文化遺產保護新興的領域,是發端于美國20世紀80年代的一種區域化的遺產保護戰略方法,是綠色通道發展和文化遺產保護區域化結合的產物[3]。此理念詮釋了世界遺產保護由“點”狀向區域化“面”狀保護的根本轉變,以特定歷史活動、文化事件為線索把眾多遺產單體串聯成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廊道遺產區加以整體保護。伊利諾伊和密歇根運河國家遺產廊道(Illinois and Michigan Canal National Heritage Corridor)是首個通過美國國會立法指定的國家遺產廊道,標志著遺產廊道這一概念的提出和確立[4]。截止2001年,美國國會已經指定和認可的國家遺產廊道及類似的項目有23個,加上州立的遺產區域以及其他朝指定和承認的方向努力的項目共有100余項[5]。
遺產廊道是在綠道基礎上形成的概念,是擁有特殊文化資源集合的線性景觀,融遺產保護、休閑游憩、歷史文化與生態保護于一體,旨在實現對較大范圍內多種文化景觀和自然資源的有效保護。這一概念源自美國,在綠道的基礎上發展而來,是“擁有特殊文化資源集合的線性景觀,可以是具有文化意義的運河、峽谷、道路、鐵路線以及廢棄的工業區或礦區等[6]。遺產廊道通常帶有明顯的經濟中心、蓬勃發展的旅游、老建筑的適應性再利用、娛樂及環境改善[6-7]”,串連多個單體的文化、自然和非物質遺產,具有歷史、人文、生態、游憩等方面的價值,體現了文化的多元性和生態的多樣性[8]。因而自然、經濟、歷史文化三者并舉就體現了遺產廊道同綠色廊道的區別。綠色廊道強調自然生態系統的重要性,它可以不具備文化特性。而遺產廊道將歷史文化內涵提到首位,注重對廊道沿線和輻射區內的文化遺址和歷史遺跡的保護,對其短暫的歷史給予最大程度的關注,同時強調經濟價值和自然生態系統的平衡能力[6,8]。在尺度上,遺產廊道的尺度變化豐富,可以是城市中的某一廊道空間,也可以是跨城市、跨國家的區域性廊道空間[9]。如美國的賓夕法尼亞州的“歷史路徑(the historic pathway)”是一條長2.4km的遺產廊道,而由北京大學俞孔堅教授主持的京杭大運河遺產廊道項目的研究對象京杭大運河則長達1764km并橫跨18個城市[10]。
遺產是歷史形態和自然形態的完美融合,它的文化屬性并不影響自然環境在遺產廊道中的特殊作用,此二者是相互依存的[8]。遺產廊道提倡的是一種區域而非局部遺產點的保護思路,將本來呈破碎狀態的動植物棲息地、濕地、河流和其他生態上重要的區域同文化遺產和鄉土文化景觀通過連續的廊道連接和保護起來,進行整體性的解說和展示,從而實現游憩、生態和文化保護等多目標的結合[4]。作為生態規劃的先聲,美國景觀規劃大師Philip Lewis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了環境廊道(environment corridor)的概念,即連接區域文化和自然景觀資源的產物。實際上,它一定程度上包含著遺產廊道理念的雛形。Lewis將坡地、濕地、地表水、礦產資源、植被等景觀類型數據輸入GIS空間數據庫繪制圖,經疊加分析劃分特征鮮明的線性環境廊道,再利用環境廊道規劃優先和重點保護區域[11]。作為一種保護理念,從規劃角度看,遺產廊道可以作為一個地方或區域資源整合的結構和方法,強調文化遺產保護、經濟發展、生態保護的多贏,其作法就常表現為把一些遺產通過建設綠色通道連接起來[12]。國內遺產廊道理論與方法研究主要表現在遺產保護[10]、廊道寬度[3]和廊道生態構成[9]等方面,從已有的文獻研究可以看出,在國內外利用生態規劃原理和景觀生態學原理,結合GIS技術進行遺產廊道構建的研究還較少。因此在我國人地關系日益受到重視、城市人口密度不斷增加、休閑資源匱乏的現實背景下,基于ArcGIS軟件平臺,運用最小累積阻力模型構建以文化遺產保護、自然景觀、遺產休閑和非機動車道為四大關鍵主題的遺產廊道網絡具有重要的特殊價值。
3 研究區概況及研究數據
3.1 研究區概況
洛陽位于黃河中游南岸,洛河之陽,“居天下之中”,素有“九州腹地”之稱,作為“華夏第一王都”、“中華民族的搖籃”,是中國歷史上建都最早、朝代最多、建都時間最長的都城。洛陽地勢西高東低,境內山川丘陵交錯,地形錯綜復雜。北據邙山,南望伊闕,洛水貫其中,東據虎牢關,西控函谷關,四周群山環繞、雄關林立,因而有“八關都邑”、“山河拱戴,形勢甲于天下”之稱(圖1)。四季分明,氣候宜人,山水城林高度融合,顯示出氣勢非凡的帝都之相。由古至今,洛陽都城、府城和現代城市建設一直與山水緊密相依,歷經五千多年的發展,特別是近幾十年來的西進南拓,洛陽市逐漸形成了“三山環抱、四水中流、九渠貫都”的山水景觀格局。

圖1 洛陽山河拱戴之勢
司馬光曰 “欲知古今興廢事,請君只看洛陽城”。洛陽歷經幾千年的城址變遷和城市發展,形成了歷史文化、民俗文化和地域文化相融合的城市文脈,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因此,可以說,文化是洛陽城市之魂,拂去歷史塵埃,城市的街巷格局、建筑風貌和歷史遺存形態均記錄了不同時代的文化特質。幾千年的歷史文化積淀,積累了極為豐富的、具有重大歷史、科學和藝術價值的歷史文化遺存。洛陽埋藏著眾多的古遺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等傳統文物古跡,同時分布著豐富的新型文化遺產,這些都是構成遺產景觀的重要內容。
3.2 基礎數據的采集與處理
基礎地理與專題地圖數據采用的基礎地理數據主要包括DEM、行政區劃圖、土地利用、大遺址保護區劃等,其中大遺址保護區劃是根據洛陽市城市總體規劃(2008年~2020年)中大遺址保護區劃圖數字化后得到;利用ArcGIS軟件平臺,結合實地調查,建立洛陽市中心城區遺產資源分布數據庫以及不同土地覆蓋類型(綠地山林、河流水系、農田、耕地、高速公路、鐵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以及建成區)數據庫。實地調查數據主要包括遺產點分布、調查問卷資料等數據。
4 遺產廊道網絡構建研究方法
4.1 遺產廊道適宜性分析
本文強調通過空間手段(如邊界、緩沖區、廊道、格局等)構建物質聯系(physical connections),把單個遺產點/地連接形成連續的空間體系結構。然而,遺產地網絡格局一般表現為:嚴格保護的遺產地/要素,通過自然或文化廊道相聯系,共同為周圍的文化景觀或生態緩沖區環繞。自然遺產在生態系統代表性、物種遷徙、水文過程、地質構造以及自然美景特征等方面,文化遺產在本體與環境的關聯、交通、歷史脈絡及文化過程等方面,都存在著直觀或潛在的網絡屬性特征,理論上可以描述為核心遺產地/點(core heritage sites/elements)、緩沖區(buffers zone)及空間聯系(spatial connections)的基本空間結構[13]。
古都洛陽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發源地之一,有近四千年的建城歷史。大量的都城遺址、古墓群以及地下文化遺產給洛陽市遺產資源保護和遺產廊道適宜性構建提出了特殊的要求。適宜性分析是指土地針對某種特定開發活動的分析,同時也是景觀規劃的重要傳統[14]。而遺產廊道適宜性分析是指土地針對遺產休閑體驗活動的分析評價,是遺產廊道網絡構建研究的重點。麥克哈格在疊加分析方法基礎上提出“千層餅”模式成為生態規劃方法和土地適宜性評價分析的經典[15];國內外很多研究都采用“千層餅”模式進行適宜性分析[16-17]。然而,目前專門針對遺產廊道適宜性分析的研究還很少,已有的研究主要對線性遺產(包括太行八徑、京杭大運河、滇藏茶馬古道等)的研究[18,19-20]。本文借鑒綠道、生態廊道的適宜性和模擬分析,模擬古都洛陽城市潛在的遺產廊道。
4.2 模型的選取
最小累積阻力模型(Minimum Cumulative Resistance,MCR)起源于物種擴散過程的研究,是指物種從源到目的地運動過程中所需耗費代價的模型,最早由Knaapen提出[21]。俞孔堅等人運用Knaapen提出的最小累積阻力模型對遺產廊道的適宜性展開了分析[4]。該模型模擬了主體(體驗者)沿一定的路徑和場所,對文化遺產體驗和感知的過程。這種體驗感知過程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在空間上水平運動的過程,即用不同景觀要素對遺產休閑活動構成的阻力來模擬:阻力越大,則該活動越不適宜開展,適宜性也就越低;相反,阻力最小的地區適宜性也就越高,也就意味著最適宜建立遺產廊道。基于上述分析,可以運用最小累積阻力模型和生態網絡分析方法來模擬和建立阻力面,其模型的具體計算公式如下[4]:
(1)
在公式中,MCR為最小累積阻力值,f表示最小累積阻力與生態過程的正相關系,Dij代表從某遺產點j到某景觀元素中一點i的距離,Ri則代表該點所在位置對于遺產休閑活動的阻力。該模型可通過ArcGIS中的cost-distance模塊實現。基于這一公式,在確定遺產休閑活動的源(source)和景觀表面中不同特性區域對該活動的阻力系數之后,運用ArcGIS空間分析模擬景觀中的遺產休閑活動易達區域,也就是遺產休閑廊道的適宜區域。遺產是遺產休閑活動的核心,即源(source),可以通過已有普查資料或實地調研獲取。因洛陽中心城區地形起伏非常小,所以在適宜性分析中不考慮地形因子的影響。移動過程中穿越不同的線形要素和土地利用類型面狀要素的難易程度表現為不同的穿越阻力,而不同土地類型或土地覆被對于遺產休閑的阻力系數是通過專家打分或針對當地居民的問卷調查等獲得的。洛陽市遺產點的分布具有沿水系分布的特征,同時河流水系也是洛陽市最重要的綠色廊道系統,適合作為遺產廊道網絡的生態基底和基本構成要素。同時,結合調查表明人們在游憩休閑中,對于綠地山林的選擇度高于河流水系等,再次是農田和其他耕地等,建筑、高速公路和鐵路在休閑活動體驗上最不適宜,在此基礎上形成洛陽中心城區進行遺產休閑活動的土地利用類型阻力系數表(表1)。

表1 遺產休閑活動的阻力系數表
5 研究結果
5.1 自然基底分析
洛陽“三山環抱、四水中流、九渠貫都”的山水景觀特征明顯(圖2),在城市起源和布局發展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由山環水繞為自然基質、廊道景觀主體的獨特組合特征成為洛陽氣勢非凡帝王之都的基底和骨架,而洛陽豐富多彩的各類功能區呈不同形態的斑塊和景觀體鑲嵌在山水基底之間,縱橫交錯道路綠帶與濱水景觀帶作為網絡景觀主體成為聯系城市的紐帶。獨特的自然山水優勢對洛南隋唐城遺址、西苑遺址、洛北隋唐城宮城遺址和漢魏故城遺址等城市大遺址起保護作用,為遺產廊道的適宜性構建提供了天然的生態基底,同時也成為了遺產廊道網絡的基本生態骨架。

圖2 洛陽自然基底空間結構分析
5.2 遺產資源及其空間分布分析
在歷史城市中,遺產不是遺產點的簡單集聚,而是處于特定城市環境中,共同見證城市發展歷史的有機整體,承載著豐富的城市歷史信息,體現著城市的特色[22]。隨著人們對人與自然關系認識的不斷深入,文化景觀作為一種重要的遺產類別被納入遺產保護體系。千年帝都洛陽擁有無數寶貴的文化遺產,素有“地下文物寶庫”和“天然歷史博物館”之稱[23]。有世界文化遺產――龍門石窟;佛教祖庭白馬寺,金代齊云塔;關羽首級安葬處――關林;另有周公廟、潞澤會館、安國寺、河南府文廟、府城隍廟、文峰塔、孔子入周問禮碑、第十八集團軍駐洛陽辦事處舊址以及天子駕六博物館等。
中州路有“三十里長街”、“古都第一路”之譽,始建于1955年,見證了古都洛陽半個多世紀的城市發展史。在邙山和洛河之間東自偃師城到七里河貫穿商都西亳、二里頭夏都、漢魏故城、隋唐東都城、周王城 5座都城遺址及金元時期的洛陽老城,形成舉世罕見的都城遺址隊列奇觀,成為洛陽城歷史演變的軸線。歷史上洛陽為絲綢之路的繁榮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也因此留下了眾多的與之密切相關的文化遺產和歷史遺跡。漢魏故城、隋唐洛陽城、白馬寺、兩京古道、漢函谷關、龍門石窟、玄奘故里、班超墓等,它們有力地佐證了絲綢之路向東延伸至洛陽的歷程。
洛陽各時期都城故城、以及墓葬、遺址等文物遺存沿伊、洛河展開分布,使伊洛河兩岸形成了特有的“歷史河谷”,構成了洛陽古代都城歷史文化展示長廊,是中國古代城市文明頂峰的集中展示長廊。洛河不僅本身自然景色優美,并且連接多個遺產(天津橋遺址、南關碼頭遺址),是遺產廊道的重要組成部分。豐富的遺產資源眾多,但分布相對集中,對其保護要運用遺產廊道的區域而非局部點的保護理念,考慮首先由遺產點構成遺產節點,再把這些遺產節點串聯,使不同的文化主題和諧的統一在一起。洛陽市部分重要歷史遺跡見表2,都城遺址及古墓葬遺址群分布見圖3,并把這些遺產資源錄入古都洛陽自然文化遺產資源GIS數據庫中,為遺產廊道的適宜性分析提供基礎數據。
5.3 洛陽市中心城區遺產廊道網絡構建
5.3.1 遺產廊道適宜性評價和整體保護格局
本文借鑒綠道、生態廊道網絡構建的適宜性和模擬分析,運用最小累積阻力模型模擬古都洛陽中心城區潛在的遺產廊道。遺產資源點是遺產廊道網絡的主要構成要素,適宜作為遺產休閑過程的“源”。

表2 洛陽部分重要歷史遺跡一覽表

圖3 洛陽都城遺址及古墓葬遺址群分布
綜合前文有關遺產資源空間分布有關分析和數據準備工作基礎,基于不同土地覆蓋類型對于遺產體驗過程的阻力分布,利用ArcGIS軟件平臺,以遺產資源點為“源”,土地利用、道路分布為模型參考阻力面,進行費用距離(cost-distance)計算,得到遺產體驗水平空間過程的適宜性評價結果,即可根據此結果評價遺產廊道構建的適宜性。結合直方圖判讀,提取有效數據,進一步劃分高適宜性、中適宜性、低適宜性和不適宜性4個水平的適宜性區域,得出適宜性評價結果(圖4)。

圖4 洛陽遺產廊道適宜性評價
從適宜性評價結果的空間分布上看,洛河、瀍河和伊河等河流水系周邊的遺產點分布較為密集,遺產點的空間分布沿水系走向呈現一定的線性分布特點,總體上遺產廊道的適宜性較高,因此,將河流水系及其緩沖區作為洛陽市遺產廊道構建的骨架和自然基底。同時,結合實際調研可知,在洛陽城區東部、南部和西部地區,周邊的遺產點分布較為零散,且交通可達性差,同時缺乏連接遺產的線性景觀要素,總體上適宜性很低。進一步運用最小路徑法,在ArcGIS平臺通過Shortest Path命令生成最小路徑,可以用來確定、維持和恢復遺產資源點以及生境保護區之間的連接,即模擬生成潛在的遺產廊道(圖5)。

圖5 洛陽潛在適宜的遺產廊道模擬
遺產廊道是城市綠地網絡體系與自然、歷史文化遺址相結合的產物,是基于城市遺產和歷史遺跡建立的線性保護空間,強調對自然環境的保護以及城市綠地網絡體系對其內部文化遺產的襯托和聯系[24]。從空間上分析,遺產廊道整體保護格局主要的構成要素包括綠色廊道、游步道、遺產和解說系統[6]。綠色廊道、游步道和遺產資源所處節點之間的關系可用(圖6)進行說明,而解說系統就是對其三者的綜合和具體解釋。運用遺產廊道理論,采用區域保護理念保護自然和文化遺產;建立自然式游步道;綠色廊道統一連續,作為文化遺產的基底背景,并發揮綠色生態基礎設施的作用;引入解說系統,不同地段采用不同的解說主題;最終形成完整的遺產廊道保護體系[25]。因此,古都洛陽文化遺產廊道以綠色廊道為串聯各遺產點的軸線,綠色廊道兩側規劃游步道,同時隔一段距離且在遺產點分布較集中的區域配備相應的解說系統。
遺產廊道內綠色廊道的構建強調對周邊生態環境和生態過程完整性的保護,同時也映襯和烘托了綠色廊道對自然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性,發揮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可將其作為城市生態安全和文化遺產保護的空間戰略[26]。而對遺產廊道保護來說,連續完整的綠地系統有助于為沿廊道散布的文化遺產形成統一連續的基底背景。在構建遺產廊道時應重視遺產節點附近的關鍵和脆弱區域[27],保護其自然環境。所以,整體保護格局應強調從整體空間的組織考慮,保護廊道及廊道周邊范圍內所有的自然和文化遺產資源,為古都洛陽將來在城市設計層面建設遺產廊道網絡提供一定的參考依據。

圖6 遺產廊道結構示意圖(改繪自文獻[6])
5.3.2 洛陽市中心城區遺產廊道網絡構建
遺產廊道包含眾多的自然文化遺產資源,提倡的是一種區域而非局部遺產點的保護思想,因此,遺產廊道網絡構建可作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的一個重要內容。自然、文化遺產的保護應從區域和網絡入手,來整體保護自然背景和文化脈絡及其協調關系,維護遺產本體的真實性和完整性,完整保護遺產的價值及其載體[28-29]。
基于以上認識,本文通過評價組成洛陽市遺產廊道的景觀元素,可知高速公路和鐵路對遺產體驗和休閑活動具有較低的兼容性,不應納入遺產休閑體驗活動的范圍。因此,結合實地調查驗證,通過遺產廊道適宜性評價潛在遺產廊道模擬分析,依據廊道的連接性、連續性和完整性原則,借鑒城市綠地系統規劃中點-線-面相結合的理念,并依據洛陽市城市總體規劃[30]和洛陽市大運河遺產保護規劃[31],構建了以遺產資源為點-河湖水系、線性遺產景觀和城市道路等為線-城市肌理及其周圍大環境為面的遺產廊道網絡,最終形成了宏觀尺度上洛陽城市中心城區整體遺產廊道網絡體系(圖7)。
通過洛陽河流遺產廊道規劃、生態環境保護和景觀生態恢復等手段,與臨近遺產廊道系統相契合,實現對自然文化遺產的保護,維護生態敏感區和生物棲息地,增強破碎化景觀的連接度,建立親近自然的連續遺產休閑活動區。真實、完整地保護并延續洛陽遺產的歷史信息,促進自然文化遺產的展示利用,發揮其潛在的社會價值。澗西工業遺址區域中營造大明渠水系和其兩側的公共綠地共同形成的帶狀水系綠化景觀帶,形成一條生態景觀廊道,具有獨特的景觀特色,有利于遺產的整體性保護和展示。結合洛陽城市總體規劃中的護城河防護綠帶和瀍河防護綠帶,形成沿瀍河經護城河東北角至含嘉倉遺址和回洛倉遺址的步行或自行車綠色廊道,實現游憩、生態和文化保護的多目標結合。這將為洛陽遺產廊道網絡規劃建設、生態廊道及景觀格生態局構建提供科學可行的參考依據,同時為探索洛陽遺產資源的保護模式和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提供新的視角。

圖7 洛陽中心城區遺產廊道網絡示意圖
6 結束語
本文遺產廊道網絡構建的基本思路是:遺產資源調查和GIS數據庫建庫—適宜性分析評價—潛在的遺產廊道模擬—整體保護格局—洛陽市中心城區遺產廊道網絡構建。借鑒城市綠地系統規劃中的點-線-面相結合理念,運用最小累積阻力模型,以建立可持續發展的遺產保護模式為目標,針對洛陽歷史文化名城的自然和文化遺產保護,通過整合具有城市文化特色的城市道路、河流水系、生態廊道等將城市遺產點及體現城市特色的節點和區域聯系起來,構建洛陽城市遺產廊道網絡體系。構建的以遺產資源為點-河湖水系、線性遺產景觀和城市道路等為線-城市肌理及其周圍大環境為面,且具備文化遺產保護、自然景觀、遺產休閑和非機動車道為四大關鍵主題的遺產廊道網絡,能夠高效地保護城市遺產資源,維護遺產體驗過程的連續性和完整性以及自然和文化景觀共生關系,為洛陽的自然文化遺產保護和可持續發展提供一種可借鑒、更完善的模式,給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提供新的視角。
然而,本文在選擇遺產休閑活動的源時極少考慮非物質文化遺產,且基于宏觀尺度,通過GIS空間方法模擬潛在的遺產廊道的連接程度模擬,即判斷廊道連接的基本方向和位置,沒有精確到廊道的寬度以及劃定遺產廊道具體的紫線范圍,具體各遺產廊道的具體范圍和寬度還需綜合考慮其適宜性和可行性對廊道展開進一步的定量研究。運用多學科知識,綜合協調文化遺產保護、傳承與發展之間的關系,可以實現遺產保護與城市建設的協調可持續發展,使遺產成為城市性格闡釋的重要載體,讓城市發展為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提供必要的社會環境。
參考文獻:
[1] 盧波.走出“單體保護”之圍[J].南方建筑,2003(2):56-58.
[2] 安定.探析西部名城中歷史遺產的“孤島化”現象[J].城市規劃學刊,2005(4):56-59.
[3] 王肖宇,陳伯超,毛兵.京沈清文化遺產廊道研究初探[J].重慶建筑大學學報,2007,29(2):26-30.
[4] 俞孔堅,李偉,李迪華,等.快速城市化地區遺產廊道適宜性分析方法探討——以臺州市為例[J].地理研究,2005,24(1):69-76.
[5] JARVIS J W.National heritage areas program and how it affects byways[N].Tele-Workshop Fact Sheet,2003-4-2.
[6] 王志芳,孫鵬.遺產廊道——美國歷史文化遺產保護中一種較新的方法[J].中國園林,2001(5):85-88.
[7] FLINK C A,SEARNS R M.Greenways:A guide to planning,design,and development[M].Washington:Island Press,1993,167.
[8] 李飛,宋金平.廊道遺產:概念、理論源流與價值判斷[J].人文地理,2010(2):74-77.
[9] 王玏.北京河道遺產廊道構建研究[D].北京:北京林業大學,2012.
[10] 喬大山,馮兵,翟慧敏.桂林遺產保護規劃新方法初探——構建漓江遺產廊道[J].旅游學刊,2007,11(22):28-31.
[11] 宋力,王宏,余煥.GIS在國外環境及景觀規劃中的應用[J].中國園林,2002(8):56-59.
[12] 俞孔堅,奚雪松,李迪華,等.中國國家線性文化遺產網絡構建[J].人文地理,2009,24(3):11-16.
[13] 劉海龍,楊銳.對構建中國自然文化遺產地整合保護網絡的思考[J].中國園林,2009,(1):24-28.
[14] MILLER W,COLLINS M G,STEINER F R,et al.An approach for greenway suitability analysis[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1998,42(2):91-105.
[15] I.L.麥克哈格,芮經緯(譯).設計結合自然[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92:90-105.
[16] SEARNS R M.Methods on landscape analysis [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1995(33):65-80.
[17] RIBIERO L F.The cultural landscape and the uniqueness of place:A greenway network for landscape conservation of Lisbon metropolitan area [D].Doctoral Dissertation,Graduate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1998.
[18] 王思思,李婷,董音.北京市文化遺產空間結構分析及遺產廊道網絡構建[J].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10,24(6):51-56.
[19] 朱強,俞孔堅,李迪華,等.大運河工業遺產廊道的保護層次[J].城市環境設計,2007(5):16-20.
[20] 王麗萍.試論滇藏茶馬古道文化遺產廊道的構建[J].貴州民族研究,2009(4):61-65.
[21] KAAAPEN J P,SCHEFFERM H B.Estimating habitat isolation in landscape[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1992(23):1-16.
[22] 王學環,李延松.“遺產區域”在中國歷史城市中的發展運用——“遺產網絡”的構建[C].《和諧共榮——傳統的繼承與可持續發展:中國風景園林學會2010年會論文集(上冊)》,2010:137-138.
[23] 李國恩.天中京洛細雕琢一一洛陽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J].城市規劃,1989(2):50-53.
[24] 王亞南,張曉佳,盧曼青.基于遺產廊道構建的城市綠地系統規劃探索[J].中國園林,2010(12):85-87.
[25] 信麗平,姚亦鋒.南京城市西部遺產廊道規劃[J].城市環境與城市生態,2007,20(2):35-38.
[26] 李迪華.綠道作為國家與地方戰略——從國家生態基礎設施、京杭大運河國家生態與遺產廊道到連接城鄉的生態網絡[J].風景園林,2012(3):49-54.
[27] SMITH D S,HELLMUND P C.Ecology of greenways:Design and function of linear conservation areas[M].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3.
[28] 謝凝高.保護自然文化遺產:復興山水文明[J].中國園林,2000(2):36-38.
[29] 周儉,張愷.建筑、城鎮、自然風景:關于城市歷史文化遺產保護規劃的目標、對象與措施[J].城市規劃匯刊,2001(4):58-59.
[30]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 [S].洛陽市城市總體規劃(2008-2020).
[31] 洛陽市大運河遺產保護規劃[S].陜西省古跡遺址保護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2011-2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