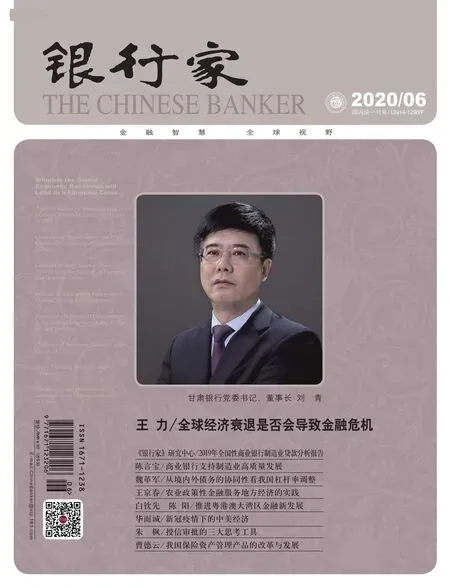如何擺正縣聯社的法人地位?
周立 楊軼塵 董玄
近期,筆者就金融支農政策的選擇性執行問題,對河北省保定市的農信社做了調查。同時,筆者也在對甘肅省聯社的培訓過程中,獲得了各地農信社系統主任、理事長及行長們所關心的農信社改革等信息。其中,縣聯社法人地位的維持,成為一個熱門的討論話題。
縣聯社的四個“婆婆”
目前在我國,除了四個直轄市外,現在各地區的農信社,實行的都是二級法人制度。2005年,各地取消鄉鎮農信社法人地位,普遍采取省聯社模式后,省縣二級法人,成為農信社治理結構的主導模式。
歷史上,農信社一直缺乏獨立地位,曾有生產大隊、人民公社、人民銀行、農業銀行等多個上級管理部門(筆者稱之為“婆婆”)。調研發現,如今已是獨立法人的縣聯社,仍然面臨一個“媳婦”應對四個“婆婆”的尷尬境遇。
人民銀行
自農信社上世紀50年代成立起,人民銀行就是農信社的主要管理者。如今,人民銀行在支付結算系統、存款準備金、超額準備金、信貸規模管控等多個方面,對縣域農信社行使著管轄權。對保定若干縣聯社的調研顯示,這幾年人民銀行實行貸款規模管控,依據有二:一是按照歷史數據,二是按照合意貸款規模。但按照農信社的理解,這是“人為嚴格地管理法人,就是惡意地不給你投放貸款”,地方人行“把這個作為一種權力來使用,你不找他,不求他,就一分錢都不給你,你必須找他,這導致農信社有貸款能力,也有貸款需求,但就是滿足不了,就是不能投放”。
以筆者調研的保定各家縣聯社為例,定州農信社2014年存款余額高達103億元,但貸款余額只有34億元,存貸比僅為32.7%,不足三分之一。易縣農信社存款余額70億元,貸款余額32億元,存貸比僅為45.7%。淶水農信社存款余額為60多億元,貸款余額為30億元,存貸比也僅僅在一半左右。相對于河北省全省而言,貸款規模和存貸比都比較小(河北省農信社2013年年底存款余額7617億元,貸款余額4685億元,存貸比61.5%)。存貸比遠遠低于75%的控制比例,也達不到50%的農村金融機構定向費用補貼資金管理的最低要求,只能眼睜睜地盯著中央惠農政策和金融支農補貼政策紅利花落他家。
在規模管控下,定州農信社有著103億元的存款規模,卻在2014年1~4月只從人行得到了1億元的貸款額度。而1~6月正是農貸需求最大的時候,卻無法得到貸款規模,也就意味著無法投放支農。想落實本地存款主要貸放于本地的政策,也就沒有任何可能。各縣聯社向筆者反映,人民銀行每月批準的信貸規模與歷史數據、各月貸款實際需求并無關系,也并不與存款規模掛鉤,實在無法理解人民銀行的批準依據。“涉農貸款說是敞口供應,不計入‘合意貸款,沒有額度控制,但是只要超過1萬元,人民銀行就又找你談話又要處罰你。說與做完全不一樣,甚至會讓縣聯社去做檢查”。而比檢查更加嚴厲的方式,就是提高超額準備金。“上調準備金,就等于罰款”。
應該承認,各地人行的政策執行情況差異較大,據筆者對甘肅農信社多位行長、理事長和聯社主任的咨詢,甘肅各縣聯社在人行信貸指標管控上,受到的干預較少,不少相對貧困地區的農信社,反而面臨貸款有效需求不足的難題。甘肅省也是最早落實去行政化的地區,已完成了省聯社辦事處改制成區域稽核中心的試點工作,區域稽核中心的主要職能是接受省聯社和監管部門的委托,提供統計、審計等服務。
銀監局
自2003年銀監會成立以來,銀監局接過了人民銀行對農信社的監管權。
如今,銀監局管轄了農信社市場進入、業務運行、市場退出等從生到死的全過程,并且在人員任職資格、網點設置、合規性監管上,具有決定性的權限。調研中筆者了解,縣聯社高管的任命,有如下程序:各縣聯社5~6名高管,都是由市辦事處提名,省聯社任命,再經過縣聯社名義選舉產生,但是,最后還需要所在市的銀監分局進行任職資格的審查批準。調研中,筆者就遇到一家縣聯社理事長的任職被銀監分局卡住的例子。縣聯社工作人員告訴筆者,正常情況下,應該是上級任命后就到位,接續工作,保持單位穩定,但諸多程序走完以后,銀監局就是不批準。拖了一年多,只好重新任命銀監局認可的另外人員。期間縣聯社諸多工作無人主持。據了解,河北省聯社的高管,也有未獲銀監局審批的先例。
按照制度設計,監管部門的主要職責,應該是從業務方面進行合規性檢查。至于金融機構的內部管理和人員任免,應該交由法人機構自行處理。即使進行資格審核,也應交給行業協會來進行認定。縣聯社高管由辦事處、省聯社,到主管部門的層層審批,使得內部控制無從談起,法人地位流于形式。
省聯社
新一輪農信社改革方案,在改革方向上曾有三種典型思路:一是堅持合作制;二是實行股份制改造;三是辦成股份合作制農村金融企業。還曾一度流行“再國有化”等說法,即將農村信用社與中國農業銀行再合并。就管理模式而言,改革方案中本來有省級聯社、農村合作銀行、農村商業銀行、信用社協會、地方金融辦和地方金融監管辦等多種模式,但從2004年起,以“地方政府負責”為總體要求的農信社改革,在兩輪試點后,都不約而同地走向了省聯社模式。
這是因為一方面,省聯社不同于農村信用社歷史上的代管機構,如人民公社、農業銀行、人民銀行、銀監會等外部機構,而是農村信用社系統內部的、自己的管理機構,有其制度優勢,尤其是在與地方政府的博弈過程中,得到了較大的話語權。但另一方面,省聯社也成為縣聯社的一個“負擔”。各個縣聯社要向省聯社入股,并交納管理費。調研中,筆者了解到保定的一些縣聯社向省聯社的入股,都在150萬元以上。河北省省聯社利用154家縣級聯社交納的2億多元股本金,成立了自己的資金運營中心,限制縣聯社和其他金融機構的同業拆借,自己統一資金運營。一是資金多,議價能力強;二是省聯社給基層縣聯社的利率低于他行利率,侵占了縣聯社利益,利差都被省聯社吃了。同時,各縣聯社每年要依照營業收入向省聯社交納0.5%的管理費。管理費的交納,采取按前一年營業收入預交的方式,年末多退少補。筆者調研的一家縣聯社反映,依據2013年的營業收入,2014年該縣聯社已經預交了207萬元管理費,而依照2013年的交納額225萬元,到年末結算時,還需要進一步上交。縣聯社一位高管調侃地對筆者說,“哎,我們是花錢買了個爹”。endprint
地方政府
2003年啟動的農信社改革,提出了“明晰產權關系、強化約束機制、增強服務功能、國家適當扶持、地方政府負責”的總體要求。農信社從總體上算是下放給“地方”了,但這個“地方”,在省聯社模式下,主要指的是省一級政府。在省聯社較強的博弈能力和蔭庇下,縣聯社接受地方政府方面的政治要求和任務,已經比以往少多了。調研中一些縣聯社高管反映,地方政府在業務性的要求上不是很多,也不再硬性壓了。過去是上級主管部門硬性壓任務,2005年成立了省聯社后,情況明顯好轉很多。
但也有關于省聯社與地方政府合謀的反映。根據一份對中國銀行業協會官員的采訪,“省聯社作為一級法人機構,有相當一部分已經掌控了地方農信社的人事任免、信貸項目審批等權力,進而成為地方政府的提款機、出納庫,這種狀況不利于農村金融市場改革,同時也將阻礙多層次金融體系的建設。因此,省聯社改革是農信社改革的重要一環”。當然,地方政府對縣聯社財務報表、貸款投向等也都有報送和要求。這使得縣聯社與其他銀行在當地的分支機構相比,獨立性還是較差。
夾縫中的弱法人
在一個“媳婦”侍候四個“婆婆”的斡旋中,縣聯社法人地位被嚴重弱化。一位理事長這樣告訴筆者:“監管上把我們當做法人,運行上根本不被當做法人。”
承擔高額成本的縣聯社法人
法人,是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依法獨立享有民事權利和承擔民事義務的組織。根據《民法通則》第37條規定,法人必須具備四個條件:依法成立;有必要的財產和經費(擁有獨立財產,即法人對特定范圍內的財產享有所有權或經營管理權,能夠按照自己的意志獨立支配,同時排斥外界對法人財產的行政干預);有自己的名稱、組織機構和場所;能夠獨立承擔民事責任。
作為一級法人,縣聯社要落實“三會一層”(社員代表大會、理事會、監事會、管理層)的治理制度。但多個“婆婆”管轄的事實,又使得法人治理制度徒有虛名。實際運行中,農信社縣聯社的法人地位只是體現在承擔稅收費用責任、根據自身盈余發放工資、經營責任自擔等方面。但是,這些權利義務就是法人地位的全部嗎?
一方面,縣聯社在監管上被當做法人,承擔各監管部門高額的監管費用。農信社在當地人民銀行支行繳納存款準備金,并向人民銀行支付農信通平臺費用、銀聯平臺費用和個人信用記錄查詢費用等。雖然目前縣聯社還不需要向銀監會繳納費用,但銀監局在當地的監管辦事處會對縣聯社采取不定期檢查,同時相關收費政策也即將出臺。作為縣域最重要的吸儲大戶,縣聯社為當地金融當局繳納了高昂的監管費用。
另一方面,在實際運行中,縣聯社沒有享受法人的許多實際權利,經營自主權受到很大的限制。四個“婆婆”使喚一個“媳婦”的現象,使得一位縣聯社高管對筆者感嘆,農信社改革一直是“走了太陽來了月亮,又是晚上”,盼不到獨立經營的那一天。
與其弱法人,還不如統一法人
調研的各個縣聯社高管,對于縣聯社名不副實的法人地位均表達了不滿:與其維持這種名不副實的法人地位,還不如讓省聯社扮演法人角色,縣聯社不再作為二級法人,只作為省聯社的下級單位,這樣可以顯著提升工作效率。據一份對遼寧省聯社負責人的采訪報道,“在縣域法人機構自身公司治理能力還不完善的情況下,如果強化其獨立性,那么很可能誘發新的風險。按照現有政策框架,省級政府應該承擔著農信社的管理和最終風險處置責任。因此,省級政府應成為省級聯社的改革主導者,由省級政府根據當地情況因地制宜地自主決定管理模式,不搞‘一刀切。”
事實上,縣聯社的法人地位現狀有著明顯的“產權殘缺”特征。諾斯提出,完整產權是指資產擁有者對其資產有排他的使用權、收益的獨享權以及自由的轉讓權,完整的產權有利于交易費用的降低以及交易的有效進行,而產權殘缺是指對一種物品、資產或資源的控制權與收益權相分離的現象。調研發現,縣聯社對其資產并沒有完整的使用權(嚴格的貸款規模控制,承擔沉重的政策性任務),但卻有比較完整的收益權,因此屬于產權殘缺。在產權殘缺的情況下,交易費用過高,降低了經濟效率。在訪談中,一位縣聯社理事長就提出,目前的監管、運行模式的確有助于防范風險,但監管的過分復雜造成了資源的浪費。
通過調研筆者發現,各個縣聯社理事長的基本觀點是,如果產權是完整的,那么更愿意保留縣級法人,因為有更多自主性可以因地制宜開展業務;但如果產權是殘缺的,那么更愿意要市級統一法人,或者省級統一法人,甚至還希望在中央有總行。這樣,就可以挺直腰桿,因為可以更好地使用資金,減少行政管理成本,更可以與人行、銀監會等“婆婆”們博弈,并抵抗來自市縣行政部門的干預和攫取。
貸款難,難貸款,支農政策左右互搏
根據保定調研的情況,筆者發現,貸款規模管控,成為各聯社壓倒性的制約因素。
縣聯社的一位理事長認為,“對于大銀行來說,他們上有全國總行,實行垂直管理,談判能力強,直接由總行下達貸款規模指標,國有大行甚至可以直接去找總理,人民銀行不敢削減這些大銀行的貸款規模。現在是柿子專揀軟的捏,人民銀行只能管上面沒根的金融機構,因此就造成這些草根金融機構經營艱難”。同時,當前由于存貸比很低,很多草根金融機構的生存都很困難。在絕大部分資金過剩,又不讓貸款的情況下,只能在銀行間做點同業拆借。另外,這種管控也造成社會上民間高息融資,想貸款卻貸不到,只能到民間進行融資,導致高利貸橫行。
事實上,縣聯社也想擴大貸款規模,但人民銀行就是不給貸款指標。雖然國家三農政策總是提出,農村金融機構的資金從哪里來,就用到哪里,以保證資金“取之于當地,用之于當地”,但是當需要用到這些資金時,人行就是不批準。而且,這種管控只是差別管控,只管農信社,對于大銀行他們卻管不了。一是大銀行本身就可以發放貸款,二是大銀行還可以做成理財產品。農信社在這兩個方面都沒有優勢,目前連理財業務也做不了,生存空間越來越狹窄。
這一方面導致資金富裕的農信社貸款難,另一方面又造成地方的小微企業和縣域經營實體難貸款,因而去尋求民間借貸、影子銀行等,助長了高利貸的滋生。
不適當的貸款規模管控,也使得金融支農政策類似于周伯通左右互搏:這邊財政部和銀監會給政策,獎勵縣域金融機構向當地發放貸款,鼓勵“支農支小”;那邊人民銀行又卡住貸款規模,無法“支農支小”。
如何擺正縣聯社的法人地位?
2014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在第六部分“加快農村金融制度創新”中,提及了十個銀行類金融機構,分別是大中型商業銀行、農業銀行、郵政儲蓄銀行、農業發展銀行、農村信用社、村鎮銀行、縣域中小型銀行、金融租賃公司、小額貸款公司、新型農村合作金融組織。對這些機構如何發揮支農作用,都做了方向性的規定。從政策引導看,過分夸大新型農村金融組織競爭作用的“鯰魚效應”說法,以及嚴重誤讀農村金融基本事實的“湯水效應”說法,都不再作為農村金融布局的參考。“十龍治水”的新局面,讓我們依稀看到了多層次、多元化、廣覆蓋的普惠導向的金融支農政策體系。
這一體系中對農信社的服務定位是:“增強農村信用社支農服務功能,保持縣域法人地位長期穩定。”如何讓農信社在多元化競爭格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就成為縣聯社法人擺正地位、甚至是存是廢的關鍵。或者,未來的政策需要不再首鼠兩端,要么坐實,要么撤銷,而不是年復一年地泛泛要求“保持縣域法人地位長期穩定”。這些都會使農信社在多年風雨飄搖中,不再重復“走了太陽來了月亮,又是晚上”這樣的老故事,在分類處理中看到深化改革的新曙光。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