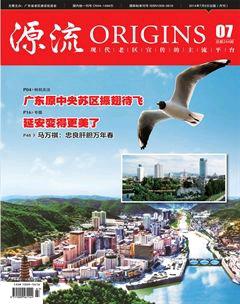滄海桑田話服裝
王貞虎
上世紀50年代初,風氣丕變,雙排扣的“列寧裝”和寬松式的“中山裝”成為時尚,西裝則被打入十八層地獄。當時穿著西裝會被人視為“資產階級”,一般人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
以南粵地區為例,舊日留存的西裝,呢絨質料的,會請裁縫改制成“文裝”(孫文式服裝,直領),只需把翻領改成直領就行,或者縮小改成女裝;夏天的白色薄型西裝,泰半壓在箱底,由它變黃;稍為破舊的,就成了拾垃圾的或干粗重活兒的工作服,恰似近年的民工穿著仿冒迷彩服。
令人困惑的是,當時流行的一部蘇聯電影《幸福的生活》,展示集體農莊的農民,恰是穿著西裝開著拖拉機種田,卻成為中國人對幸福生活的向往。
然而,無論城鄉,日常生活中卻保留著“唐裝”,沒有被視作封建、落后。不過,沒有人會穿著唐裝到機關、學校和“正規單位”上班(下班聽便);在各種店鋪工作的,則無拘。中醫、熟藥店伙計、跑江湖賣武的,更是名正言順。
南粵地區,天熱時人們都愛穿黑膠綢唐裝。居家和走路時,風涼颯爽且不黏身;農民在田里作業,喜歡它吸汗,快洗易干。青年女子穿著一身細花“大襟”唐裝,踏著木屐款款而行,更顯婀娜多姿。過年時,人們穿著一套薄花呢唐裝,或者一件薄薄的綢緞面唐裝絲綿襖,雍容而帶喜氣。
但是,當時銀幕上的壞人形象,不少就是身穿黑膠綢唐裝,戴副墨鏡,歪戴盔帽,也是叫人困惑。
據說,一次粵人在廣州球場觀看足球比賽,踢到激烈處,忽有一位觀眾激動地站起來,振臂高呼:“(把球)交給楊子旋!”此人身穿一套唐裝,腳上一雙球鞋,如此搭配甚是滑稽。楊子旋是當時著名射手。
穿唐裝褲可以不必系腰帶,只需左面往右一搭,右面往左一搭,再加一卷,就可以系住褲子(因為這三個動作,上海人戲稱唐裝褲為“一二三”)。
表姐小韻曾給我講過一個關于唐裝褲的笑話,我們一起笑了好些年。小韻的伯父有一次穿著汗衫和黑膠綢唐裝褲,在褲頭卷入一張兩毛錢紙幣,趿著拖鞋,施施然走到巷口理發。要付錢時,翻開褲頭,卻沒見到那張兩毛錢紙幣。心里一急,手一松,唐裝褲脫落,理發攤里的人哄堂大笑。他又羞又惱,只好和攤主商量,回家拿了錢送過來。
上世紀60年代初,上海已很流行“中裝”。“中裝”限于冬天穿的棉襖,特別是穿在棉襖外面的“罩衫”:棉襖易臟,罩衫則可以換洗。“中裝”棉襖比較寬大,立領,對襟一行暗扣,取代了傳統的襻鈕或撳鈕,左右兩側腰際有暗插袋,不用唐裝的四個貼袋。這種中西合璧稱為“中裝”的棉襖,無疑是上海人獨特的革新。從50年代到80年代,看到穿著這種“中裝棉襖”的,就知道是上海人。
“中裝棉襖”組合中,翻花樣主要靠“罩衫”。罩衫有市售,也有不少人是自家縫制。男式以藍布為主,間以淺灰或深灰色,十分單調。的確良問世后,也有不少人改用的確良面料,不但穿著更顯“挺刮”,而且易干,晚上脫下洗了,次日又能穿上。
女式棉襖和罩衫分別有兩種,一種與男式全同;另一種稱為“中西式”,主要是把袖子做成“裝袖”,更西式化,中式成分似乎就只剩下高企的立領了。但“中式”古雅,“中西式”秀雅,二者各饒韻味。
女式罩衫爭奇斗艷,由各色花款的花布、人造棉、的確良制成。穿著中裝,再圍上一條羊毛圍巾或羊毛領套,頭上戴著自己編織的“滑雪帽”,滑雪帽在頜下打個結,露出兩條飄帶,英姿颯爽,即便在文革期間,中裝也沒有遭禁。
此時,女士們更是進一步“翻花頭”:60年代中后期,忽然時興把花襯衫的領子翻到罩衫的立領外頭,于是立領變成了“相拼”花色小翻領,這個招數,錦上添花,畫龍點睛,又為中裝棉襖平添了些許艷麗嬌俏。
在那物質匱乏和百般禁忌的年代,上海女士們憑著心靈手巧,竭盡全力把自己打扮得亮麗高雅。冬日的上海,馬路兩旁的法國梧桐樹都是光禿禿的,顯得蕭瑟,而女士們的中裝把這個城市妝點得繁花似錦、春意盎然。
那年頭,上海男女老幼都穿中裝棉襖;天寒外出,外面可以再加一件“風雪大衣”保暖。
改革開放以后,冰封漸解,長頭發、交誼舞、西裝領帶……逐漸在電視節目亮相,一點點透露開放的消息。80年代開始,三件套西裝加領帶開始作為正裝流行;再后來,羽絨衫興起,中式服裝日漸式微終至退出主流生活。
80年代中期,一支中國代表團首次出國洽談合作專案。在西德一個萬把人的小鎮阿侖,晚上有年輕酒鬼攔路,作手勢問中國人討錢買酒喝。東道主后來玩笑著說:“你們都穿西裝,他們錯把你們當日本人了。”
如今,西式服裝在中國已經占絕對優勢,國人不但沒有自己的民族服裝,連本來多少帶點兒民族特色的服裝如“唐裝”、“中裝”等都付闕如。有時到一些偏僻的小鎮游玩,在幽深寂寞的小巷子里,時或可見個別留守老人,穿著舊時中裝棉襖,蜷縮在夕陽深處,無語話滄桑。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