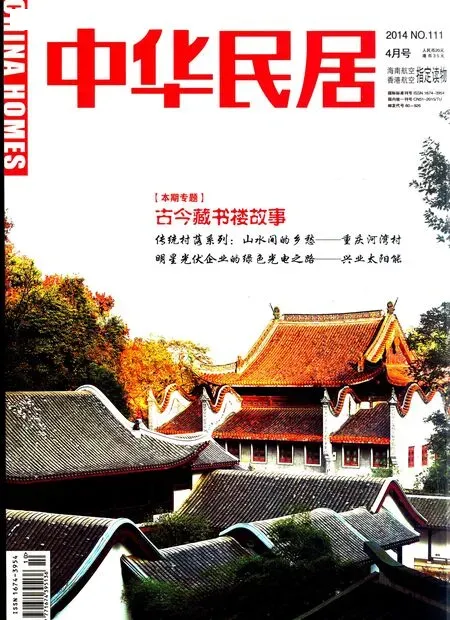唯水而居
撰文/嘎瑪丹增
攝影/姜 曦 羋友康
唯水而居
撰文/嘎瑪丹增
攝影/姜 曦 羋友康
在藏區,眾生平等不是口號,愛護山川萬物的意識,和大地一樣古老,一直在血管里汨汨流淌。這種愛,源自先人對宇宙世界的理解。人與自然萬物是共生關系,誰也不比誰更高貴。

精神圖案MENTAL PATTERN
這是瀾滄江上游的扎曲河畔翁達崗村。
村內有夯土墻梯形平頂單層建筑,除了門洞,開有幾孔內大外小的斜向天窗,沒有檐廊,屬過去時代的建筑式樣,于今已經很難見到。以前的奴隸主或部落頭人的住房,大概也是這個樣子,唯一的差異,無非土夯墻和原木墻的區別。
才讓一家及其祖先,在這樣的屋子里生活了很多年。有爐灶和火塘的屋子是才讓一家人日常起居活動的中心,吃喝睡均在其間完成。這個半農半牧的家庭,對物質生活的理解和需要,還停留在輕物輕身的傳統里。文明世界對物質的貪婪和占有欲望,還沒有侵入才讓和家人的精神肌理。
才讓把我們引入他家經堂最初那一刻,我徹底傻了:佛和神像居住的房子竟是如此富麗堂皇!木板墻壁,羊毛地毯,實木大門,整潔得一塵不染。一溜數十盞酥油燈全亮著。佛、護法神像、唐卡、銀銅供器,在明亮的經堂熠熠生輝。跟才讓家黑漆漆的居所天壤之別。在西藏,信仰是一個事實,這個事實就是:很多人活著來世,對今生的物質生活,不像我們那樣貪得無厭。
翁達崗村制作銅像的歷史非常久遠,大概可以追溯到藏傳佛教嘎瑪嘎舉派祖寺在烏冬山最為興盛的時期,也就是公元15世紀前后。尼瑪澤仁一家是翁達崗率先致富的家庭之一,2002年,在昌都買地蓋了一棟四層樓房,并于2004年舉家搬離了扎曲河谷。前不久,這個工匠村村民全都搬進了有玻窗檐廊的三層樓新居。
仁增部長安排我們采訪扎曲河畔依靠傳統手藝率先致富的巴桑家。兄弟三人只娶了卓嘎一個妻子。一妻多夫在扎曲的遺留,更多的涉及地域環境和民俗傳統。人口相對密集的扎曲河流域,土地和牧場資源極為有限,為了實現家庭財產的積累和余足,兄弟共妻可以不分家立戶,財產和資源因此得以完整傳續。這樣的傳統和扎曲河一樣久長。

巴桑家的三層樓房,獨門小院,石木結構。根據功能使用劃分明確。一層牲畜房,二層廚房和居所,三層經堂和客房,二、三層有走廊。玻璃窗的大量使用,使得用于一家人吃飯和接待的屋子,寬敞明亮。有靠背的長椅沿墻線安放,均有羊毛坐墊,上面的圖案拙樸生動。茶幾上擺滿了風干牛肉、奶渣、卓馬,康巴點心“卡賽”和各樣水果,甚至還有維維豆奶、紅牛等來自工廠的灌裝飲料。我更習慣咸味的酥油茶,在蔬菜和水果無法生長的高海拔地區,酥油茶有替代作用,可以通便潤腸。
卓嘎穿著鮮亮的袍子,梳著典型的康巴女子大戶人家那種珠母發式,周身佩戴著祖傳的金銀飾品和珠寶。看上去既雍容華貴,又沉靜安詳。我知道,為了這身裝扮,卓嘎沒少花時間和心思。根據我的經驗,僅頭上無數小辮編成的珠母發式,就足以用去整夜的時間。卓嘎在廚房忙碌,對于我們的到來,一直沒有停止手中的勞動。卓嘎除了承擔一家人的日常飲食起居,照顧兩個半大不小的孩子,40多畝土地的播種收割,畜牧牛羊、待人接物等都落在了這個女子的肩頭。
巴桑家的院落在河谷草甸緩坡地帶,貼近原始森林,嘎瑪大草壩盡收眼底。河水自雪山腳下彎曲而來,一路滋養萬物,一路隨物賦形,一路隨緣就度。一條河流過混沌洪荒的大地,必然滋養出森林、草場、人和動物的勃勃生機,原本灰暗貧瘠的荒蕪大地,于是變得有聲有色。文明就這樣產生并前行,必然滔滔滾滾。水與生命和神靈有關,河流與文明的起源、發展或結束有關。一條河死了,文明必然結束,或遷徙產生新的文明;如果一種文明死了,河流依舊可能活著。這是水的宗教,還是河的哲學?一滴水留在原地,顯然走不去生的壯闊。
有幾個年輕姑娘身肩長長的木桶,穿行在細線般的亮白羊道。姑娘們應該是結伴到河邊汲水。周身穿戴得花花綠綠,金銀佩飾叮叮當當,蝴蝶樣在陽光下飛舞。
如果說才讓家的經堂,讓我在人神居所的類比中,感觸到藏區厚神靈,薄自身的存在狀態,以及信仰的強大力量。參觀過巴桑家三樓曬臺后方的木作經堂后,其精美豪華程度,我只能用瞠目結舌來形容了。門窗、柱頭、檐梁、頂棚、墻壁覆蓋精致彩繪,凡是木頭和金屬材質的供器,均雕有精美的花紋圖案。那是我在藏區,見過的最華美莊嚴的家庭經堂。也是藏區眾生匍匐大地,敬仰佛和神靈的人間天啟。
雖然,那可能不是佛所需要的儀式和排場。

神啟獵人DIVINE HUNTER
你在藏區不能隨便傷害動植物,人民群眾的覺悟都很高,一旦被逮住,會很麻煩。
即將走出沼澤,一只白馬雞突然出現在前方林間草地。理論上,應該在槍的有效射程。經驗告訴我,在這個呼吸困難的高海拔地區,要配合瞄準、預射、擊發一系列勻速動作,然后擊中目標,一點把握都沒有。
我一步步向白馬雞靠近。這種生長在高寒地帶的飛禽,除頭頂黑羽臉側緋紅,通體羽毛雪白。在地毯樣松軟的林地,有很多機會扣動扳機。白馬雞實在太漂亮了,沒舍得下手。又不愿輕易放棄,乃至于跟著走了很久。它應該早就發現了危險,但一直沒飛走,某種引領似的,始終在我的視線和射程內。我歇氣,它也留足。幾乎是無意識卻又不由自主地繼續跟隨著。林地里充滿腐殖質陰冷潮濕的氣息,呼吸越發困難了。經過一小片針葉林之后,就將走出濕地和原始森林,實在是走不動了。白馬雞也就停下身,安閑地站在一小片空地上,優雅梳理起了羽毛。我慢慢舉起槍,瞄準了它。目標、準星、眼睛三點即將連成一線,壓在板機上的食指蠢蠢欲動。
突然,我看見山上的一座石頭寺廟!我確定前一秒的視野里完全沒有一絲它的影子,瞬間物象憑空漂移一般占滿了整個眼球。高大石墻、鎏金寶頂、藍色琉璃瓦,在荒蕪貧瘠的山原,兀然挺立,一下子就撞倒了我。
我慢慢放下槍,石頭樣杵在那里。好像獵人的槍口剛剛抬起來,就撞見了微笑的觀音。
然后,聽見翅膀的煽動聲。有松針落下,在風中飄舞。白馬雞飛走了,留下一座石頭寺廟,被荒原覆蓋。
幡然如悟,烏冬山的白馬雞,是在給一個獵人神啟嗎?!
就在那里。貧瘠嶙峋的凍土邊緣,突然出現一座石頭寺廟,讓看見它的獵人呆若木雞。無論顛沛何方,歸途何處,我都記住了這個恍若隔世的遠方,因為一座石頭建筑,帶給我的神圣聯想,完全來自于荒原,神龕樣端然于胸。
嘎瑪寺建于1185年,在歷史上很有名,曾經左右過西藏的政治和宗教。作為噶瑪噶舉教派的祖寺,創建者為智悲雙運的堆松欽巴。大師首創活佛轉世制度,為后弘期格魯派達賴喇嘛和班禪活佛轉世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堅實基礎,并逐漸被藏語佛教各派沿用至今。
嘎瑪寺主殿門口,有一棵柳樹。一個僧人指著它對我說,這棵柳樹是噶瑪巴希從內地帶回的柳木手杖。據說大師從內地云游歸來,順手將手杖插在那里,次年它生根發芽長成了樹。在嘎瑪寺的后山,見到了一池被卵石圍堵的山泉。旁邊堆有刻滿經文的嘛尼石。佛教傳入西藏以前,關于宇宙萬物的起源,人們普遍認同“卵生說”,萬物起源于空。這個卵是神卵,形似石頭。人們認知自然萬物的世界觀和人生觀,首先來自于靈石崇拜。石頭不僅身懷風、雨、雷、電、土,還以圖騰的方式,在高原統領人心數千年。也是眾山之神沿著一條河,走向東方心靈的古代背景。
“看見了吧,這就是瀾滄江的源頭”。盡管,只是瀾滄江的源頭之一,距離最新認定的吉富山那個源頭距離差不多78公里,僧侶們把它當作源頭供奉,那就是源頭。
事實上,這個水源,已經澤被嘎瑪丹薩寺600多年。雖然寺廟建筑數毀數建,水一滴滴地冒出來,從未中斷。
這個源頭,自然是瀾滄江的另一個源頭。也是我的白天黑夜,觀想和記憶的精神高地。
一滴水的旅行A DROP OF WATER IN TRAVEL
其實,應該從一條河的身份說起。一條河的產生和結束,人類至今很難給予正確定義。它被文明命名,只是開始和結束之間的地理行程,也是人們容易看見和識別的部分。
瀾滄江的源頭在青海雜多縣有多個,最新考察結果確定在海拔5224米吉富山冰融區。我們所知道的第一滴水,是從冰原上冒出來的。我在嘎瑪溝和江源一步之遙,但我沒有去看。同行者看到過扎納日根山上的另一個源頭,他說:“那源頭……常年細細地滲著水,像一只腐爛的眼。”那么神圣的地方,他這樣比喻,有悖于我的想見和敬仰。他在這個源頭,跪了下去。“未來的大河就從石頭下面淚水般冒出來。”如果我在那個地方,也會下跪。“這可是一個世界的源頭啊!”一滴一滴的水從那里出生,慢慢匯集成流,順著查加日瑪峰南坡光溜溜的山體,流到群山深切的溝谷,形成了扎阿曲掌紋般的溪流。扎曲的藏語意思就是源頭,它不是一個地理名稱,在眾水之源的青藏高原,有很多地方的河流叫扎曲。有多少源頭,就有多少扎曲。
我在敘述這個源頭的時候,其實在說瀾滄江和湄公河的共同圣母,生養萬物的大地母親,養大了東亞第一大河的第一滴雪水。顯然,僅靠最初的這滴水成不了河流,途中有了更多冰川雪原水群的加入,才有了我們稱之為扎曲、瀾滄江和湄公河的浩浩湯湯。
我沒有去看最初那一滴水出生的冰原,只是見到看上去開始像河的部分——嘎瑪溝的扎曲河。這里位于西藏東部與青海玉樹的交匯地帶,白西山麓的亞高山草甸,也是我迄今距離這條長河源頭最初那滴水最近的位置。我們來到扎曲河畔。亞高山草甸的嵩草已經枯黃,沿著平緩的河谷伸向林緣。牛羊在其間埋頭吃草,不怕生人,見到我們只是抬起腦袋,像天真的孩子樣打量我們片刻,然后繼續在草甸工作。
已是深秋,太陽雖然還在空中掛著,晃蕩在河谷的雪風刀樣扎人。河水更是冰涼寒骨。仁增和司機下到清淺的河床,牽網分立左右,沿著河岸上游拉網。扎曲河在陽光下,像一根松落的亮白腰帶,蜿蜒在舒緩起伏的草甸上,周身都在彈射太陽刺眼的光斑。遠方山頂有零星的積雪。冰原末端至林線之間的高山牧場,即將被白雪覆蓋,自然沒了牛和羊的行跡。原始叢林東一塊西一塊,鱗甲般散布在貧瘠的山體,用暗綠的蒼涼圖案,襯托出一條河的絕世空凈。蒼鷹在上,云飛藍天。軀體龐大如獅子的藏獒毛發零亂,掛滿眼屎,黑糊糊的一團,正趴在石頭上小睡。偶爾有人騎著摩托車,在土石路面飛奔,身后跟著一溜飛揚的塵煙;引擎的叫喊消失了很久,煙霧才漸漸散去。

秋天的原野
大地亙古荒寂,只有河水的聲音。水邊的藍色梅朵、咿啞的磨坊,河道中的飄木、索橋和成堆的滾石;草甸上的經幡、白塔、桑煙和嘛尼堆,以及成群的牛羊;村莊上空自由飛翔的翅膀,不用擔心飛彈的野鴿群。而最初那滴水成為河流,以扎曲河的名義走到昌都,正式使用瀾滄江這個名字,一滴水就開始了它尋歸故鄉的漫長旅行。

瀾滄江源頭之一 吉富山
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