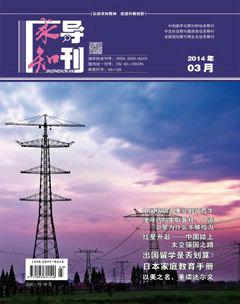如何做好傳播科學(xué)的“二傳手”
王大鵬
在排球賽中,除了有發(fā)球員之外,二傳手的作用也值得重視。如果二傳手沒有發(fā)揮“承上啟下”的作用,那么就難以形成有效的進攻,進而扣殺得分。
科學(xué)傳播是一項集體“活動”,它涉及方方面面,也涉及各行各業(yè),特別是在媒體多元化的時代,媒體已經(jīng)不再單純的是科學(xué)傳播的介質(zhì),它已經(jīng)演化為了科學(xué)傳播的一個參與者。公民在完成正規(guī)教育、離開學(xué)校之后,媒體就成為了他們獲取科技信息的重要渠道,也成為了非正規(guī)教育的最重要途徑之一。如果說在科學(xué)傳播中,科學(xué)家是“第一發(fā)球員”,那么科學(xué)新聞記者就應(yīng)該是“二傳手”。科學(xué)新聞記者從科學(xué)家和科學(xué)共同體中獲得相關(guān)的信息,在對信息進行加工編輯之后傳遞給目標受眾。在這個過程中,“第一發(fā)球員”的作用需要重視,以確保信息源頭的客觀性,科學(xué)性和可靠性。當前,科研與科普相結(jié)合的相關(guān)問題也越來越引起學(xué)術(shù)界和產(chǎn)業(yè)界的重視,同時已經(jīng)有地方已經(jīng)對科研與科普相結(jié)合的做法進行試點。在這個過程中,科學(xué)家如何在科學(xué)傳播中承擔(dān)相應(yīng)的責(zé)任和義務(wù)受到了很多的關(guān)注和探討,但是對于科學(xué)新聞記者這個“二傳手”的探討還有待深入。
作為科學(xué)傳播“二傳手”的科學(xué)新聞記者,是記者這個行業(yè)的一個分支,甚至可以說科學(xué)新聞記者還沒有成為一個獨立的“建制”。因為從國內(nèi)外的相關(guān)數(shù)據(jù)來看,從事科學(xué)新聞報道的記者還對其他議題進行報道。學(xué)術(shù)界和業(yè)界一直以來也對科學(xué)新聞記者需要專才還是通才方面存在著持續(xù)的爭論。因為媒體高層管理者認為在一個方面能夠工作出色的記者一定能夠報道其他方面的議題,因而科學(xué)新聞記者應(yīng)該是通才而非專才。甚至從近幾年相關(guān)的一些調(diào)查來看,這個爭論也一直持續(xù)著。同時也有一些新聞機構(gòu)對記者進行輪崗,這是為了避免某些記者與新聞渠道之間形成過去“親密”的關(guān)系,這也在一定程度上為培養(yǎng)專才設(shè)置了某些障礙。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科學(xué)新聞記者這個職業(yè)近年來也面臨著各種挑戰(zhàn):由于經(jīng)濟利益的壓力,一些新聞媒體開始壓縮科學(xué)報道的數(shù)量和版塊,壓縮了科學(xué)新聞報道的空間。比如1989年美國每周有科學(xué)報道的媒體達到95家,但是僅僅3年之后,這個數(shù)量下降到了44家,隨著出現(xiàn)的是科學(xué)版塊的減少和壓縮,這不僅體現(xiàn)在數(shù)量上,還體現(xiàn)在篇幅上,特別是那些小報,到了2005年,僅存24家。國內(nèi)也有一些致力于科技傳播的媒體或者改版,或者并入其他媒體。
“二傳手”如何看到“球”
在科學(xué)傳播中,科學(xué)家是信源,是渠道,是“第一發(fā)球員”,沒有了科學(xué)家,科學(xué)傳播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但是作為“二傳手”的科學(xué)新聞記者如何看到或者找到科學(xué)家發(fā)出的“球”至關(guān)重要。只有“發(fā)球”和“傳球”銜接到位,科學(xué)傳播才能更好地發(fā)揮作用。
傳統(tǒng)上,科學(xué)新聞記者們獲取科學(xué)新聞素材的渠道主要是新聞發(fā)布會,當然也包括各自所在媒體的提出相關(guān)的選題,然后聯(lián)系科學(xué)家進行相關(guān)的采訪。在收集完材料之后,記者們對相關(guān)的信息進行編輯和加工。同時針對一些社會熱點和焦點問題進行的科學(xué)報道,比如H7N9、轉(zhuǎn)基因食品、霧霾等。當這些話題成為公眾討論的熱點和焦點時,新聞媒體記者敏銳的觸角也會第一時間發(fā)現(xiàn)相關(guān)的話題,從而著手進行報道。
如果說上述方式是科學(xué)新聞記者主動看到了“球”,那么科學(xué)家自身和科學(xué)家所在的組織也會通過某種方式提醒科學(xué)新聞記者注意某些“球”(即話題)。
國外較成熟的組織和機構(gòu)都設(shè)有公共關(guān)系部門(PR)來協(xié)助科學(xué)家開展科學(xué)傳播活動,公共信息官(PIO)也會和科學(xué)家一起對相關(guān)材料進行完善并定期地發(fā)給科學(xué)新聞記者,提醒他們近期本組織和機構(gòu)的一些科學(xué)研究進展,從而增加組織、機構(gòu)和科學(xué)家的媒體“可見性”,這也有助于科學(xué)新聞記者接近和獲取新聞渠道。比如英國皇家學(xué)會(the English Royal Society),法國科學(xué)院(the French Academie des Sci-
ence),澳大利亞聯(lián)邦科學(xué)與工業(yè)研究組織(the Australian 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zation)以及美國科促會(the A-
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都要求其成員(同公眾)探討他們自己的研究工作。
這些機構(gòu)中的一些,比如美國國家科學(xué)基金會(the American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和英國研究理事會(the British Research Council)已經(jīng)出臺了傳播指南,還有一些成立了新聞辦公室或者聘用了從事傳播的工作人員,提升各種類型的活動,包括具有教育功能的網(wǎng)站、紀錄片、科學(xué)表演和研究中的志愿服務(wù)。還有一些,比如美國神經(jīng)科學(xué)學(xué)會(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Neuroscience),甚至組建了專業(yè)團隊來致力于幫助科學(xué)家同普通公眾進行交流。
另外還有一種主動獲取找“球”的途徑,那就是專業(yè)期刊。有些科學(xué)新聞記者會定期瀏覽專業(yè)科學(xué)期刊上發(fā)表的論文。通過這些論文也可以找到很好的報道話題。另外一方面,論文的作者有時候也會準備一篇科普性的材料發(fā)給記者,當然這些材料上會有“embargo”的標記。記者們也會在專業(yè)期刊對論文進行正式發(fā)表之前整理報道的材料,但是不會提前發(fā)布相關(guān)的消息。
“二傳手”如何處理“球”
無論通過什么途徑獲取的信息,科學(xué)新聞記者都要對信息進行加工和處理。媒介議程設(shè)置理論認為大眾傳播往往不能決定人們對某一事件或意見的具體看法,但可以通過提供給信息和安排相關(guān)的議題來有效地左右人們關(guān)注哪些事實和意見及他們談?wù)摰南群箜樞颍粨Q句話說,它不能決定人們想什么,但是卻可以決定人們怎么想。因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公眾接收到的科學(xué)信息并不是科學(xué)家直接傳遞過來的,而是經(jīng)過媒體加工過的信息。在這個過程中,信息的加工和處理方式會影響著公眾對科學(xué)信息的獲取。
在學(xué)術(shù)論文的發(fā)表過程中,同行評議是一個成熟的論文評審模式。經(jīng)過評議,論文中的一些錯誤和偏差可以得到修正,從而確保文章的可靠性。科學(xué)新聞記者在處理新聞信息的過程中也應(yīng)該借鑒這個模式,他們就某個話題采訪而來的材料,可以邀請其他本領(lǐng)域的專家和學(xué)者進行補充和完善,從而佐證采訪而來的材料的科學(xué)性;另外一方面,
通過引用與被采訪專家的觀點相左的觀點和看法,也能夠給公眾呈現(xiàn)出問題的全貌。
在科學(xué)新聞處理過程中,客觀性和平衡性是科學(xué)新聞記者們踐行的兩個準則。在一個科學(xué)新聞記者無法決定什么是真實的世界里,客觀性就要求這個記者進入“中立的傳播者”模式,并且不僅聚焦于正確性,而且要關(guān)注精確性。也就是說,不是去判斷一個真實主張的正確性,科學(xué)記者應(yīng)該專注于報道中對這種主張進行精確地再現(xiàn)。這個議題不再是該主張是否得到證據(jù)的支持,而是新聞渠道所說的和科學(xué)新聞記者所呈現(xiàn)之間的契合度。類似的是,當一個科學(xué)新聞記者無法判斷誰說的是真相時,平衡性規(guī)范就建議他應(yīng)該在報道中盡可能多地呈現(xiàn)真實的主張。換句話說,當正確性無法實現(xiàn)時,最好的退路就是綜合性。實際上,科學(xué)新聞記者在告訴讀者們“真相就在這里的某個地方”。
科學(xué)傳播需要科學(xué)家、科學(xué)新聞記者、公眾之間的積極配合。科學(xué)新聞記者這個“二傳手”的作用十分重要,它銜接起了科學(xué)家和廣大公眾,是二者之間的橋梁和紐帶。因而必須重視科技新聞媒體和科學(xué)新聞記者的科學(xué)傳播能力,在科學(xué)新聞記者獲取科學(xué)新聞素材方面有多種途徑,然而現(xiàn)行的實踐并不完全與相關(guān)的理論和研究相一致。筆者在與部分媒體記者溝通中發(fā)現(xiàn),很少有記者會定期查閱科學(xué)期刊中新發(fā)表的科研論文,同時也很少有記者是專職的科學(xué)新聞記者,另外一方面,雖然國內(nèi)已經(jīng)有科研機構(gòu)開始了相關(guān)的實踐工作,但是科學(xué)家所屬的機構(gòu)和組織還很少主動聯(lián)系媒體,或者幫助科學(xué)家完善用于科學(xué)報道的材料。理論上一般認為科學(xué)新聞記者應(yīng)該具有一定的理工科背景,但是目前國內(nèi)的科學(xué)新聞記者大多數(shù)并非理工科專業(yè)出身,當然這并不是說他們不能做出優(yōu)秀的科學(xué)報道,但是讓科學(xué)新聞記者知道并理解一些基本的科學(xué)還是十分必要的,這樣“二傳手”才能真正地發(fā)揮出承前啟后的作用。(來源:果殼網(wǎng))
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