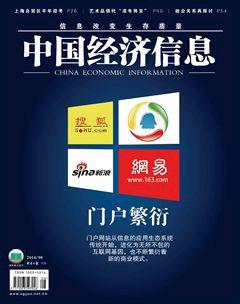飯局
曦明
一次生日宴和一場婚禮,是我4月份第一個周末的主要行程。輾轉過四號線的某站和東城的崇文門之后,導航儀的公里數定格在58的數字上。一路上,楊絮兼之柳絮,不時地從車窗外飄進駕駛室,噪雜的路況伴著1039調頻里的嘻嘻哈哈,著實是考驗人的郁悶極限呵。深呼一口氣,吹散了車窗夾孔的一片。
已經不知道是這個月的第幾次飯局了。就在此前的兩天,因為連續的加班爽約了一次大學同學的小聚,然后在大半夜接到他的電話,硬著舌頭和我抱怨,說屢請屢不到,還怎么做哥們兒。明顯是喝高了,和醉酒的人解釋實在是費勁兒,更不識趣的是旁邊還有個不知名的人在那搗亂,說“不來實在不應該”。
尤其是最近幾年,我都不知道是怎樣從吃貨蛻變為逢局必怵的。在剛走出大學校園的時候,每個月都要呼朋引伴,回到學校附近去饕餮一下那些最愛吃的館子。而現在,即使有人主動做東,都寧愿待在家里看好萊塢大片兒。
從個人經驗來說,的確不是每次飯局都皆大歡喜。在移動互聯時代,所謂的同學聚會、同事聚會有時候無非是找個地方集體玩手機,看八卦,扯咸淡。如果再碰到幾個適逢懷孕的,會把營銷學里的Push strategy用得恰到好處,保證把你的孕齡知識從ABC提升到專業四級。如果恰巧你的同學里有幾個拜金的,無非就是某某老公體貼、多金,開奧迪寶馬,去馬爾代夫或巴厘島度假之類的了。誰讓我是文科生呢,同學里十之七八都是異性,且忍且珍惜吧!
但飯局仍是難免,有被動更有主動。去掉出差和旅行的時間,其實我在北京常駐的時間也就是半年,作為一個標準的社交動物,微信、微博和QQ我一個都不少。所以友人們基本能知道我的所有動向。每次出發和回歸,都能成為我們飯聚的理由。
歸根結底,我的確是屬于一個吃貨。隨著年齡變大,在懶漢與吃貨之間尋找著一種平衡,又在發福與減肥之間不斷博弈。記得有一段時間我寫不出文章的時候,就圍繞著吃動腦筋。大半夜看大眾點評里的各種五星級評論的飯館。在這樣的情形下,每當有個新的飯局邀請,我的腦海里的兩個小人難免不爭論:是待會去,還是立刻去?
一個吃貨縱容自己的最好方式,無疑是在文化上尋根究底。食色,性也,老祖宗早就說過了。還有,陳曉卿的《舌尖上的中國》不也就是講述了這樣一個道理嘛:咱們中國人都是吃貨。
某種層次上來講,飯桌就是中國人的群體癥候。好久不見的朋友,一起攢個局,可以拉近因常年不走動而生疏的關系。馮小剛在春晚前的那個短片,從各行各業的人入手,不也是觥籌交錯、熱氣騰騰的飯桌嘛!
考量一個人的人緣好壞,飯局數量也是一個硬性標準。絕對宅男宅女等于墮落和腐化的代名詞。如果一個人天天在家自給自足,扮演孤島上的羅賓遜,那你身邊的人肯定會問你:你這么孤獨,你家里人知道嗎?
在吃上我還有一個發現,就是風卷殘云這種吃法可能是中國人專利。比如在遙遠的意大利,中高檔的餐廳就沒有什么翻臺率,幾個金發碧眼點上一盤兒菜葉子,能聊到天荒地老。我在博洛尼亞流連過的那兩周一直在為杞人擔憂:他們餐廳是靠什么活著的,如果海底撈開到這,估計沒幾天就黃鋪了。
一直想寫一部與本文同名的短篇小說,來述說飯桌上的人生百態。但是鑒于吃的文化這么龐雜,而我只是觸碰到皮毛而已,遂作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