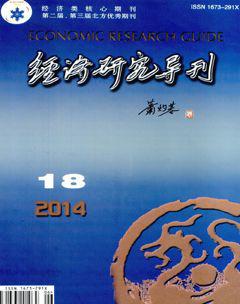亞里士多德的德行思想及現實啟示
摘要:亞里士多德的德行思想既是一種倫理學理論,也是一種倫理學實踐,亞里士多德強調德行源于人的理性,它要求道德與行動的統一。德行指向終極的善,這終極的善不是異于人之外的超驗準則,而是存在于人們追求德行的過程之中,善的目的與追求善的過程是內在統一的。亞里士多德的德行思想對當下的公民道德建設以及學生德育教育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
關鍵詞:德行;善;道德準則
中圖分類號:D64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4)18-0207-02
亞里士多德以其著作《尼各馬可倫理學》使倫理學從哲學中獨立出來,而其最主要的思想就是關于德行的思想。在此之前的古希臘哲學家或將德行融于神性之中,或將德行融于現世幸福中,而沒能將德行作為獨立的理論進行研究。很明顯,德行是指向作為人的道德生存層面的,而人具有自覺的道德意識是作為理性人的獨有特征,這樣,由理性去關照德行而不是由經驗乃至信仰去關照德行是由亞里士多德首開先河的。
一、德行的內涵
德行,顧名思義內含著兩個層面的意思,德性以及行動,德性是指向實踐行動的德性,而行動是以德性為理論基礎的行動,故而這里的“德”與“行”是不可分割的有機統一體。亞里士多德曾這樣來定義德行:“所謂德行就是使一個人好并使他的實現活動完成的好的品質。”[1]對這一定義進行仔細分析不難發現,德行的本質是指向人的品質的,也是一個人的品質好壞的風向標。德行的認定首先依賴于如何認定一種品質是否具有德行,這需要人的理智需要人的理性能力,這也就是如何認識德行為“真”的層面。光是認識了何為德行的品質還是不夠的,就像一個人光有成為有德行的人動機還不足以證明這個人是一個有德行的人,還要訴諸行動并且在行動中實現出來德行的品質。所以德行除指向認識德行之“真”的知識層面最根本的指向則是使德行上升到“實現活動”的實踐層面,這也意味著亞里士多德倫理學從一開始就具有實踐哲學的性質。
作為理性的人是行動的人,不是任意去行動,而是按照某種尺度和標準去行動,人的這種行動的根本動力不是來源于外在的強制而是來源于內在的自覺,顯然這是作為道德人的內在固有屬性。亞里士多德認為人天生就適合過群體式生活,他曾指出人天生是政治的動物也是在這個層面上來說的。交往必然是一種實踐性的活動,無論交往的主體是否有等級差別,交往行為本身需要一定的原則來規約,當然法制層面的規約是必要的,但法制是作為外在強力層面來規約人們的行為,而從根本上說是需要一種內在自覺層面的規約,這就指向人的德行。一定要明確指出的是,亞里士多德的德行觀絕不是超越于人們的交往行為之外的一個先驗的理論體系,也不是一個冷冰冰的外在原則約束人們的各種交往行為,而是從人們交往過程中生發出來的內在德性品質,這種內在的德性品質往往是以一種潛在的形式存在。也就是說德行作為一種品質經過人們長久的交往中會形成于一種人類的“集體無意識”,由此來從人類的生存層面內在地規約著人們交往活動。
二、作為實踐哲學的德行思想
眾所周知,亞里士多德不同康德,康德是一位義務論倫理學家,而亞里士多德是一位目的論倫理學家。在康德看來,判定一個人是否具有德性的根本標準看這個人是否具有道德的動機,如果一個人動機不純正即使做了再善良的事情這個人也不具有德性,不能以目的的合理性來判定一個人是否具有道德。亞里士多德認為,必然要在人的行動即實踐過程中來判定人是否具有德性,而人的行動總是指向一定目的,是有一個作為行動的目標指引著人們去行動。動機是否純正完全依據于人的主觀判斷而不具客觀標準性,如果一個人只有想成為道德的人的觀念而沒有附諸實踐這個人肯定不具德行品質。這里引出了倫理學中的兩種極具代表性的理論即義務論倫理學與目的論倫理學的爭端,一個重動機,一個重行動。二者的分歧是非常明顯的,但二都有指向“善”的理論情結,康德在其德性論中將幸福與道德的融合稱為至善,亞里士多德將德行的終極目的引向“善自身”,即終極的善是最高的德行范疇,其自身決定其他的具體的善但不被其他范疇所決定。
既然德行是指向終極的善,那必然要使德行思想指向實踐的維度,從這一層面來理解亞里士多德哲學就是一種實踐哲學。亞里士多德絕不把德行僅僅囿于理論之中,當然從人的實踐維度理解德行也必然對德行進行更為細致的分析,“人所特有的實踐生命活動在實現程度上是有差異的:有的人實現的好,有的人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實現這種活動。德行就是對人的出色的實現活動的贊賞,稱他有一種好的品質。”[2]德行作為一種品質實現出來必然要付諸實踐,但因人的德行程度與實踐深度以及廣度的不同,在人們的日常交往中就會呈現出不同類型以及不同層面的德行品質。進一步劃分可知,德行分為道德德行與理智德行,理智德行形成人們對德行的正確認知以及實現德行所必需的各種手段,這些手段是為了實現德行的目的,手段僅僅是工具性存在,而目的則為根本;道德德行將我們的活動和行為引向正確的軌道,即使人們的實踐活動符合正確的目的,符合善本身。
亞里士多德的德行思想終將要轉向生活實踐層面,也即德行指導下使人們必將獲至幸福。幸福是指向“善自身”的,具有超越性的維度,即道德形而上學的維度,“那個被亞里士多德稱為‘善自身的是具體的善的終極的形而上學的實在和最后原因,也是將幸福與德性引向趨于一致的那個終極實在。”[3] 亞里士多德將幸福引向道德形而上學意在追求德行與幸福的統一,進一步說來就是將幸福納入到德行的視閾中來理解。但必需強調的是,亞里士多德絕非將幸福拉至虛無飄渺的形而上學中,而更為根本的是幸福在于人的現實活動中,不過是這種現實活動不依于具體的現實之物而依據德行。亞里士多德給幸福做了一個經典的定義,他指出,幸福是靈魂合于德性的實現活動。這樣,幸福是依據于德性而獲得的,并且是在實踐中實現出來的,這種實踐更體現于一種超驗的維度,意味幸福的實現必然向著一個終極的目的趨向,否則幸福僅浮于日常生活表面或干脆停留于外在物欲的滿足。
三、德行思想與現實的關聯及啟示
亞里士多德的目的論倫理學的實踐維度具有很強的現實關懷意義,亞里士多德之后西方在很長時期的倫理學理路是沿著亞里士多德的理論航向前行的,無論是經院主義神學倫理學還是近代理性主義倫理學,無論是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學還是20世紀人本主義倫理學的現實關照都繞不開亞里士多德所設定倫理學理論論域,以至于20世紀后期著名的社群主義者麥金泰爾在對各種倫理思想考察后感到極度失望不得不提出重新“回到亞里士多德”的觀點。進入21世紀,我們依然生活在一個道德無序的時代,人們失去了對終級的道德關懷的尋求而走向實利化,今天重提亞里士多德的德行思想是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的。
首先,亞里士多德的德行思想給我們尋找人類終級的精神家園保有很大希望。這里所說的精神家園不是指宗教信仰意義上的精神家園而是指道德意義上的精神家園,畢竟還有很多人沒有宗教信仰。當下人們缺失對道德普遍性的信仰,這源于人們對能否達成人類道德普遍性缺少信心,在很大程度上人們放棄了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對善本身的追求,或是將善本身視為一個虛無飄渺的目標而不屑于提及。其實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善并不是一個外在于人們行為之上遙不可及的空中樓閣,而是存在于人們追求善追求德行的過程之中,是內化于這一過程中的。如果我們能充分挖掘亞里士多德這一思想的深刻內涵就能明確當下人們所處的道德困境實際上是對道德普遍性充滿懷疑,更是因為人們將道德普遍性理解為異于之們交往之外的冷冰冰的準則。
其次,亞里士多德的德行思想的實踐維度使道德建設關照人的現實生存。德行不單單是理論的更是實踐的,在承認德行具有道德形而上學的指向的同時必然認識到,德行是關照人的現實生存的。當下我們國家已將公民道德建設提高到事關國家和民族發展的戰略高度的重大舉措,公民道德建設絕不是喊幾句口號做幾次動員就能實現的,而應當將道德建設與人的現實生存關聯起來,這也就意味著道德建設應當落實具體的人的現實生存上,使作為道德主體的人體認到道德是理性人的內在價值,是人之為人的根本標志。由此人們將具有普遍意義的道德準則內化到心中,并在人們交往過程中自愿遵守從而維系人與人之間的健康交往,達到提高人的生存質量的目的。
最后,亞里士多德的德行思想對當前學生德育教育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當前我們的教育中最為急需的就是對學生的德育教育,一個明顯的事實是,不是學校學生的道德現狀影響社會的道德發展而是反過來社會的道德現狀決定學校學生的道德發展,社會上諸多急功近利的價值觀在嚴重沖擊著學生們的心靈,教育工作者往往對學生的德育教育只是在外表上修修補補,根本起不到應有的實際作用。亞里士多德的德行思想給我們指出一條道德形而上的關懷之路,也即人的道德與幸福指向終極的善,沒有這一維度人們只能生存于表面,而且這一終極善是存在于人成為德行的人的過程之中。我們的德育教育往往只注重學生的外在修為,即便重內在德育教育也往往將一些具體的價值觀念強行往學生頭腦中灌輸,而缺失一種使學生人格完善向著一個更高的德性目標邁進的終極價值關照,這樣的德育教育只能使學生的心靈成長越來越片面化、表象化和功利化,應當從亞里士多德的德行思想中尋找有益的啟示來應用于我們的學生德育教育中。
參考文獻:
[1]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M].廖申白,譯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38.
[2]丁立群,等.實踐哲學——傳統與超越[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27.
[3]杜宇鵬,趙榮華.康德道德形而上學探本——以德福觀為視角[J].天府新論,2013,(6):24.
[責任編輯 吳迪]
收稿日期:2014-03-19
作者簡介:孫琳(1981-),女,黑龍江齊齊哈爾人,大隊輔導員,小學一級,從事德育教育與法治教育研究。
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