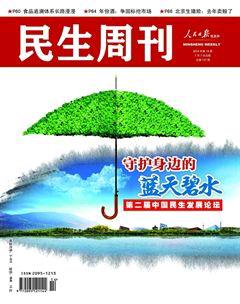環境問題形勢嚴峻
駱建華
目前,我國的環境問題可以概括為形勢非常嚴峻、問題積重難返、前景不容樂觀。
今年世界環境日,環保部公布了2013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公報顯示,74個按空氣質量新標準監測的城市中,僅有海口、舟山和拉薩三個城市空氣質量達標,超標城市比例為95.9%,尤其是京津冀地區。而美國PM2.5平均值在10微克/立方米以下,歐盟是20微克/立方米,日本是15微克/立方米。
此外,十大水系的國控斷面中, V類水質的比例達到9.0%。
環境的嚴峻形勢直接給公民健康、經濟發展帶來損失。世界銀行在2007年發布了《中國環境污染損失》報告,報告稱,每年中國因污染導致的經濟損失達1000億美元,占GDP的5.8%。然而,這一比例,到2009年上升到9%。
環境質量惡化的趨勢何時才會得到遏制?這并不樂觀,最近四五年仍然是霧霾最嚴重的時期。因為,我國重工業化時代還沒有結束,少數幾項污染物排放指標下降并不意味著環境狀況開始好轉。
預計2020年前后,中國主要污染物排放將會陸續達到峰值,污染排放全面下降的時代才會到來。2030年,環境污染有望得到全面控制。
怎樣應對環境危機?除了樹立信心外,更重要的是確定環境治理的總目標,必須注意處理好環境與發展、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中央與地方四個關系。
首先來看環境與發展的關系。事實上,我國一直不缺乏“環境保護”的理念,但改革開放以來的30余年,環境保護一直在為經濟發展讓路。那么未來30年,經濟發展能不能為環境讓路?新環保法明確規定“保護優先”的原則,這是第一次將環境保護置于優先位置。
其次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過去,各級政府通過制訂相關的法律、標準、規范等行政手段的方式治理環境。現在,可以引入更多的市場手段來保護環境,環境稅、環境保險、環保產業發展等方面都可以創新。
這幾年,我國已經開展了有益的嘗試,如電價中就包含了脫硫、脫硝和除塵的成本,水價中也包含了污水處理的成本。
第三是處理好政府與社會的關系。西方國家的環保歷程告訴我們,政府、企業和公眾,始終是環境保護的三大支柱。因為政府的監管力量畢竟有限,所以環境保護離不開公眾參與,需要更多地依靠公眾團體參與環境決策、環境治理。
最后是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方面。新環保法再次重申,地方政府對本行政區域的環境質量負責,意味著環境保護的主要責任在地方政府。
如果地方官員的政績觀沒有改變,還是把追求GDP作為第一要務,那環境改善的可能性將非常渺茫。環境和經濟發展之間是內在沖突的,想達到雙贏的局面非常困難。
(本刊記者陳沙沙根據錄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