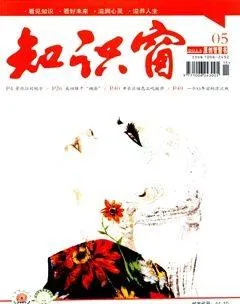安能長少年(上)
李斐洋
1.
十七八歲那會兒我和葉秋玩得特瘋。高考完那年暑假我們去北京找很久沒見面的小叔,探親是虛旅游是實。頭兩天我們很規矩地讓小叔帶著去轉了轉頤和園和北海,第三天中午我靠在沙發上昏昏欲睡,葉秋拽著我的胳膊把我拖起來:“別睡了,我們出去玩吧。”我往窗外看了一眼。七月的午后,北京的太陽就是一個熔化的巨大金球,熱度幾乎要變成液態黏糊糊地從空氣里流到地面上去。小區院子里高大的槐樹被曬得葉子打蔫兒,這個時候恐怕連隔壁那只逮著機會就往外溜的薩摩耶都不樂意出去。“去哪兒?”我坐直了身體。“南鑼鼓巷。”“你知道怎么走?”“不知道。”葉秋很不耐煩地晃了晃手機,給我看里面的地圖應用:“你去不去?”“去。”南鑼鼓巷是個好地方,聚集著各種各樣的吃貨、扛單反的文藝青年,還有外國人。那些精致的瓷器、絲綢和明信片套著七百多年的民居殼子,好像放在檀香木盒里的夜明珠滟滟生光。黃昏時分,有人坐在酒吧天臺的桌子邊彈吉他,被夕陽染成金紅色的柳條溫柔地掃著他的手肘。微風里混雜著花朵樹木和食物的香氣。一切都撩撥著文藝青年纖細敏感的神經。我和葉秋幾乎逛了所有的店。一家茶具店的櫥窗外面放著許多生機勃勃的盆栽,繡球花有半人高,碧綠茂盛的葉間托著比拳頭大些的雪白花團。我對著它們拍了好長時間,葉秋等了半天不耐煩了,強迫我把鏡頭聚焦在他身上。“你們這些文藝青年光知道關注花花草草,一點都不懂得人文關懷。”這是他的原話。
這句話可吐槽的地方太多了,但我心情很好,所以從善如流地調轉鏡頭給他拍了幾張照片。十八歲的葉秋在鏡頭里笑得很少年,張揚澄澈的少年氣息幾乎就要從畫面里溢出來了。那一瞬間太驚艷了,此后我再沒見過比葉秋更少年的人,也沒見過比那一叢開得更好看的繡球花。二十四歲這一年的末尾我決定跨越半個中國回一次H市。即使在南方生活了六七年,我仍然不習慣這里的冬天。不甚分明的四季讓人感覺生命流逝得十分混亂。沒有徹底蟄伏而后新生的過程,始終是一口氣哽在喉頭,講不出話也哭不出聲音。長期處在這種狀態讓我覺得自己逐漸趨向麻木和健忘。這對一個程序員來說或許無傷大雅,但對一個以賣字為生的人來說卻是一個足以致命的缺憾。但我必須承認不能將自己靈魂敏銳度的倒退全盤歸咎于氣候。如果非要說出一個原因,我認為于我而言寫作是一種消耗而非創造。那些東西原本就在我的身體里面晃來晃去,當我把它從身體中抽離出來變成文字后,它們就不再屬于我。很久以前聽說過一種言論,說生命中所有的東西都是有配額的。如果寫作也是其中的一樣,那么我相信自己的那份只留了一點留底的殘渣。江郎才盡真是一個可怕的詛咒。
2.
蘭因一直很不理解我的悲觀。我費了很大的勁兒跟她解釋,我是在依靠回憶寫作,而回憶總是有限的。我不是七八十歲寫回憶錄的老人,有很長很長的年歲可以去追憶,有很多很多的細節可以去捕捉……刨去我重復的學習時光和還沒有完整記事的幼年,我的手里大約只攥著十來年的光景可以肆意涂抹,這就是我寫了三年之后開始寫不出東西的原因。“那你可以去創造新的回憶啊?去旅行、采風,甚至直接走到大街上跟人聊天,干嘛要守著過去的東西不放呢?”她問到了問題的關鍵。我想了很久,然后去網上訂了一張火車票。
此刻我坐在這列因大雪被擱置在鐵軌三個小時的火車上。這是個靠窗的座位,很容易看見天色由青灰變成沉沉的黑暗。車廂里非常擠,到處彌漫著一股油膩膩酸溜溜的人味兒。暖氣倒是燒得很熱,但熏蒸著煙味、腳臭味、汗腥味……種種奇怪的味道在這暖烘烘的空氣里發酵。我盡量將鼻子貼近窗戶的縫隙,感受一點極其微弱的清爽涼氣,緩解一點自己頭暈的感覺。以夜幕為底色的玻璃上反射出車頂的昏暗燈光和我自己的臉,一張模糊的、年輕而疲憊的男人的臉,被光線扭曲,讓人覺得很陌生。我不記得自己曾經有過這么冷漠的神情,但此刻我注視著玻璃,仿佛和心臟深處的自己毫無遮攔地對視著。這種自我拷問一般的對視令人難堪,過了一會兒我就逃避地轉過臉。回憶是一種要命的勾連。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在一列大雪中的火車上突然想到了時隔七年的一次旅行,而最初勾起我回憶的紛飛雪花和那叢繡球花也只不過顏色相似罷了。
3.
對坐身材微胖,面相看起來三十上下的東北女人一直在很響地嗑著瓜子,旁若無人地將瓜子皮扔到腳下那一塊狹小的空隙。她右手拿著一本書讀得聚精會神。坐在我身旁的戴眼鏡女孩,略微好奇地問了一句:“大姐,你看的什么書?”那女人把書舉起來好讓對方看清封面,同時發表了一句評價:“寫得蠻好玩兒。”“哎呀!我也喜歡這個小說!”女孩的聲音一下子興奮起來。她看起來很文靜,這樣猛然地提高音調讓我受到了小小的驚嚇。她緊接著問:“大姐最喜歡書里面的誰呀?”“喜歡誰……譚遠吧,挺單純一小伙子。葉秋也不錯。”“我最喜歡葉秋了!葉秋是我的最愛!”這女孩子大概也是無聊透了,這會兒遇到一個相同愛好者萬分興奮,歡快地說道:“看我的手機鎖屏就是葉秋!大姐你混葉知秋的論壇嗎……”她們的聊天很快就進入了一個別人都無法插話的狀態,女人的丈夫很惆悵地看著黑乎乎的窗外。我知道那個大學生模樣的女孩子一定是網絡上我最瘋狂的一批粉絲中的一員。他們是真心喜歡著我所創造的那些人物——或者不應該說創造,我不過是把他們從回憶里拿出來,放在了電子文檔中。要是這女孩子見到了真正的葉秋,她會怎么想呢?
我很快地否定了這個假設,開始主動和東北女人的丈夫攀談起來。談一些無關痛癢足以消磨時間的話題:天氣,回家的路有多么遠,火車什么時候能到站,諸如此類。這些話題都是很安全很和氣的,唯一令我意外的是在說到回家的時候那男人露出了一瞬間傷感的神情。“都已經四五年沒回家,現在鄉下到處都在建新區,估計回去連路都不識得了。”他臉上有一絲苦笑,雖然很快就被掩飾了過去,在那短暫的時間里他看上去還是無端蒼老了許多。我一時語塞無話可說,因為我也沒有比他更強些。不知何時火車已經重新咣當咣當地往前開了。然后旁邊的女孩到站下車,上來了個平頭小伙子,后來他又下車了,我身邊的座位空了下來……長夜寂寂,我看到窗外遙遠的燈火一閃即逝,東北女人靠著她的丈夫,兩個人都發出不甚輕微的鼾聲。我坐了太久的火車,感到渾身上下每一塊骨頭都在疼,但除了上廁所和接熱水之外我幾乎沒有挪動過。已經凌晨兩點鐘,大腦疼得發脹卻沒有困意。車廂里一直有一種小聲交談引起的蚊蟲振翅般的嗡嗡聲,間或一陣子小孩高亢嘹亮的哭泣。我用大衣領子裹住自己的臉,閉上眼睛,突然感到一陣刻骨的凄涼。我想到葉秋,心里翻攪得難受,但心知肚明即便痛不欲生也沒有任何意義。(未完待續)
(作者系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13級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