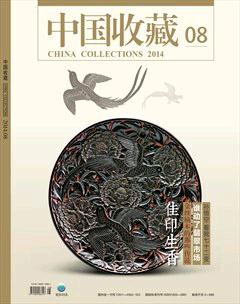篆刻皆巧致 書畫亦有情
胡西林



明清以來,隨著文人印的興起,書畫與印章的結合日益緊密,印借畫而抒情,畫憑印而顯致。吳昌碩、黃賓虹、潘天壽、傅抱石作為近現代中國書畫的大家,他們也是治印名家,他們在治印方面的造詣,也極好地闡釋了中國書畫的特質。
技高而貌樸
今年是吳昌碩誕辰170周年,大家都在紀念他。一位藝術家去世已經八九十年了,后人不但沒有淡忘他,反而越發緬懷,這不是誰都能夠做到的,可見藝術能夠深入人心,可以歷久彌新。
以大眾而言,吳昌碩最廣為人知的是他的畫,但以他本人的標格,繪畫則排在他諸項藝事的末位。他對自己藝術的排序,印第一,書法第二,畫第三。如果將詩也列入其中,則為印、詩、書、畫。但是他的印向來憑藉的是他的書法,而其書法,篆書出入石鼓文,爛熟于心,行草書則廣納王鐸、歐陽詢、顏真卿、鐘繇諸家,化為己用。這些都體現到了他的印章上,所以他的印章吸足了他的書法的養分。
而呈現在他作品中最突出的特點是氣勢,無論篆刻、書法還是大寫意的花卉,都是氣勢最勝。比如他畫葫蘆,往往圖呈半弧形,高處落筆,花葉藤蔓依勢而下,如同草書行筆,盤來繞去。五六只葫蘆各擇其位,垂枝向下,忽然最下面的藤蔓彎環一翹,筆墨的氣勢在那瞬間變成了葫蘆的勃勃生機。他作篆書也是這樣。篆書用筆圓渾,講究內斂,吳昌碩作篆書參以隸書和草書筆法,入方出圓,筆力剛健,更富律動性。若嫌不足,其勢也不外溢,而是溢向一旁的行書款題上。所以吳昌碩作篆書特別是篆書對聯,往往有行書長題,他是讓篆書的嚴謹與行書的活潑互寓動靜,互作挑逗,以此來呈現勢之不可遏。
印章也一樣,印章雖小,謀篇布局即所謂章法最難。吳昌碩印章的章法,虛實與疏密、參差與呼應常常穿插盤帶,憑著那股氣勢讓印面相生相克,情趣盎然。比如朱文“竹趣園丁”印,極得趙之謙所謂“古印有筆猶有墨”之趣,鐵筆鑿鑿,有如墨書,勢不讓人;再比如白文“無須老人”印,粗放與妍麗,渾穆與秀逸,在方寸之間交互,尤其邊底的處理,正如西泠印社執行社長劉江先生所言:“其邊均較中為低,尤嫌不足,又在印底四邊刻上無數刀痕,或在印底空處刻鑿刀痕,以增其虛。”那“在印底空處刻鑿的刀痕”,星星點點,如同雪花,為印平添空靈之趣。說到這里,讓我想起了一件事,我曾在另一本論述吳昌碩藝術的書中也看到收入其中的這方印,但是那方印上的“印底空處”竟無一點“刻鑿的刀痕”,顯然制作者不識其妙,以為那“刻鑿的刀痕”是鈐印不實留下的紕點,于是加以“修復”,弄巧成拙。
吳昌碩篆刻成就這么高,畫上鈐印卻不事張揚,如其做人,樸素謙懷。但是印文很有趣,比如他曾因人舉薦任江蘇安東縣(即今漣水)知縣,卻因不善奉迎上司而棄官,前后僅一個月,于是刻“一月安東令”印用以解嘲。又因得一古陶器,小口鼓腹,形如其人,甚合心喜,于是改字為“缶”,刻“缶”、“老缶”諸印,鈐于畫上,不僅記事,更幽默風趣。如此事例,不勝枚舉。今年4月筆者應邀往新加坡訪友觀畫,秋齋主人出示吳昌碩大幅《花卉》四屏,分別繪梅、荷、竹石、古松,一律水墨,然其用墨既有松煙,也有油煙,極盡墨趣之能事。如此好畫,鈐印他卻“不”講究,四屏之中三屏同一名章,但是押角印卻講究,分別鈐“虛素”、“歸仁里民”、“禪甓軒”、“大聾”,這是寄興的所在。比如“虛素”,語出《管子》,意為虛靜淡泊,這樣的閑章與所畫內容及表現形式十分貼切。近日又讀吳昌碩《十二洞天梅花圖冊》,甚為歡喜。此為吳昌碩晚年所作,一詩一梅,詩托言寄興,梅孤懷抱雪,詩作行書,梅若篆筆——其實那就是吳昌碩名副其實以篆筆寫梅,我們不妨任取一截作考察,都能從中透視其用筆的圓渾,中國畫之“畫”也可以稱之為“寫”,這就是詮釋。印則多鈐“缶”、“老缶”,印很古拙,一點點紅,樸素但是醒目。這樣的作品,印、詩、書、畫如何排序?
詞淺而意深
前不久,在中國嘉德2014年春季拍賣會上,黃賓虹的《南高峰小景》以6267.5萬元的成交價刷新了黃賓虹單幅作品拍賣的最高記錄,在藝術市場目前的情況下,這幅作品拍得如此高價有其道理。首先它是黃賓虹為數不多的署齡九十二歲的作品;其次它是黃賓虹最后階段作品中非常難得的大幅(177.5×74厘米)作品;再次它是在黃賓虹年逾九十之后所作山水中鮮見的以淺絳設色并且畫得華滋華贍的大幅山水;最后,當然這一切都與作品的上款有關,《南高峰小景》是繪贈他的老友章伯鈞的。這中間有鮮為人知的往來故事,本文因受主題所限,我將在另文中談及。這里我們不妨將目光投向畫幅上方的題款、鈐印,以及下幅左角所鈐押角印。
大家知道,黃賓虹是一位高壽的畫家,一生履歷豐富,學養并舉,不僅有大量畫作遺世,而且著述宏富。從鑒賞的角度來說,他不僅精于金石書畫的鑒定與古璽文字的考釋,并且傾力收藏古璽印,一生藏璽印2000余方,這使他多方面獲得營養,書法篆刻也從中受益。而于印學及篆刻史的研究尤其功不可沒,先后著有《冰虹古印存》十卷、《印說》四卷、《陶璽合證》、《龍鳳印談》、《古印概論》等,并在編訂《美術叢書》時收入相關印論文章,推動了印壇學術研究。所以他早在上世紀40年代就已經加入西泠印社,是西泠印社的早期社員。
黃賓虹篆刻宗法漢印,同時對古璽以及清代鄧石如、趙之謙都有涉及,劉江先生在《中國印章藝術史》中評其印說:“用線用刀有古拗峻折之趣,雖未能創家立派,但蒼勁簡拙,內蘊深厚之氣格,如同他的山水畫一樣,清(峻)疏朗,意在含蓄,意境深幽,富有畫理,耐人尋味。”惜其印作不多,畫上鈐印也甚簡單,多為題款之后鈐一名章,或在兩下角補一二押角印,至晚年這更成定式。所鈐名章多為白文無框“黃賓虹”和白文帶框“黃賓虹”,僅數方而已。閑章則是那兩方著名的朱文“黃山山中人”、和“冰上鴻飛館”。這與其繪畫如出一轍,不飾華麗,在黑白之間求雋永,求渾厚,以至無限。
《南高峰小景》則是黃賓虹的晚年特例,所繪是老人胸中的審美山水,故得如此氣韻。須知,當年黃賓虹棲霞嶺畫室里的畫桌并不大,僅似一書桌而已,作此大畫對老人的折騰可想而知。畫得隆重,鈐印自然也要隆重,題識署款之后,鈐起首印、名章并閑章二方,這幾乎是他90歲之后常用印的全部。與之相仿的還有一幅作品,這幅作品現藏浙江博物館,也是大幅(150×82厘米),也是繪西湖,并且取景的角度與《南高峰小景》也相仿佛,就是那幅著名的《宿雨初收》。兩幅作品所繪時間相隔不到一年,《宿雨初收》偏重墨色,花青鋪陳,畫得渾厚華滋,蒼茫而有生氣,是黃賓虹的晚年杰構。《宿雨初收》也是題識署款之后鈐起首印、名章并閑章二方,且同為上述四方。這并非偶然,他自知這樣的作品會傳世,兩方閑章并舉,“黃山山中人”藉里,“冰上鴻飛館”記懷。特別是這方“冰上鴻飛館”,刻于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時,印面內容據賓虹老人當年與石谷風所言:這印語中“冰鴻”二字是我的名字,我羈居舊京困于淪陷區整整八個年頭了,現在日本國投降,我重獲自由,可以像大雁一樣南飛了。就是這個原因,這兩方印成了老人晚年最喜愛的閑章,鈐用終身。閑章不閑,這樣的閑章是鈐給后人和歷史的。
磅礴而獨到
在潘天壽當年擔任的諸多社會職務中,有-個是西泠印社副社長。或許有人以為這是因為潘天壽在繪畫領域取得的突出成就而獲得的一個名譽職務,其實不然。潘天壽是一位天賦極高的藝術家,幼年時候即酷愛繪畫、書法和篆刻。1915年入杭州省立第一師范學校,這是近代浙江教育史上一所赫赫有名的學校,前身即魯迅當年任教過的浙江兩級師范學堂,人文和藝術氣氛濃厚,業師中便有經亨頤和李叔同。經亨頤是校長,李叔同為音樂和圖畫教師,他們學識淵博,而且都擅書法篆刻,潘天壽深受影響。后來他又在上海拜吳昌碩為師。潘天壽治印,青年時所作方正平穩,端莊沉雄,走的是漢印一路。新中國成立之后則隨著繪畫的變法印風也變,無論書法還是篆刻都挾著一股磅礴氣勢,章法不落常套,筆法意趣醇拙,刀法艱澀遒健,表現出與眾不同的強烈個人面貌。非常可惜的是他刻印作品不多,因為“自己要畫畫、寫字、作詩、刻印,又要教書、研究史論,還要寫書,精力太分散,時間也不夠用,決定放棄一些項目。中年以后,主攻繪畫,刻印較少。”(與劉江語)但是打開一部《潘天壽印存》,從所收近百方潘天壽自刻印章中,不難感受所呈現出來的大家風范。而他在畫上鈐印的嚴謹,更值得后人學習。
我們以大家熟悉的《春塘水暖圖》為例。《春塘水暖圖》是潘天壽的大幅作品,縱248.5厘米,橫102厘米,豎幅構圖。繪一牛匐水,牛角橫犄,目光溫存,眼神里充滿了勞作后獲得歇息的滿足。身后是巖崖巨石,上有山花,爛漫蔥籠。畫左中側有題識:雷婆頭峰壽者指墨。但是顯然潘天壽發現題錯了,因為此畫并非指墨所作,而是筆墨繪成,于是在畫幅上端以古隸再題,糾正此說。但這并非當時發現,而是隔了二三年之后才發現的,因為畫上所署時間為“六一年初暑”,而在1963年7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潘天壽畫集》中這幅畫的上方還沒有補題,左下角也沒有押角章“知白守黑”。也就是說,《春塘水暖圖》最初是單題并只有“雷婆頭峰壽者”下面那方白文“潘天壽印”。這是恰當的,因為“雷婆頭峰壽者”六個字題在中側的巖崖上,古拙如同摩崖石刻,非常妥貼,如果不是那個錯誤,上方不題本無妨。但是題了就要鈐印,于是這幅畫有了三處鈐印,即右側的“潘天壽印”、上方的“潘天壽”以及左下角的“知白守黑”。三方印,大小不同,朱白有別,分擇三個方位,構成上中下三角等邊關系,于視覺既養眼又停勻,恰到好處。那么三方印出自何人之手呢?白文“潘天壽印”出自老友、西泠印社社員諸樂三之手,1938年刻,潘天壽非常喜歡,用了一輩子;上方的朱文“潘天壽”為其本人所刻,作于1961年,其時因為他常受政府委托畫各類布置畫,“畫完后,常缺少與畫相配的內容與較大之印,請人刻一時也來不及,于是抽空又自己動手刻了幾方,以補畫面之需。”(潘天壽與劉江語)這方就是其中之一。左下方的押角章“知白守黑”則出自他的另一位老友、也是西泠印社社員的余任天之手。潘天壽藝術眼格極高,囑人治印,印家必有獨到之處。此印古隸朱文,平直的筆劃中穿插斜筆,既大膽也大放,別有一種生趣。印側有邊跋:己亥十二月,天壽道長正刻,天廬。又跋:知白守黑為天下式,見老子。天廬又刻,辛丑。己亥為1959年,辛丑1961年,可見印家之費心,歷三年而呈潘天壽。此印極合潘天壽美學主張,為其晚年常用閑章之一。
雄渾而常新
與潘天壽一樣,傅抱石也是西泠印社社員,并且也是入社當年即被選為西泠印社副社長。或許也有人以為,傅抱石也是因畫名而獲此殊榮,其實也不然。回溯傅抱石的童年可知,他其實就是從刻印開始走上藝術道路的。他是江西新余人,生于南昌,因為父親早逝,家境貧寒,靠母親為人修傘維持生計。當年在母親的傘鋪左右鄰中分別有一家刻字攤和裱畫店,刻字攤主人姓鄭,傅抱石經常在這兒看人刻圖章從而引發興趣,并因為聰敏得到這位鄭姓手藝人的喜歡,于是教他許多刻圖章的知識,包括從《康熙字典》中識讀篆字。裱畫店則勾起了他對繪畫的興趣,尤其店里一位左姓師傅對石濤作品的修復本領,讓傅抱石產生了對石濤作品的喜愛和對石濤的崇拜。但是無論是刻章的鄭師傅還是裱畫店的左師傅,都一定未曾想到,當年家境貧寒的少年長生(傅抱石兒時名長生)后來竟然一生不離篆刻,并且出落成為一位大畫家。
傅抱石治印入門于民間藝人,脫胎卻是在漢印,并且因為他對趙之謙、黃士陵的喜好,構成了他的印章布局穩重、奏刀雄渾又不失俊逸活潑的面貌。名章之外,他喜藉印紀年,又常常借印抒懷,托印言志,伸張畫學主張。前者如“一九六O”、“甲辰所作”、“癸卯”等,后者如“蹤跡大化”、“其命唯新”、“往往醉后”、“抱石得心之作”等,這樣的印鈐于畫上,不僅互補了畫面,也促進了畫的詩性表達,而詩性表達是傅抱石繪畫的重要美學特征。
1961年,傅抱石曾赴東北寫生,并創作了一批描繪東北山水的畫作,這批畫作呈現了傅抱石畫風與技法的新的進展,《林海雪原》是其中最為優秀的作品之一。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傅抱石之前所作山水都以江南或者四川的山水為描繪對象,而畫東北山水則為第一次。“長白山是不以峰巒取勝的,雄渾闊大,山頂積雪,的確氣象非凡。主山以外,盡是一望無際的林海”,“山的起伏不大,曲折不多,加上寸草不生,除了白的積雪,無非是黝黑的石塊。”(傅抱石語)對象變了,繪畫的手段自然也要變,但是如何變卻讓傅抱石苦思瞑想。
東北山水不以高峻稱奇,而是廣袤闊大,“蒼茫”是它的特征。顯然傅抱石抓住了這個特征。畫幅橫展,平遠構圖,以東北最多見的紅松為主要描摹對象,拉于近景,濕墨點簇,一種渾淪即現眼前。中景遠景則花青墨染,層層鋪展,至遠處是皚皚雪山。這種表現看似平常,卻有渾厚蒼潤的效果,恰到好處地表現了無際林海中“蒼茫”的意象。若以他獨創并常用的“抱石皴”繪之,當然可以輕車熟路,但那不符合東北山水特征,亦復蹈既有舊轍。于是畫上林海,蒼茫而有層次,山不高大,卻更雄渾,可謂平中見奇。顯然傅抱石也得意,這從鈐印中可從看出,名章以外,另鈐多枚閑章,其中“一九六一”為紀年印,過了當年即告廢用,而“蹤跡大化”傅抱石從四十年代鈐至今日,只有得意或者筆墨有新意的作品他才鈐用,因為此印伸張的是他不斷思索的畫學主張和筆墨實踐,用了一輩子依然常用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