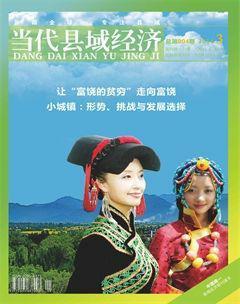“農業工”興起農村內部勞動力市場
黃健
在豫東后村調查時,發現這里很多種菜的農戶都雇人干農活,特別是在農忙時節。清晨在后村村口的道上,可以看到很多等待著雇用的人,他們大多是周圍村里來的中老年人。后村90%的農戶都是專業蔬菜種植戶,在自家的三至四畝承包地上種蔬菜,然后在后村村口賣給外地來的菜商。
這些專業種菜的農戶,大部分都是老人在地里勞作,年輕人基本上都去城里打工了,這樣的代際分工使得農民能盡可能的增加家庭年收入。但這樣的勞動分工,也使得在種菜忙碌的時候勞動力缺乏。而此時,雇用工人在自己的地里勞動成為了大部分農民的選擇。在后村,他們被稱作“天工”,也就是以天來計算報酬。后村“天工”的價格是35元/天。這對于那些農閑在家又沒法上城里打工的中老年人來說,是不錯的收入。雇用工人為規模并不大的家戶經濟勞動,并給予報酬,是當下農村非常值得重視的現象。它代表了一個新的群體的出現,我們稱其為“農業工”。
農業工是在農村內部為農民打工的人群,他們依靠本身的勞動力和農業知識、經驗為農民勞動,并按照某種協商的方式計算報酬。他們從事的工作都是與農業生產相關,更為重要的標準是他們工作的對象是農民,不論是一般農戶還是從事規模種植的農業大戶。
在鄂西北黃村,也有這樣的農業工,他們在當地農民培育香菇的過程中,承接了很多活計,其中有的是按照工作量計算報酬,也有的是按照時間計算報酬,甚至還出現了“承包制”,即由組織農業工的負責人與農戶協商,承包下一定的工作。農戶將協商好的報酬付給負責人,他組織人來完成工作。而在豫東后村,種有10畝大棚蔬菜的包全營說,他每年都要雇很多人來大棚里工作,所以他有至少10個聯系人——這些聯系人幫助他從周邊的農村找人來干活。對這些來干活的人,包全營負責他們的吃飯,但是他們都是自帶諸如鏟等工具,工作時間則是清早來,晚上回去。包全營家里,除了夫妻二人勞動之外,還有兩個老人也能干活,但是這都不夠,他的大棚里每天都有請的工人在干活。
后村種菜的農戶大多數有雇用工人的現象,只是有的雇工多有的少,有的常年雇工,有的則是在農忙實在缺勞動力時雇工。這些農業工組成了鄉村內部的勞動力市場。無論是鄂西北黃村還是豫東后村,這些為農民干活領取報酬的農業工,基本上都是外村的勞動力,這就使得這個鄉村內的勞動力市場也就更加純粹,因為雇主和雇工之間往往沒有親緣關系,也就不再是家庭之間的幫忙、幫工等包含人情性質的互助行為,而是純粹的市場交易行為。我們的調查也證實,雇主和農業工之間雖然關系融洽,但并不存在人情行為,他們實質上是市場中的雇傭關系。雖然這種鄉村內部的市場發展得并不十分完善,但是已經基本成形。農民的生產不再單純地依靠家庭勞動力或者通過村莊內部的互助來完成,而是引入了“農業工”成為農業生產中家庭勞動力的補充或者是主要的勞動力。這預示著農村內部也在發生巨大的變化,而這個變化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在村莊中務工的先聲。
農業工的興起,與小農家庭經濟的發展有關,特別是對于像后村這樣專業種菜的農民家庭,他們比種糧需要更多的勞動力,而種菜的收入較高,也讓他們有了支付工資的能力。在一些種糧的地區,也有這樣的現象,但前提都是家庭收入足夠他們支付雇用工人的工資。傳統的小農經濟在此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新時期的小農生產中,在農村內部造就了一個勞動力市場。與年輕人到城里打工變成農民工不同,這個農村內部的勞動力市場給那些有農閑時間的中老年人創造了更多充分就業的機會,無疑將對農民家庭經濟模式和農村經濟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與那些在利用農閑在農村內部打工的人不同,在皖北宋村,大量的村民每天都去村里一家蔬菜種植和加工企業打工,他們按天領報酬。宋村村民的土地都被流轉給了大型蔬菜生產和加工企業,某種意義上他們實際上是“無地”農民,更像是企業的臨時工。宋村的村民是否屬于于農業工群體,尚不能輕易斷定。因為他們的土地都已經被流轉,他們打工的對象是企業,但都是在村里,從事與農業生產相關的勞動。相比前面所言的農業工,宋村的這些打工者其實擔負著更大的風險,他們已經失去了土地這最后的保障線。
農業工的大量使用,與專業種菜這樣的農業經濟發展模式有著密切的關系。對于從事專業經濟作物生產的農戶來說,往往需要更多的勞動力。現在在土地流轉的前提下,不少種糧大戶也需要大量的農業工從事生產。農業工群體的出現和壯大,其實與農業專業化生產有著緊密的關系。傳統兼業模式的小農經濟,只需家庭的勞動力就夠用,而不需要額外雇用勞動力,也沒有能力雇用。新形勢下,農業專業化的發展,也促進了農村內部農業工群體的壯大和農村內部勞動力的發展。這對農村經濟的影響將是重大而又深遠的。
目前關于這個部分群體的研究并不多,政府的政策也極少涉及這部分群體,社會關注的程度也不高。這主要是因為這個群體和農村內部勞動力市場的發展還處于較為初級的階段。但隨著農業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小農經濟模式也將不斷發生變化,而鄉村內部市場的發育和發展將更加迅猛。
(作者系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