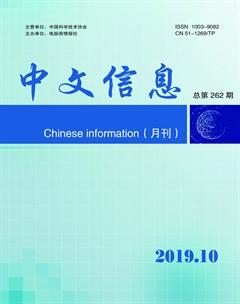游戲在幼兒教育中的運用研究
宋楊楊
摘 要:游戲在幼兒的教育中扮演著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游戲能夠吸引小朋友們的注意力,能夠調動課堂的學習氣氛使其生動活潑,能夠在很大的程度上提高教學的質量。幼兒時期是小朋友心神發展不穩定的一個階段,正是處于活潑好動的一個時期,我們可以運用于游戲來讓小朋友注意力更加的集中,更好的完善自我,能夠加強小學們對這個社會更多的認知,當然游戲不是簡單的游戲,需要根據小朋友們自身的特點來設計一種游戲,只有這樣,小朋友們才能夠真正的感受到玩游戲的樂趣,完善他們的特點。
關鍵詞:游戲 幼兒教育 應用研究
中圖分類號:G613.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9082(2019)10-0144-01
幼兒的年紀是在3-6歲般的年紀,這是一個小朋友們身心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這也是一個小朋友們關于個性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1]。在這個階段的小朋友們的好奇心,敏感心比較重,會主動的去模仿別人做的事情,逐步的形成自己的人格特征。因此,在這個時期,對幼兒的教育也就變得十分重要,這個階段的教育能夠取決于你的孩子在長大之后會是一個什么樣個性的人。游戲對于幼兒的教育放面中,能夠讓小朋友們充分的發揮一下自己的創造力和想象的能力,讓小朋友們感受到童年的樂趣,有助于今后的發展。
一、游戲在幼兒園教學中的重要作用
1.游戲可以加深和擴展幼兒對周圍事物的認知
游戲的過程是一個可以自然而然的進行學習知識的過程。這種學習方法是建立在幼兒好奇心和玩樂的基礎上的,是通過幼兒自己觀察和發現問題,得出結論的一種學習方式,而且是屬于主動性的發現式學習,這種學習方法就是現在教育家所提倡和支持,并且具有重要價值的學習。在游戲過程中幼兒是直接接觸自然材料和玩具的,因此他們可以通過這種活動自我發展觀察力和感官能力,認識各種物體的特點和不同。游戲也可以反映現實生活,如在玩具家中認識各種家具,學會如何使用飲水機;在完醫院的游戲時,可以明白看病的基本順序,讓寶寶知道不能自己亂吃藥,要上醫院讓醫生看過后才能吃藥等各種游戲。
2.游戲可以促進幼兒想象力的提高
幼兒是依靠想象力進行做游戲的,在老師的引導下,通過游戲可以促進幼兒的想象力的發展。如在做娃娃家的游戲時,老師可以和幼兒一起用折紙,折出沙發,床,板凳等家具,在制作時可以通過詢問幼兒喜歡的家具種類,然后讓幼兒喜歡什么樣的就可以自己折什么樣的[2]。因此在老師的引導下,幼兒就可以自由發揮然后制作出很多家用電器或者是其他家具。通過這種方法就可以讓幼兒在進行簡單的聯想后,經引導使想象越來越更具有目的性。在游戲之前先制作好計劃和想好結果,然后再按照計劃去展開想象的游戲,這就是創造性思維的慢慢萌芽。
3.游戲可以促進幼兒的思維創造能力
進行游戲也可以提高幼兒的思維概括能力,而且做游戲是要求要有概括能力的。在幼兒看到自己與媽媽的相同之處時,才會有自己想當媽媽的角色。通常是女孩會當媽媽,而沒有男孩子當媽媽。幼兒把這些不同事物的相同點結合在一起就是剛開始的概括。所以,在游戲時幼兒很自然的依靠辨別事物的具體形象作為思維的支柱,通過各種不同的游戲,積累了大量經驗,為思維概括打好了基礎。
二、游戲在幼兒教育中的應用策略
因為游戲本身的特殊魅力,在現在教學中被廣泛使用融合。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興趣,培養學習積極性,讓他們邊玩邊學。在幼兒教學過程中,我們往往會把游戲和教學相結合。
1.將游戲融入到健康活動中
幼兒階段正是孩子成長發育的階段,讓孩子進行一定的體育鍛煉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因為它的枯燥無聊,導致很多孩子不喜歡它甚至反感。但是如果將游戲和鍛煉活動相結合,孩子們更容易接受,因為愛玩是孩子們的天性。例如,以鍛煉學生身體為目的的“體能達標”活動,通過一年一次的測試,鼓勵學生多參加體育活動,鍛煉身體。為了增加學生參與的積極性,在設計活動項目時,特地將游戲融入到了體育活動中,以孩子們更容易接受的方式呈現在他們眼前,如:丟手絹、跳方格、過小橋、老鷹抓小雞等形式。因為游戲的融合,使得原本乏味的活動變得更加有趣充分調動了學生對體育活動參與的積極性,讓孩子們在游戲中鍛煉了身體。
2.將游戲與科學進行整合
科學性的數字活動相對較抽象、枯燥無聊,如果把數字活動和游戲相結合,讓孩子們邊玩邊學,這樣的話不僅可以滿足幼兒階段孩子對游戲的需要,還能更好的完成教學任務。例如,在中班學習“7”以內的數字教學活動中,教師可以采用“幸運闖關”的方式,將幼兒進行分組,每組分別進行闖關,成功一次即可為本組贏得一朵小紅花,最后按照贏得紅花數進行冠、亞之分,并獲得相應的小獎品。游戲讓幼兒們全身心的投入到了活動中,使的枯燥的學習變得生動有趣,幼兒們的學習也更加輕松,教學效率和質量也得到了一定提高[3]。
3.將游戲和社會活動相融合
社會是孩子們學習的大課堂,游戲是孩子對社會生活的體驗,體驗會反映到他們的游戲中。例如,端午節假期結束之后,孩子們回到學校之后,肯定會討論著假期之中發生的事。如:吃粽子、賽龍舟、插艾葉等等,于是就有了“假期歸來話收獲”這一教學主題活動,通過“端午知識”讓學生們了解吃粽子的由來、詩人屈原的故事,充分調動學生們對我國傳統節日文化的學習興趣,更有利于他們傳承傳統文化精神。
結語
綜上所述,游戲的實施在幼兒們的教育中能夠讓小朋友們在獲取基本的生活技能的基礎上,還能夠身心等方面都能夠得到更加健全,更加全方位的發展。因此,這就需要一名幼師來指導和教育[4]。而作為一名合格的幼師來說,要主動的意識到游戲的教育對于小朋友們的身心發展存在著的重要的意義和重要性,要始終堅持著幼兒在其中所占據的主導的地位,讓小朋友成為幼兒教育課堂教學中的主導者。總而言之,怎樣能夠在最大的程度上能夠調動小朋友們參與的積極性,怎么樣才能夠設計出來更多的非常具有特色的游戲,并且這款游戲是根據小朋友們自身的身心特點而設計出來的。這是現在所有的幼師都應該不斷的探索的課題。
參考文獻
[1]李祥飛.課程游戲化背景下集體教學中幼兒學習工具優化的研究[J].作文成功之路(上旬),2019,(3):33.
[2]姚翠琴.分析如何在區域游戲中培養幼兒的交往能力[J].時代教育,2018,(12):209.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8.12.177.
[3]馬斌.幼兒教學中游戲教育的應用研究[J].科學咨詢,2018,(33):156.
[4]黃爽.淺談幼兒游戲回歸自然與回歸生活[J].北方文學(下旬刊),2017,(8):171. DOI:10.3969/j.issn.0476-031X(x).2017.08.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