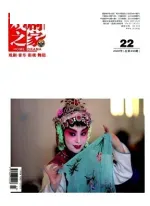宿松文南詞現狀及應對措施
錢源源,王 瑩,周冠安
(安徽大學 文學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文南詞原系湖北黃梅一帶的漁鼓小調,主要流行于湖北黃梅,江西湖口等地,清末民初由逃荒賣唱者傳入安徽省安慶宿松縣以及池州東至縣等沿江一帶,與當地民歌、小調等藝術形式相結合,形成獨具當地文化特色的戲曲形式,被稱為“文南詞”,以此與湖北“文曲戲”、江西“文詞戲”相區別。經過近三百年的發展與演變,宿松文南詞形成獨特的藝術表現形式,在宿松被保存、傳承至今。2008年,宿松文南詞被列入《第二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然而其傳承和發展境遇卻日漸式微,筆者幾次深入宿松縣進行調研,從文南詞的演出傳承、藝術形式、流傳形勢及人才培養四個方面分析其存在的問題并提出相應的解決措施。
一、演出傳承:政府官員領導,“一套人馬,兩張牌子”
筆者在調研中了解到,宿松縣文南詞保護傳承單位出現了“一套人馬,兩張牌子”現象,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文南詞的保護單位與傳承單位各自獨立,宿松縣文南詞的保護單位設在宿松縣文化館,演出傳承工作由新黃梅演藝公司承擔。無論是保護單位文化館還是傳承單位的上層領導均是政府的文化官員。文化館不參與任何演出,僅負責資料的整理與保管。文南詞保護與傳承的資金來源主要是國家、政府的資金補貼,自2008年以來,國家撥款共約一百萬元左右,這些款項被用來整理、編印存續的少數劇目,錄制老藝人的聲腔音樂,購買戲曲服裝、道具等。經調查發現,這些存續的劇目也只有少數被整理、編印出來,記錄存檔的劇目既有在“圍鼓坐唱”和燈戲的基礎上改編而成的,也有經藝人從外地引進并加入當地音樂元素混合而成的。很多古老的資料存放在老藝人的箱底被蟲蛀,或是僅僅是一人之間的口耳相傳,難以整理,因此國家所撥資金在投入到這項建設中后,便無多余資金用于劇團的建設。
另一方面,盡管文南詞是宿松縣的一個文化名片,但迄今為止一直沒有成立一個專業的文南詞劇團,現如今的文南詞演員仍然是黃梅戲演員出身,這些演員均就職于宿松縣新黃梅演藝公司。宿松縣新黃梅演藝公司由原宿松縣黃梅戲劇團在2010年全國文化體制改革中整改而來,由事業性單位整改為企業單位。新黃梅演藝公司現有員工中36人系原黃梅戲劇團員工,仍享受事業編制時待遇,改制后招5名演員,1名舞場,享受企業員工待遇,加上從退休員工返聘回5人共47人,其中演員均為專業黃梅戲演員出身,有演唱文南詞經驗的人極少,黃梅戲出生的演員難以駕馭原生態的文南詞,因此舞臺上演出的文南詞仍靠新老演員一起研討、摸索。這種一人唱兩種戲的情況,容易導致戲曲串味兒,難以達到精致的效果。
傳承單位新黃梅演藝公司目標責任書上規定其每年需完成60場次商業性演出以及70場次“送戲下鄉”的民生工程。其中在“送戲下鄉”工程中文南詞演出不多,這主要是因為農村的觀眾群基本為年紀較大的人,他們喜愛故事完整、情節性強的傳統戲目,而文南詞多以百姓生活為主,在舞臺上的表現力不夠突出。“送戲下鄉”工程,縣政府也會給予一定的資金的補助,但這些資金并支付不了“送戲下鄉”工程的所有開支。商業性演出中文南詞占三分之二,包括縣內的企業、事業單位招待,農村的紅白喜事歡慶及一些外省演出,有綜藝性節目也有文南詞專場。此外自2011年連續三年,公司都編排一個文南詞小戲參加安徽省小戲調演,2011年為《陳姑追舟》,2012年自創《巧縣令》,2013年為《蘇文表借衣》。據新黃梅演藝公司總經理陳誠介紹每年公司商業性演出所得有80萬,由于文南詞資金短缺,公司需自己抽出部分商業所得投入到文南詞的保護與發展,長此以往,公司的資金壓力越來越大,公司對于文南詞的建設可以說是有心無力,在軟件硬件兼備的情況下,卻缺少推動這些因素共同發揮作用的要素。
二、藝術形式:與黃梅戲唱腔同源,觀眾難以識別
宿松縣的文南詞與黃梅戲同臺演出時,觀眾很難將文南詞識別出來,這主要是因為文南詞與黃梅戲同出一源,素與黃梅戲并稱為“孿生姐妹”,都植根于民間文南詞因與黃梅戲在唱腔上相似,如黃梅戲所唱的“陰司腔”就是原汁原味地借鑒于文南詞的“還魂腔”。文南詞來自于黃梅一帶的漁鼓小調,而黃梅戲的起源,王兆乾先生和陸洪非先生在各自的著作中提出的三種推論,其中一種便是源自黃梅的采茶小調。因此,文南詞與黃梅戲有著不可分割的親緣關系。在宿松縣,黃梅戲和文南詞常同臺演出,當地黃梅戲老藝人會演唱文南詞,文南詞老藝人也都會唱黃梅戲,兩種戲曲時常難以區分。
黃梅戲和文南詞的發展都離不開燈戲。廣義的“燈戲”泛指包括舞蹈、雜技、音樂、說唱、幻術、武功、木偶、皮影乃至戲劇故事在內的文娛活動。在商業還未進入藝術領域的廣大農村,燈會是聚戲的主要手段[2]。安慶地區的燈戲活動格外豐富,無論是懷寧的牛燈戲、五猖戲,還是岳西燈會,尚未成型的戲曲都隨著燈戲在農村廣泛流傳。燈戲的傳播逐漸豐富了文南詞和黃梅戲的劇情和唱腔而演變成花腔小戲,最初花腔小戲在兩種戲曲的內容和曲調上都十分相似。隨著發展,兩種戲在選曲上有所側重,黃梅戲側重于民歌,文南詞側重于小曲,文南詞相對于黃梅戲顯得原始直白。如今黃梅戲在發展的過程中脫離了原生態的演唱風格,成為全國五大劇種之一;而文南詞卻發展緩慢,仍處于原生態的土腔土調階段,咬字干脆,唱腔簡約古樸。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有兩個方面:首先,黃梅戲在發展過程中兼收并蓄,博采眾長,不斷吸取其他戲曲的精華,藝術體系漸漸成熟,而文南詞卻始終停留在鄉野之中,封閉的地理環境使其未能有機會吸收其它戲曲的優秀成分。其次,黃梅戲發展到安慶地區,采取現代表演手法,并且得益于丁玉蘭、嚴鳳英、王少舫、張輝、黃新德、吳瓊、馬蘭、韓再芬等知名黃梅戲演員的推廣,加之有專業的創作家為其作詞譜曲,黃梅戲便越走越遠,將其“姊妹戲”遠遠甩在了身后。文南詞在被黃梅戲擠出舞臺后,缺少優秀藝人,創作也遭遇瓶頸,整體顯得比較粗俗、簡陋,偶爾穿插在黃梅戲中的文南詞并未被普通觀眾識別,老套的藝術表演形式也不能吸引觀眾的眼球,在黃梅戲的光環下,文南詞發展日漸困難。
三、流傳形勢:養在深閨人未識
文南詞形成至今已有三百年歷史,久于黃梅戲,但是其流行的區域并未像黃梅戲一樣蓬勃向上,反而停滯不前,處于養在深閨人未識的狀態。這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文南詞的表演形式限制;形式各異的文化大餐沖擊。
文南詞以盲藝人逃水荒,沿街賣唱的形式進入宿松地區,一個人手持漁鼓(也有敲碟子、打云板),另一人手拉四胡(另一些盲藝人以胡琴伴奏),這時的戲曲難登大雅之堂,只是逃難人的一種謀生手段。進入“圍鼓坐唱”時期,文南詞表演形式已較為完整,中間一人操琴,兩邊敲鑼打鼓,藝人演唱,此時沒有正式的舞臺,演員除演唱外,并無過多的角色裝扮和動作表演。直到文南詞與燈戲和“斷絲弦”鑼鼓結合,成為一種完整的曲藝形式,它才正式登上戲曲歷史的舞臺。
現階段宿松縣文南詞有兩種演出形式:其一是公益性演出,由國家舉辦的文化戲曲類藝術節或由當地政府主持開展,諸如“送戲下鄉”文化工程,邀請各類戲曲登臺獻藝,或組織專場匯演。這種情況下,文南詞的演出往往需要投入大筆資金,對參演人員進行培訓,購買專業服裝、道具、樂器。或以單獨的大戲登場,如2012年參加第六屆黃梅戲藝術文藝匯演的《楊馥初》;或將文南詞片段穿插在黃梅戲、民歌中表演,如江麗娜演唱的《秋江》、《竇娥冤》中穿插了幾段文南詞唱腔以及根據文南詞音樂作曲演唱的《游江》、《你說呀說呀》等。其二是商業性的演出,這種形式是在國家實行文化體制改革后流行起來的,主要分為兩個部分:一是民間自發組成的非專業劇團在農閑時走村串戶,集中在以宿松縣為中心的周邊農村地帶,應客戶要求,進行小規模演出,以黃梅戲為主,穿插文南詞。民間自發組織進行的商業流動演出,成本廉價,演出環境簡陋,以盈利為目的,在客觀上促進了文南詞的向外傳播。我們調研到的此類民間劇團有12個左右,以“群芳劇團”為例,該劇團所接演的一場演出在1000元左右,演員不上20人,其中一人負責服裝道具,一人負責炊事,主胡一人,三弦一人,司鼓一人,一般在臨近宿松縣的湖北省農村地區演出,民間劇團不享受政府的優惠政策,需要辦正規的經營類證件并記錄在案,自愿參加政府開展的公益演出。由于科技水平和傳媒多樣性的沖擊,這種民間劇團逐步走下坡路,面臨著嚴重的生存問題。二是宿松縣新黃梅演藝公司,完成政府指定的公益性演出以外,還接受一些企業公司的文藝晚會演出邀請。受邀演出時,應客戶要求有選擇性的表演節目,一般以綜藝性演出為主,特殊情況下進行文南詞專場演出。這種登上戲曲舞臺的表演,相對比較正規,有專業的伴奏,角色設定分明,演員也需要經過精心裝扮。文南詞在成熟穩定時期,屬于自身的獨立演出的機會少,常作為黃梅戲的配角登臺演出的形式是其流行區域狹窄的第一個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快速發展,農村人員大量外出,民間燈會組織困難,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村的民俗活動也出現了變異。雖然近些年來,國家對文化重視,戲曲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然而隨著各種文化大餐的輪番上演,人們可以通過各種途徑獲取文化上的補給,文南詞在宿松縣本地的文化競爭力日趨下降,缺少過去的生存氛圍和空間。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對中國的傳統戲曲文化失去興趣,稀有劇種更是鮮為年輕人知道,文南詞的欣賞群體中,難見中青年的身影。高榮生介紹,宿松縣知道文南詞的人大多在50歲以上,而真正了解文南詞的人多在60歲或更高。這就導致文南詞仍然處于養在深閨人未識的狀態,除了在宿松縣本地以及與臨縣交流,參加黃梅戲藝術節演出外,基本上不能對外發展。
四、人才培養:人才老化,后繼無人
宿松文南詞如今面臨的另一大問題是人才老化,后繼無人。宿松縣新黃梅演藝公司文南詞演員余杞敏申請為唯一國家級文南詞演員傳承人,文南詞音樂創作者高榮生申請為唯一省級文南詞音樂傳承人,他們均從新黃梅演藝公司退休回家。宿松文南詞民間傳承人大多都已作古,即使健在的藝人都年紀已高,在世的文南詞老藝人不足20人,他們已無法參加演出或教授學生。近些年來,民間的文南詞班社減少,能演出文南詞小戲的民間班社也所剩無幾,并且這些機構仍處于松散的狀態,基本沒有年輕人向民間藝人拜師學藝。近些年國家大力提倡保護稀有劇種以來,稀有劇種的傳承人為政府指定,保護與傳承部門也由政府規定,一些民間的藝人由于是農民出身,思想覺悟在一定程度上還未達到一定高度,因此就出現了民間藝人因未享受到國家、政府的補貼、照顧或照顧的不夠周到,不肯參與稀有劇種的保護與傳承,進而民間班社與專業劇團之間基本無交流,文南詞也出現了這種情況。文南詞具有地方性,由民間藝人賣唱而來,脫離民間,失去民間藝人的支持,無疑是一筆人才損失。在音樂創作上,有創作興趣的年輕人不多,即使對作曲感興趣,具有作曲天賦的人少之又少,所以文南詞的創作也處于無年輕人傳承的尷尬境地。隨著老藝人的年齡逐漸增長,能夠傳授技藝的時間越來越短,文南詞面臨著后繼無人的危險局面,人才儲備后勁不足,使得傳承岌岌可危。后繼無人的原因主要有:
第一,演出市場不廣闊,演員演出機會少。宿松縣新黃梅演藝公司在文化體制改革后,主要以營利為主,在商演中以綜藝性節目為主,雖然其中文南詞能占到三分之二的比例,但是演出的基本都是小戲,而且重復演出多,此外在承擔政府指定的公益演出中,以大型的黃梅戲為主,農村的觀眾對文南詞了解甚少,喜愛看大戲,文南詞幾乎無舞臺,僅有少數小戲用于開場。而每年從安慶黃梅戲學校招收的年輕演員,基本都沒有接觸文南詞,實際參加文南詞演出的機會也不多。因此,新培養的文南詞演員演出經驗不夠,表演的文南詞也就比老藝人遜色不少。即使培養出了能將文南詞表演的比較出色的青年演員,在大型的文南詞演出中又難以獨當一面。
第二,市場經濟的主導,青年人熱衷于追逐利益。文南詞的經濟效益小,青年人追求高效益、高利潤的職業,很少將目光轉移到文南詞上,沒有生源,就沒有培養的可能。沒有專業的文南詞劇團、藝術研究機構和研究人員,僅僅有幾個已經退休多年的傳承人,新生傳承人基本空缺,即使是專業的黃梅戲劇團也難以承擔文南詞的傳承和培訓任務。
五、文南詞發展的對策
筆者通過走訪文化部門、民間藝人,調查、采集資料發現的以上問題,是文南詞在發展過程中需要解決的重中之重,因此試探性地提出以下三點解決措施:
(一)節約人才,走劇團專業化道路
迄今為止,宿松縣一直未成立文南詞專業劇團,新黃梅演藝公司承擔文南詞的演出,這種做法造成了“一套人馬,兩張牌子”的尷尬局面,雖然是經濟、實用的發展方式,但是對于一個形式完備的劇種的發展卻是不利的。從長遠的角度來看,文南詞要想可持續發展,就必須成立專業劇團,儲備專業人才,能夠獨挑大梁、獨當一面。如今,宿松縣新黃梅演藝公司幾乎具備了成立一個專業劇團的條件,但缺少的是政府的資金扶持。文南詞屬于當地的文化特色,自文南詞申請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來,應政府的文化號召,新黃梅演藝公司一直不間斷地進行文南詞排演,取得了初步的效果,使得資金問題的解決有了可能。
在人才培養方面文南詞走人才節約型的經濟發展之路,緩解資金短缺問題。在新黃梅公司黃梅戲演員中將已經有表演文南詞經驗的演員挑出,進一步利用他們自身已有的文南詞演唱經驗傳授文南詞的演唱技巧,使其成為更專業的文南詞演員。這既解決了生源難招問題,又節約了培養新人才的資金。將節約出來的資金投入到返聘回來的老藝人身上,提高老藝人教授文南詞的積極性,不只是在必要時召回老藝人,而是長期返聘,充分發揮這些老藝人的主觀能動性,挑選合適的演員,進行專業培訓。青年演員與老藝人長期雙向互動,不僅讓老藝人有所發揮,接受系統的培訓更有助于提高演員的專業技能,使文南詞的演唱能得味兒。另外,還可以在當地招入土生土長的受文南詞熏陶的演員,將文南詞的原生態演唱方法帶入劇團,經過老師的培訓,這些演員能將文南詞的原生態韻味表現的更優異。人才走一條經濟路線,其他劇團成立的條件皆備,節約很大一部分資金,成立專業的文南詞劇團,文南詞的保護與發展更向前一步。
(二)以黃梅戲為橋梁,走本土路線
文南詞與黃梅戲并稱“姊妹戲”。發展到后期黃梅戲風靡全國,備受關注,無論是在演員上還是演出市場上都限制了文南詞的發展。從現階段的表演模式來看,文南詞的發展實際上沒有脫離黃梅戲,受黃梅戲的牽制很大。因此在宿松地區保護與發展文南詞首先要解決好文南詞與黃梅戲的關系。黃梅戲發展的成功經驗可以為文南詞所借用,但這種借用不是盲目搬用。文南詞流傳的區域狹窄,知名度不高,生存空間小;而黃梅戲是家喻戶曉的國粹,演出機會多。因此以黃梅戲為橋梁,借助黃梅戲的戲曲舞臺,在黃梅戲搭臺演出時,適時適當加入文南詞的演出,這樣不僅豐富了舞臺內容,而且也讓文南詞有了更多面向觀眾的機會。但是這種借助要適度,不能使文南詞成為黃梅戲的附庸,要通過黃梅戲與文南詞的同臺演出體現各自特色,用最直接的方式為文南詞正名。在這里尤為重要的是將文南詞與黃梅戲的藝術形式的不同突出表現,這需要更專業的表演人才。因此借力于黃梅戲是建立在專業劇團和相對專業演員的基礎上的。
文南詞與黃梅戲的唱腔及劇目相似,黃梅戲的觀眾群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文南詞的潛在觀眾群,文南詞的發展不能一味求流傳區域的擴大,脫離文南詞自身土生土長的環境,在謀求更多聽眾群的同時,更要利用好人們地域文化認同的心理,以宿松當地及其周邊文化區域為對象,走本土發展路線,有針對性地吸引觀眾,挖掘潛在的文化市場。文南詞大戲《楊馥初》為這條發展道路開了好頭,《楊馥初》是由宿松縣新黃梅演藝公司牽頭,高榮生作曲,根據民間傳說進行改編,講述清代宿松名士楊馥初的傳說故事。為了使文南詞與黃梅戲區分開來,高榮生此劇中大量加入文詞,同時融入具有濃厚地域色彩的民歌道腔,以及宿松當地的兒歌等音樂素材,在第六屆黃梅戲藝術節上得到了廣泛認同。借鑒其成功經驗,將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南詞大戲展示在觀眾眼前,加強觀眾對文南詞的認識,對地域文化的認同。
(三)豐富表演形式,以劇目帶動戲曲發展
文南詞之所以歷經三百年而更富濃郁魅力,就在于它自身獨特的藝術特色和地方文化特征,因此要立足于文南詞自身發展,豐富其表演形式,走出一條以劇目帶動戲曲發展的道路。
文南詞發展到今天,雖可以獨立在舞臺上完整地表演,但無論是表演形式還是劇目都沒有創新,面對日新月異的文化大餐,傳統的曲藝形式受到很大沖擊,一成不變的內容很難吸引觀眾的眼球。如果能利用現代科技成果從舞臺、道服、配樂、燈光等方面變革文南詞的外在形式,并不丟精髓,吸收新質,用新瓶裝老酒加入現代舞臺的燈光效果和大眾喜愛的配樂器材,搭配新潮的舞臺裝扮,就會韻味有余,讓觀眾耳目一新。
文南詞有完備的唱腔體系:它的唱腔分正本戲主腔和小曲兩大類,正本戲主腔分為文詞、南詞、平詞三類,小曲有《疊斷橋》、《觀花調》、《采花調》等五十余種曲牌[3] 。宿松文南詞以文詞為主調,文詞分為正板、慢板、就板和敘板等,后經老音樂者整理,又分為老生文詞、小生文詞、旦角文詞、丑角文詞、花臉文詞五種。南詞又分為正板、慢板、樂板三類。平詞有四板、正板、數板三種。小曲流行于民歌,曲調簡陋,但獨具特色,沿用至今。另外,文南詞大部分曲譜、詞譜都以文檔的方式記錄在案,與其它地方稀見戲曲劇種相比,這是它的優勢所在,因此文南詞的發展不應束之高閣,應該鼓勵并推動它走向民間。從優勢出發,文南詞應著重對劇本劇目的完善與重建,以劇本劇目促進文南詞的發展。首先,整修經典劇目,在此基礎上融入時代特色,形成具有時代氣息的大戲。文南詞保存至今的經典劇目不少,但這些經典劇目往往年久未經修改,很多劇目傳達出來的傳統觀念已不符合當代人的思想觀念,因此,將保存下來的文南詞經典劇目進行修整,在不改變其藝術特色的同時,對落后的文化結構進行適當修改,融入符合時代發展的精神面貌,使文南詞經典劇目成為適合大眾審美觀的與時俱進的活的經典,而不是停留在歷史的經典層面上。其次是在經典劇目完善好的基礎上,利用文南詞完備的唱腔體系,創作新劇。文南詞吸收了長江沿岸的民歌素材,有著濃厚的鄉土韻味和優美的旋律,這為文南詞的劇本創作奠定了基礎,創作和發展空間大。在現階段,文南詞的保護與傳承要以豐富文南詞經典大戲為主,以創作新戲為輔,只有當經典劇目為大多數人所熟知時,才能向外推廣新戲;也應當抓住機會鼓勵動員百姓進行新戲的創作或提供新素材,使新戲生于民間而傳于民間,有深厚的群眾基礎,才能經久不衰。
作為獨具地方特色的稀見劇種,文南詞很好地展現了宿松地方的風土民情,日漸式微的文南詞需要加強保護與管理措施,使其繼續傳承與發展下去,唯有此,文南詞才能更好地體現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魅力,為古老的戲曲藝術增添一份光彩。
[1]洪云.古韻鄉音——戲曲“活化石"文南詞[M].黃山書社,2012.
[2]王兆乾.燈、燈會、燈戲[J].戲劇研究,1992.
[3]中國戲曲音樂集成編輯委員會.中國戲曲音樂集成[G].1994.
[4]時白林.安徽戲曲音樂的源流與特色[J].音樂研究,1993(02):61-69.
[5]汪勝水,方文章.見微知著彰往昭來——東至“文南詞”的興衰[J].戲曲研究,2006.
[6] 唐彥春.文南詞文詞、正板、音樂形態與板腔體式探析[J].安慶師范學院學報,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