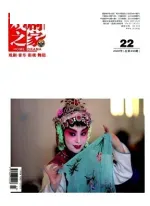二十世紀甘肅秦腔史研究現狀
張志峰 周媛媛
(西北師范大學 文學院, 甘肅 蘭州 730070)
秦腔作為一種地方戲曲,自其創立伊始,在娛樂秦地人民的同時,也起著高臺化民的作用。焦循《花部農譚》曾謂:“花部原本于元劇,其事多忠、孝、節、義,足以動人,其詞直質,雖婦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氣為之動蕩。”1.陜西省藝術研究所編:《秦腔研究論著選》,陜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9頁。.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山西省文化廳戲劇工作研究室編:《梆子聲腔劇種學術討論會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5頁。1912年,同盟會成員孫仁玉、李桐軒等以“改良社會、啟迪民智”為已任,以戲曲為手段,在“移風易俗”的宗旨下,創辦了易俗社,輔助社會教育,在歷史的歲月中閃耀著光芒。1913年,朱怡堂在蘭州成立化俗社。1926年,魏紹武與水梓,仿照西安易俗社,以提倡文藝、移風易俗、普及社會教育、改良秦腔戲曲為藝術宗旨,創辦“覺民學社”。甘肅秦腔曾在隴原大地上,高臺化民,教民真善美,普及歷史知識,但是在二十世紀之前關于甘肅秦腔史的研究較少。
首次以理論形式闡明陜西秦腔與甘肅秦腔差異的,是通渭人牛士穎(1882—1942)。牛氏在《隴上優伶志》2.該書發表于《甘肅文化》2004年第2期,后半部分缺佚。.《陜西戲劇》,1984年第11期,第14頁。中稱,“隴上梆子,亦稱秦腔,但與陜西秦腔稍異。陜西秦腔以往稱為南秦腔或關中梆子,吾甘秦腔稱為西秦腔或隴南梆子。”3.《甘肅文化》,2004年第2期,第32頁。.《當代戲劇》,1994年第4期,第59頁。并在該著“牛寶山”條下再一次重申二者的差別,“隴上秦腔原稱西秦腔,與陜西秦腔不盡相同。隴上秦腔用皋蘭音韻,陜西秦腔用關中音韻。隴上秦腔注重傳統,陜西秦腔頗多改革。至劇情、唱詞,更多差異。”4.《甘肅文化》,2004年第2期,第39頁。遺憾的是,該文自2004年發表以來,并未受到戲曲研究者重視。
甘肅演出秦腔的班子,據張慎微《甘肅秦腔隨筆》一文,也被觀眾稱為“老班子”5.《蘭州文史資料選輯》第16輯,蘭州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03頁。。由于藝術風格的差異,關于秦腔起源的論爭也逐漸產生。論爭的起源只是清人吳長元《燕南小譜》聽聞友人所說:“蜀伶新出琴腔,即甘肅調,名西秦腔。其器不用笙笛,以胡琴為主,月琴副之。工尺咿唔如話,旦色之無歌喉者,每借以藏拙焉。”6.張次溪編:《清代燕都梨園史料》上冊,中國戲劇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頁。《燕南小譜》首次將西秦腔和甘肅秦腔等同起來。1933年,杜穎陶在《劇學月刊》2卷第4期發表《記玉霜簃所藏鈔本戲曲》一文,其在介紹《缽中蓮》傳奇時,稱“末頁有‘萬歷’、‘庚申’等印記”,又兼劇中出現【西秦腔二犯】曲調,所以此后學者如周貽白《中國戲曲史長編》、徐扶明《元明清戲曲探索》,都認為西秦腔產生于明萬歷年間。
1950年2月25日,程硯秋在《人民日報》發表《西北戲曲訪問小記》一文,在秦腔演藝界產生了巨大轟動。該文以《燕南小譜》為基礎,繼續佐證了該說法,稱“魏長生所演的秦腔是什么樣子?我們不曾看見過,但從《燕南小譜》一類的書上來看,可以斷定其唱法是很低柔的。現在的秦腔,唱起來卻很粗豪,似乎不是當年魏長生所演的一類。”7.程硯秋:《程硯秋戲劇文集》,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208頁。
1982年,“梆子聲腔劇鐘學術討論會”在山西召開,將西秦腔的研究推向高峰。流沙《西秦腔與秦腔考》一文,肯定西秦腔為吹腔,是不同于陜西秦腔的,為秦腔之源。并稱“西秦腔在陜西發展為秦腔,大約是在明代末年”8.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山西省文化廳戲劇工作研究室編:《梆子聲腔劇種學術討論會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頁。。焦文斌《從<缽中蓮>看秦腔在明代戲曲聲腔中的地位》不同意流沙之說,認為“【西秦腔】即秦腔”9.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山西省文化廳戲劇工作研究室編:《梆子聲腔劇種學術討論會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1頁。,以《缽中蓮》中觀音自白“今當下界大明天下嘉靖壬午春朝”句,斷定該劇系“嘉靖元年(1522年)”a.陜西省藝術研究所編:《秦腔研究論著選》,陜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9頁。.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山西省文化廳戲劇工作研究室編:《梆子聲腔劇種學術討論會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5頁。創作,并根據唱詞推論《缽中蓮》傳奇是江南民間藝人創作,開《缽中蓮》辨偽之風。
1984年,孟繁樹在陜西原鳳翔八縣做長時期田野調查,通過采訪老藝人及有關人員,再次認定西秦腔即秦腔,在《西秦腔及甘肅調即秦腔辯》一文稱“我們沒有理由因為《搬場拐妻》唱長短句小曲這一特殊情況而懷疑西秦腔不是秦腔。”b.該書發表于《甘肅文化》2004年第2期,后半部分缺佚。.《陜西戲劇》,1984年第11期,第14頁。此文發表后,西秦腔起源于甘肅的說法逐漸沉寂。
1993年,王依群發表《<搬場拐妻>中的【西秦腔】考》,該文通過大量詳實的調查,認為《搬場拐妻》中的第一支【西秦腔】曲牌系【馬頭調】,在音樂結構上否認了【西秦腔】的存在,認為西秦腔是秦腔發展到南方后,南方人對秦腔的稱呼,并稱“《搬場拐妻》兩處標西秦腔,前者為西調,后者為秦腔。”c.《甘肅文化》,2004年第2期,第32頁。.《當代戲劇》,1994年第4期,第59頁。
1996年,甘肅籍學者王正強發表《為“西秦腔”探源尋蹤》一文,認為“‘西秦腔’是甘肅古老地方劇種。又稱琴腔、西調、隴聲、甘肅調、甘肅腔、隴西梆子等等。”3.《戲曲藝術》,1993年第3期,第96頁。此后王正強2004年在《戲曲研究》第3期發表《西秦腔再考》、2008年,在《當代戲劇》第1期上《西秦腔≠秦腔》兩篇力作,認為西秦腔不是劇種而是影戲腔調,起源不在陜西,而在甘肅,與陜西秦腔在唱腔體制、音樂風格、樂器伴奏等方面有很大的差異,二者曾在四川發生融合交流。
2007年,寒聲發表《西秦腔研究——兼對“二百年學術懸案”的破解》一文,駁論王正強“錯誤地認為陜西板腔體秦腔‘是西秦腔基礎上衍化和發展’”4.寒聲主編:《黃河文化論壇》第16輯,2008年3月版,第188頁。,收錄了二十四支鴻盛社老藝人、平涼老江湖班和西秦腔曲牌譜例,認為“西秦腔曾是一種闖蕩江湖連外演出的專業戲曲藝術”5.寒聲主編:《黃河文化論壇》第16輯,2008年3月版,第211頁。。
這些關于甘肅秦腔和陜西秦腔的論爭,都是以“西秦腔”為切口,自建國后,一直持續不斷,此消彼長,近幾年持續升溫。諸多文章證明西秦腔存在的根據就是吳長元的《燕南小譜》所載的“甘肅調”與《缽中蓮》傳奇的【西秦腔二犯】。王正強引《燕南小譜》《賭棋山莊詞話》《清稗類鈔》三書,謂“三位前人異口同聲,均言這種‘甘肅調’乃‘起于甘肅’”6.《當代戲劇》:2008年第1期,第21頁。,其實這三則材料均出自《燕南小譜》,而《燕南小譜》又系他人所說,并非作者親見。
《缽中蓮》傳奇,長期以來,研究秦腔的學者,以此為證據,證明秦腔最遲產生于明代。但是胡忌《<缽中蓮>傳奇看“花雅同本”的演出》一文,從劇本體制、劇本內容與風格角度,認定“《缽中蓮》這個抄本時代應在康熙中期創作的《漁家樂》之后(可暫時推想在1700年前后)。”此觀點先后經寒聲、陳志勇進一步考證。寒聲《西秦腔研究——兼對“二百年學術懸案”的破解》一文以《缽中蓮》第十四出有【京腔】一曲,據《都門紀略·詞場》序考訂,京腔系高腔清代在北京演出時的稱謂,其更懷疑庚申為嘉慶庚申(即1800年)7.寒聲主編:《黃河文化論壇》第16輯,山西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86頁。。陳志勇《<缽中蓮>傳奇寫作時間考辨》一文,認為《缽中蓮》是清中業的梨園整理本。關于西秦腔的起源與甘肅秦腔,還有進一步探討的余地。
整體而言,二十關于甘肅秦腔史的研究相對較少,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對西秦腔和秦腔的關系以及西秦腔起源時間的考辨上,進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由于《缽中蓮》逐漸被定性為偽作,所以關于甘肅秦腔史還有很大的空間可以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