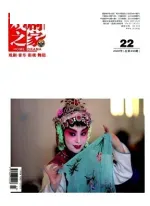《奧賽羅》中的創傷與悲劇解讀
彭家海,孔 霞
(湖北工業大學 外國語學院,湖北 武漢 430068)
莎士比亞的悲劇著作給西方文學和戲劇的發展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資本主義社會與封建社會交替初期宗教神學與人文主義的戰爭沖突中,莎士比亞以其獨到的眼光和巧妙構思批判了種族歧視和階級權力帶來的不可彌補的罪惡。《奧賽羅》的悲劇就是當時社會悲劇的例證。很多評論認為奧賽羅悲劇源于其性格,即性格決定命運,而忽略了性格的形成因素。作為一個效力于威尼斯的摩爾人,即使他已是赫赫有名的戰將卻似乎仍舊擺脫不了命運的安排。深究其因,一是種族歧視給奧賽羅本人帶來的精神創傷,造成對其自我身份認同的困惑和悲劇性格;其次是小人的嫉妒和陷害讓性情剛烈且多疑的奧賽羅陷入了陰謀,自卑和敏感讓這位悍將對自己愛妻產生懷疑,最終他因為誤殺了妻子感到內疚而殉情。
凱瑟琳銀石賽道通過一系列文本檔案收集和研究,探討了莎士比亞如何通過舞臺戲劇表現暴力事件和歷史對人的精神創傷。暴力事件涉及種族歧視、殖民統治和戰爭等,明確地表達了創傷事件與歷史之間的關系。她試圖通過倫理和政治影響等方面來展現創傷,因此莎士比亞悲劇創作也成為對歷史創傷的見證[1]。現代對莎士比亞的戲劇研究著重于表演和戲劇藝術性的研究。事實上不論是對著作本身還是戲劇表演的研究,都期望將歷史進程中的創傷悲劇重新展現,了解創傷經歷更明確地定位悲劇的意義。
一、莎士比亞的創傷意識
英國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思潮開始興起,即肯定個人的價值,發展人的個性,追求平等反對宗教神權。而此時人們對黑人、奴隸和異教徒的歧視問題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奧賽羅》的創作可以說是莎士比亞展現時代創傷的文學著作。《奧賽羅》的創作時值伊麗莎白女王統治末期,封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關系開始緊張,宮廷貴族生活日趨腐朽。外部勢力擴張和內部權利爭斗日益激烈,封建制度開始瓦解,此時正值新興資產階級開始上升的大轉折時期,人文主義在社會文化思潮的影響下開始廣為盛行。但是中世紀的英國是處于一種家長式的嚴格統治下,社會等級觀念還是根深蒂固。特權觀念和攀附權貴的思想深入人心,普通人必須循規蹈矩。隨著“圈地運動”和畜牧業集約化,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游牧民族和失去土地的農民。物價上漲和貧困問題使得當時的窮人們難以維持生計并不斷發生暴亂。在新教與舊教的交替和復雜的社會環境中,人們遭受迫害,甚至是個人的宗教信仰也面臨兩難的選擇[2]。在經濟轉型期,莎士比亞對普通社會群體窘迫生活的關注以及對政治和社會文化的質疑是其創傷意識的先驅動力。
莎士比亞時代的英國,戲劇是最為流行的藝術形式。在對莎士比亞的研究中,彭貴菊在其論文中指出了莎士比亞的戲劇語言與創傷的關系。莎士比亞劇作的創傷體現在各種創傷人格上[3],人物的塑造基本上就是時代的鏡子,正是人們對世界的認識和建構與封建傳統思想的沖突造成了人物的悲劇性格。
莎士比亞對奧賽羅這個黑人的描述多是正面的,但命運多舛的故事情節似乎還是如影隨形。莎士比亞試圖讓人們意識到人們所承受的恐懼與本應有的尊嚴,在舞臺上演繹階級政府權力下的不公正和執政者的傲慢和冷漠。而民眾就像莎士比亞喜劇人物福斯塔夫的臺詞說的那樣“普通人不過都是些商品的奴隸”。莎士比亞將注意力放在時代背景下被過度壓抑而扭曲的人格上,他能做的就是將無法重現的痛苦經歷展現出來。莎士比亞在早期創作的悲劇故事就有了種族創傷的意識,企圖喚起人們對人性和權力的思考。
二、種族創傷與創傷性人格
創傷的廣義概念主要是指人因受到暴力、災難等而受到巨大的精神打擊而無法應對,或產生偏激行為。弗洛伊德認為心理創傷是由于創傷事件對心理的破壞,可能導致創傷后的應激障礙,對大腦產生生理影響并改變未來人對壓力的應激反應[4]。種族創傷作為創傷理論發展的一部分,主要是指在歷史演變過程中,少數人因為種族差異而無辜地受到排擠和迫害。造成創傷的事件不僅有具體外在的現實事件,也有由相關人物感知和建構的心理事件[3]。對創傷事件的回應也是多種的,莎士比亞筆下的奧賽羅雖然已經身為貴族階級的將領,為異國威尼斯征戰沙場,卻始終不能得到對他人的認可。正如勃拉班修對奧賽羅所說“啊,你這惡賊!你把我的女兒藏到什么地方去了?你不想想你自己是個什么東西,膽敢用妖法蠱惑她”[5],他認為自己的女兒嫁給一個微不足道的黑人是可恥的。生不逢時的奧賽羅,不能突破自身局限的根本原因還是因為種族歧視帶來的不可磨滅的創傷。在貴族人士的口中,甚至連他的隨從將士都總是稱其為“摩爾人”、“黑將軍”、“黑鬼”,他們在利用奧賽羅能征善戰的謀略之才,卻不曾對這個效忠于威尼斯的摩爾人多一絲尊敬。
莎士比亞對人物的設定已為悲劇埋下伏筆。奧賽羅作為一個供職在威尼斯的摩爾人,受到種種歧視和排擠,為了摯愛苔絲狄蒙娜愿意放棄自由而征戰沙場。對愛情的向往和勇敢追求讓奧賽羅感覺到了他人對自己身份地位的認同,可是這段違背世俗價值觀的愛情注定是不被祝福的。“要是這樣的行為可以置之不問,奴隸和異教徒都要來主持我們的國政了”[5]這就是勃拉班修對女婿的定位,他認為奧賽羅不過是個與奴隸無異的黑人。奧賽羅珍惜愛情,更渴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讓白人認同自己對國家的奉獻。如果愛情背叛了他,那么他存在的意義都被否定了。他無法接受的,除了愛情的欺騙更多的是對自己付出的懷疑,因此這樣的故事發展必定是悲劇。奧賽羅拼盡全力尋求他人對自己身份的認同,但對白人伊阿古的居心叵測沒有堤防。他以為為國家不惜生命的付出可以換來威尼斯人對他的尊敬以及對他的愛情的認可,伊阿古卻說苔絲狄娜:“她要是圣潔,她就不會愛這摩爾人了”[5]。戰場的奧賽羅是驍勇善戰的,威尼斯元老對他戰功的表彰讓他誤以為是整個社會的接納。奧賽羅的成就感讓他自信,這本是人之常情,無辜的是他的優秀卻招來了更多的忌恨,如果他是個威尼斯白人,他的愛情會受到舉國上下的祝福,他的戰功也將聲名遠播,但事實卻是這個社會并不允許一個對國家有貢獻的異族人得到應有的尊重和幸福。
弗洛伊德認為人格發展會受到外在環境或突發事件的影響[6]。奧賽羅的創傷性人格表現在其因自卑和身份認同的問題,陷入伊阿古的陰謀并對臆想出來的事件表現出的過激反應。他困在了創傷所導致的偏執、自卑、沖動中,不敢面對問題而是選擇了逃避,始終想著讓自己的“心腹”去證明自己妻子的罪過,最后積怨成疾憤怒殺妻。面對死亡的奧賽羅不是害怕而是痛苦,因為不能面對摯愛的人死在自己手上,不能接受自己的心腹是個惡魔。故事結局讓人看到了奧賽羅是多么的偏執和殘暴,奧賽羅把對世界的不滿都歸咎到了這個為愛犧牲的女人身上,似乎只有殺死妻子才有可能撫平他的痛苦。奧賽羅在逆境中掙扎卻仍被叫做“命運”的東西無情作弄,讓人覺得既惋惜又無奈。可是殺戮只是悲劇的開端,毀滅了救贖的希望,放大了悲劇的效果。
三、創傷悲劇
在對戲劇的研究中, 帕特里克·杜根認為創傷的本質是將事件本身或生理傷痛轉移到了心理上的影響。他分析了創傷悲劇的理論與實踐,并認為社會通過媒介手段來刺激這一流派,因此戲劇也是創傷悲劇的一種宣泄方式[7]。莎士比亞文學作品的廣泛流傳,并形成莎學這一龐大學術流派,可見其作品的現實意義和影響力。莎士比亞的悲劇主要表達了對人文主義理想社會的向往,和對現實中各種阻礙社會進步的惡勢力的不滿。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開始受到重視,對人的自由和生命存在的意義進行了新的詮釋,即為自己而存在,追求個性解放、地位平等[8]。綜合所有社會背景,人文主義被人們接受卻不能實現的根本還是階級傳統思想對人的殘害,統治階級不愿意放棄自己的利益,弱勢群體在長期壓抑的環境中無法站在客觀角度衡量事情利弊,無形的創傷導致了他們思想和行為的偏激。
人文主義思潮鼓勵苔絲狄蒙娜和奧賽羅勇于沖破禁錮追求幸福,但階級勢力的傳統價值觀讓奧賽羅深陷種族歧視的漩渦,最終新舊勢力的斗爭和奧賽羅自身的悲劇性格讓這段真摯的愛情毀于陰謀。對愛情的贊譽和追求是莎士比亞作品的一大特點,以世人的普遍價值觀來設定故事情節,使讀者產生強烈的共鳴。將意料之外的事件和意料之中的結局巧妙聯系,給了人們似乎只要努力看清事實就能改變命運的錯覺。事實上莎士比亞的悲劇就精彩在此,努力地掙扎著離開混沌,卻又不幸地陷入另一個泥沼。《奧賽羅》的悲劇無關宿命論,但是在那個時代他的出身和經歷決定了命運波折。
四、結束語
愛與死都是生命里的永恒話題,無論人的身份地位如何都要面對的重大問題。莎士比亞贊揚愛情的偉大,贊同奧賽羅沖破禁錮和束縛去追求自由和愛。然而封建禮教的思想包袱永遠是人類進步的絆腳石,面對封建制度與社會輿論造成的創傷,人們需要勇敢和智慧,更需要社會大眾從思想上認同文化,從根本上改變態度。奧賽羅的悲劇人生反映了社會階級與種族的矛盾,以死終結的情結局既達到悲劇的終極效果也讓人們深刻反思種族問題帶來的創傷。莎士比亞的超前意識為后人努力的方向設定了航標。
莎士比亞通過描寫奧賽羅這個英雄人物的悲劇命運,表達了他對時代的質疑,期望人們能夠正視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帶來的創傷以及創傷對人造成的負面影響。每個時代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隨著社會文化的發展和對人文主義認知程度的加深,人們應該更多的關注和提倡人權平等,強調人性發展。
[1] Catherine Silverstone. Shakespeare, Trauma and Contemporary Performance[M]. London:Routledge. 2011.
[2] 彼得·艾克洛德. 莎士比亞傳[M]. 郭駿;羅淑珍 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0.
[3] 彭貴菊. 莎士比亞的戲劇語言與創傷記憶[J]. 廣東工業大學學報.2009.9.(6):57-60.
[4]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引論[M]. 唐譯 編譯. 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3.
[5] 威廉·莎士比亞. 莎士比亞悲劇集[M]. 朱生豪 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
[6] Sigmund Freud.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6[M]. New York:Vintage Classics. 2001.
[7] Patrick Duggan. Trauma-Tragedy: Symptoms of Contemporary Performance[M]. 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2.
[8] 唐景春. 莎士比亞的人文主義思想在其四大悲劇中的體現[J]. 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2013(140):11-12.
[9] 戴京倞. 歐洲種族文化沖突在《奧賽羅》中的體現研究[J]. 湖北函授大學學報.2011.11(24):149-150.
[10] 黃青華. 從夏洛克和奧賽羅兩個藝術形象來看莎士比亞的種族觀[J]. 南昌高專學報.2010.5(90):37-38.
[11] 胡宗鰲. 莎士比亞筆下的黑人[J]. 國外文學.1983(4):68-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