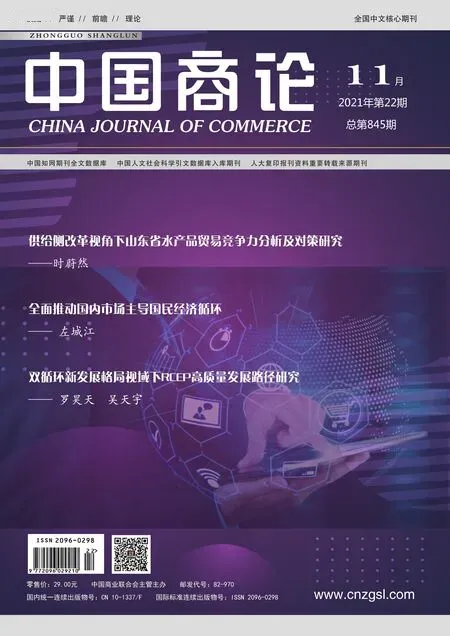中國經濟從日本經濟發展中獲得的啟示:從貧富擴大現象進行分析
青海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日語系 仲玉嬌
日本經濟是經歷戰后恢復和制度改革后迅速崛起的發達國家,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進入21世紀以來,日本經濟在資本自由主義經濟沖擊下已經表現出頹廢的態勢,并一直處于低迷期,同時出現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導致日本貧富分化現象愈發嚴峻。據有關調查報告顯示,日本“貧困率”在發達國家行列中已經高居第三位,相比10年前高出1倍。因此,了解和認識日本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中出現的貧富問題的現象,為解決中國經濟發展出現的貧富分化現象提供了較好的借鑒意義。
1 日本經濟與中國經濟發展的異同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經濟先后經歷五次不同大小的經濟危機影響,包括石油危機、泡沫經濟危機、亞洲金融風暴、互聯網危機及最近的金融次貸危機。其中對日本經濟造成最大影響的是1989年的泡沫經濟大崩盤危機,使日本經濟發展倒退了20年。隨后,世界經濟危機依然重演,日本經濟也經受著極大的生死考驗,從1989年到2000年底,日本經濟平均指數縮水70%,住房價格累計下跌40%,商業用地價格下跌60%左右。雖然這些觸目驚心的數字對很多國家來說是致命的,但對于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的狀態中卻創造了一個奇跡,在2000年,日本經濟GDP總量40789億美元,人均GNP為37528美元,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
今天的中國,全世界都可以看到這三十年中國經濟的變化,一直保持高漲態勢的中國經濟總量已超過日本成為第二大經濟體,并成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而且所謂的“中國經濟模式”也為很多國際學者追捧。從這些表象可以了解,目前中國的經濟現狀與日本20年前的經濟狀況非常的相似,這種“驚人的相似”中,房地產為首的資產價格飆漲和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更讓人們疑問:“中國經濟發展會不會成為下一個日本?”這也是很多國內經濟學家擔心和經常提起“中國重蹈日本經濟覆轍”的基本邏輯。提出這種假設的前提是對當年日本經濟出現危機后該如何采取更合理、更穩健的經濟政策進行假設,但事實是不可以假設的,人們需要擺脫一味評論經濟政策得失的層面去了解日本經濟與中國經濟發展的異同,可以從兩個國家的收入水平和貧富差距出發,分析經濟發展的狀況。因為,經濟的發展會導致社會資源分配不均,收入差距擴大既是經濟增長的原因,也是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不可兼顧的必然結果。從經濟學中衡量貧富差距的標準來看,在過去20年間,日本的基尼系數指標一直處于0.27左右的正常指標中,中國的基尼系數指標常處于0.4以上的警戒狀態,因此可以知道,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確實比日本經濟要快,但同時伴隨的是貧富差距比日本要大。從本質上看,中國貧富差距擴大也折射了中國經濟畸形的社會形態和體制的不公,收入分配不均現象無處不在,收入分配不均的擴大會直接導致中國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增加。所以,認真研究和分析經濟發展與貧富擴大的矛盾所在,充分了解中國經濟與日本經濟的差距是非常必要的。
2 日本經濟導致的貧富差距擴大原因分析
2.1 經濟體制變化是貧富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
日本的經濟體制原本是以政府為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為主的,強調的是政府本身的指導、產業政策和職員終身雇傭的行政措施。80年代后,日本經濟政策基本轉向了新自由主義的新立場,新行政改革以取得國民預算平衡來解決國家財政危機為目的,實行政府內部裁減公務員,將國有企業私有化,并對很多產業領域采取解除政府管制的行政措施。21世紀初,小泉政府上臺后更加推崇資本自由主義經濟的政策主張,在這場制度改革下,原有的日本企業終身雇傭、企業工會和年功序列等制度風光不再,取而代之的是臨時雇員、民營化和能力主義等新概念。資本主義新自由經濟改革是一場不平等的改革,日本經濟社會機制越來越有利于有錢人,大企業與中小企業的工資差距也越來越大,工薪者收入差距也在增大,很多人感到自己的生活比以前更加困難。且改革并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民眾收入縮水,生活安定感缺失,結果導致社會各階層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使貧富問題也越來越嚴重。經濟評論家荻原博子在接受《日本新華僑報》采訪時指出:“如今能夠享受到所謂景氣上升恩惠的,只有大企業和高收入者,一般的工薪階層不僅工資沒有漲,而且稅金和社會保險金負擔還加重了。被各公司優化組合所淘汰的那些50歲出頭的人,為了生計不得不尋找條件惡劣的‘非正式員工’的工作。這種經濟體制只能帶來富者越來越富,窮者越來越窮的惡果。”因此,經濟不景氣和貧富差距擴大,日本各政黨就這個問題也展開了各種激烈的爭論和角斗,所以近年來,日本的政權頻繁更迭,社會治安條件也愈加惡劣。
2.2 經濟制度不平等,資源分配不均勻
很多人稱資本主義有三大頑疾,即經濟危機、就業危機和貧富差距,這三大頑疾正讓資本主義走上末路狂歡,這些頑疾是資本主義自由經濟體制下根本無法解決的,而解決頑疾的最佳途徑是走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法國著名經濟學家托馬·皮克提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一書中也稱“資本主義必然導致貧富差距擴大,人類社會未來會進入寡頭時代,資本主義是一種攜帶自我毀滅基因的制度”,皮克提通過對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貧富差距數據分析發現,幾乎所有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貧富差距都在近年來不斷擴大。通過分析以上的觀點,社會貧富差距的擴大跟國家政治制度是分不開的,其帶有保護色彩的自由市場經濟更加有利于上層社會和大企業的資本持有者,“不平等”、“不均勻”造成資本持有者和勞動者獲取收入間的不平等,如果資本回報率高于經濟增長率,即使經濟增長的繁榮時期,也不可能使社會成員全部受益,且財富與收入的分布都不均勻,只能使富者更富、貧者更貧,結果是造成貧富差距日益加劇。
2.3 與發展中國家市場經濟競爭的原因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際經濟市場競爭也異常激烈,發達國家與新興的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也在不斷地變化和擴大,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廉價的勞動力和市場的迫切需求,導致發達國家勞動力使用下降,生產力也會隨之下降。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中引發的全球經濟大蕭條,使過度依賴美國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日本也受到了重創,強調弱肉強食的自由市場競爭,忽視了弱勢群體和民生,造成日本貧富差距拉大,“勞動貧困族”增多,日本終身雇傭制受到削弱,就業形態更不穩定。與此同時,同樣受金融危機影響的中國與日本經濟相比損失會較少,因為中國較好的投資環境和政策,加上相對較廉價的勞動力和龐大的市場內需,吸引了眾多的外資企業,使中國經濟在金融海嘯中較平穩地渡過難關。這種國與國之間的政治的、文化的、甚至地緣性的經濟條件是日本資本主義經濟在國際競爭中無法比擬的,產業結構的變化最終使日本國內相關的產業逐漸走向衰亡,造成人員失業,收入水平不斷降低,貧富分化更加明顯。
3 中國從日本經濟發展中得到的啟示
中國經濟的發展具有其時代的獨特性,與日本經濟的發展有著很大的區別,但仍然可以借鑒日本的經濟發展經驗來指導我國以后的經濟發展,通過上述對日本經濟導致貧富分化問題進行分析,中國面對同樣問題時會有什么樣的啟發,對以后經濟的發展會有什么幫助,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首先,要學習日本經濟逆境中求發展的經驗。日本經濟危機后,日本在財政收入銳減的情況下,能夠不謀求短期的經濟效益,從新幫助日本產業結構進行調整,鼓勵發展短期有效的文化產業,淘汰高耗能產業;鼓勵大企業把低端產業向海外轉移,實行在哪里生產在哪里銷售的戰略。最難能可貴的是,在日本經濟最低迷的時期,日本政府積極應對而非回避經濟危機。這種逆境中求發展的經驗是值得我國學習和借鑒的。但是時代背景在變化,我國在面對經濟問題及貧富差距的問題時,要結合我國自身的經濟發展規律和條件,解決經濟與社會的矛盾和沖突。
其次,要進一步完善經濟制度,實行正確的政策。從日本實施的經驗來看,經濟制度的政策會對分配收入產生極大的影響,市場競爭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是經濟增長的產物,如果需要調節這一分配的不均,只有政府通過對分配起點和分配過程進行調節,施行正確的調控政策,即通過對高收入者征稅,對低收入者進行有效資源轉移。但從我國現在的實情來看,我國再分配的手段和功能嚴重不足,高收入人群收入越來越高,低收入人群缺乏政策保障,所以,完善經濟制度,實施正確的經濟政策對我國來說還有很長的路要摸索。
最后,需要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日本經濟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到現在,已經形成社會多層次、多種類、多領域的市場經濟體系。中國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也需要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它是對社會分配進行再調節的重要經濟杠桿,既要保證經濟的發展,又不能造成社會貧富分化問題及其他不可控的經濟問題出現。實現多層次、多渠道、保障范圍不斷擴大的社會保障體系,既是我國經濟發展從量變到質變的轉變過程,也是提高人們生活水平和實現社會資源公平利用的保障。
4 結語
綜上所述,日本經濟的發展的確有著很多經驗是值得我國學習和借鑒的,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中,既要汲取日本經濟發展的經驗,也要規避日本經濟掉入的陷阱。中國雖然通過經濟政策手段使得貧富差距問題還不很明顯,市場經濟“泡沫”危機還未顯現,但也要清楚知道,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使跟隨美國的日本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對經濟失敗的事實,所以中國經濟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需要更多的人和企業走到時代的前列,通過與國際的合作與交流,創造出更加符合我國國情的新經濟發展的道路和價值理念,進一步縮短民眾的收入差距,降低貧富分化現象任重而道遠。
[1]王海濤,譚曉軍.日本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及趨勢分析[J].國際資料信息,2008(04).
[2]藍慶新.新自由主義的失敗與美國金融危機的警示[J].國際資料信息,2008(04).
[3]周賽.淺論經濟全球化與貧富差距之間的關系[J].經濟導刊,2009(11).
[4]李超.日本發展循環經濟的背景、成效與經驗分析[J].現代日本經濟,2008(04).
[5]托馬斯·匹克迪.二十一世紀資本論[M].哈佛大學出版社,2013.
[6]崔健.論現代日本的階級(階層)與經濟差距的關系[J].現代日本經濟,20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