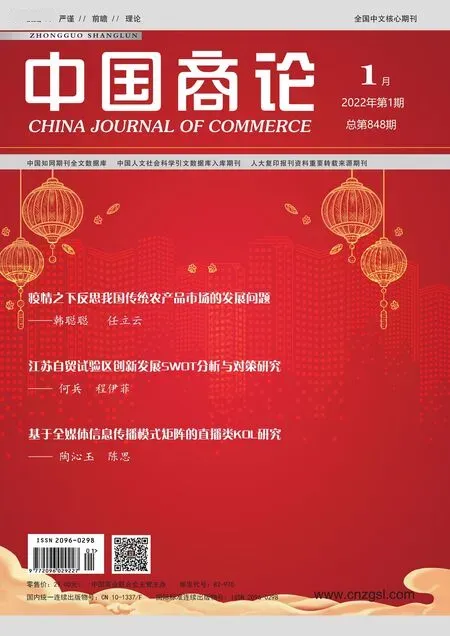浙西古民居三雕藝術的符號學解讀及商業價值①
浙江商業職業技術學院 李小紅
浙西三雕以衢州為代表,衢州主要以明清時期的古民居建筑居多,這些古建筑在規劃布局與傳統工藝方面融合閩、贛、皖、浙建筑風格于一體,形成了具有濃郁地方特色的建筑風格。在浙西的古建筑中,石雕、磚雕、木雕是浙西古建筑裝飾藝術水平的完美體現,也是傳統裝飾藝術風格一種民族符號的表現。符號是人類認識事物和傳達信息的媒介和載體,本文通過對符號學的解讀,使人們重新認識到浙西三雕裝飾藝術在現代設計中的表現及其較高商業價值,這是對古今文化的傳承與再創。
1 三雕符號學
1.1 符號學
符號是由形式和意義所組成的。符號學的目標自從索緒爾研究開始就已確立,經過了一個從符號系統到意指系統又到意指方式的發展,換句話說,從事物的外在結構形式轉化為內在意義的產生。早在古埃及時期,符號就已出現,當時符號作為信息的傳遞工具,同時又是表達思想的一種方式,依靠符號的作用進行相互的傳遞和交流,因此人類的意識領域正是由符號的發展開始。法國當代杰出的思想家和符號學家羅蘭巴特指出一個符號的感念:“能指與所指,能指是一種相關物,它是以中介體為物質的,所指是事物的心理再現,能指和所指結合為一體的行為為意指,其產物便是符號”[1]。事實上,人類所有的生產勞動、心理變化的進行,都有賴于符號的存在,人的認知過程根本就是一個符號化過程。
1.2 浙西古民居三雕——符號學載體
浙西三雕裝飾藝術中所運用的各種雕刻圖形都是一種視覺的載體,這些圖形是體現出當時人們向往美好生活的一種情感寄托方式。作為裝飾藝術,其雕刻手法的表現多樣和靈活,不但記載著本地的歷史文化遺跡,同時也是展現出視覺傳達符號的一種表現形態。在民居建筑中不論是大型祠堂和寺廟,還是庭院樓臺、家居擺飾等,其中的雕刻圖形都是一種信息的載體,并成為了當時歷史文化的符號形態。在浙西三雕裝飾藝術的構思方面,“以人物為主的題材有名著故事、神話傳說、名人軼事、戲曲唱本、忠孝節義、生產生活、民間傳說等;以山水為主的題材有衢州名勝和各縣具有代表性的名勝風光;以宗教為主的題材有蓮花、羅漢、福祿壽三星等;還有表現植物圖形的有菊花配蓮花、佛手配桃子、葡萄配葫蘆、荷蓮靈芝等;也有喜上眉、獅子滾球、 雙獅對舞、花草蟲魚等花鳥動物題材的;也有福祿壽喜等用文字形式來表示的圖形”[2]。這些表現形態已成為當今傳統民間文化符號載體,具有較強的象征意義。
2 浙西古民居三雕裝飾符號的語義表達
符號的本質在于意義,意義是符號的真諦,正如沙夫所說:“沒有意義就沒有符號。”“根據羅蘭·巴特的符號觀,符號的意義主要分為兩部分:外延意義(功能) 、內涵意義(價值)。任何事物都要表現外延和內涵才能形成一個完整符號。”[3]
2.1 浙西三雕符號的外延意義
外延意義是指符號具有特定的、顯在的常識性意義。浙西古民居建筑中,常見的門罩、牌坊、掛落、石鼓、牌坊、角獸、脊飾、漏窗、梁仿、斗拱、欄桿、門窗等其他諸如家具雜件、生活用品以及裝飾擺放等物品都是以平面雕 、淺浮雕 、深浮雕和透雕出現,許多構件和局部本身就是三雕的藝術精品。
2.2 浙西三雕符號的內涵意義
符號的內涵意義是指事物本身所具備的內在特點和屬性,具有較強的象征性,其意義要比外延意義更復雜、更抽象、更含蓄。浙西三雕裝飾藝術所表達的傳統審美和文化精神具有其內在的特點,其象征性為當今社會的物質與精神文明建設,起到了積極的現實意義。根據其象征性的不同分為以下三個含義。
(1)感性含義是指在作品表達中直接反映的感性特點,如浙西三雕最具代表性的牌坊,它最直面的特點就是反應明清時期建筑的雄偉、壯觀、氣魄,反映了歷史文化價值,同時體現出了人們對物象的最直接感性認知。
(2)表意含義是一種認知結果,是在創作設計中蘊含的一種特殊意義和特性,它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并通過受教方式形成的一種價值理念。如在浙西三雕藝術作品里,常表現的知足常樂、安貧樂道的處世哲學及其四季平安、五谷豐登等樸素的思想觀念。
(3)敘事含義是一種更深層次的意義,以當時的思想文化、社會背景、地域環境、人文風俗等為基礎,反映了當時人們生活、勞動、文化、精神層面等社會發展的現象。浙西三雕符號藝術敘事含義表現為三方面:
第一, 以儒家文化精神核心體現的美學思想,如“忠君報國”、“忍讓”、“中庸”、“福祿”、“禮義廉恥”等的內容題材。
第二,在浙西三雕裝飾藝術中體現人生價值觀的圖形紋樣,通常表現為“福祿壽喜”、“如意”、“忠孝”、“禮儀”等,體現了當時人們對生活的一種堅定樂觀、積極向上的美好理想。
第三,浙西三雕裝飾藝術還反映了一種社會現象,反映了當時的多重文化價值。如儒家文化表現的二十四孝;表現忠義的是“岳母刺字”;表現“節”、“義”的“送郎趕考”;佛教文化的“萬”字紋符號、盤長紋樣、蓮花紋樣等[4]。
2.3 浙西古民居三雕裝飾符號表現手法
符號是人類特有的社會文化現象,是一種公共約定的指稱方式。“根據皮爾士、M.本澤和H.賀爾梅等人所提出的發展符號學理論,可將符號的表現手法分成為五個方面:添加、融合、疊代、象征與寓意、解構與重構”[2]。
(1)添加,是一種線性序列,是開放的、可延續的,浙西三雕中常用到“添加”的手法。如三雕中的回文、錢文常作為添加內容,以設計結構的形式圍繞著主要的圖案內容,回文、錢文的添加運用,使得作品結構更加飽滿、充滿活力。
(2)融合,是將各種符號綜合在一起,設計成一個完整形態的一種結構形式。這種形式在浙西三雕裝飾藝術中常見,比如“抬頭見喜”,設計者把麒麟和喜鵲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個新的形式。
(3)疊代,是將符號與其他符號構成在一起形成上下文,同時產生出其他符號的一種表現形式。比如浙西古民居建筑中的“八仙的故事”,其用八仙的手中的寶物來替代人物的形象,表現“八仙”待人處事等內容故事的這類題材符號信息。
(4)象征與寓意。象征是一種符號,是認識的手段和方式。象征的手法使抽象的建筑形式清晰和準確地傳達其豐富的意蘊,可使創作從表面的形式轉向深層的內涵表達。因此,建筑師通常用象征的手法來表達自己對建筑的理解與設想。比如“締結良緣”是美滿婚姻生活的象征;浙西民間常用“年年有余”、“五谷豐登”的窗格和年畫,來象征吉祥與喜慶。寓意是一種重要的設計思想和表現手法,可以用一種或幾種造型的結合來表達和暗示人們所要追求的美好愿望,比如,喜鵲和梅花的組合而成“喜上眉梢”寓意喜事連連、萬事順心的含義。
(5)解構與重構分解,是對以往理念的變更,根據設計者的思路,對事物進行分解組合的表現方法,然后依照一定的審美法則,再進行有次序的重新排列組合,是新形式的、突出性的設計思路。在浙西三雕藝術中很常見,是繼承傳統文化形式上的一種創新理念的表現手法。如“回紋”、“細紋”的分解重組的應用,富于新的節奏和新的裝飾形態,同時,解構與重構分解手法也是當代設計師繼承傳統文化,進行現代設計的一種重要的表現方法。
3 浙西古民居三雕裝飾藝術符號的商業價值
浙西古民居文化是我國建筑藝術領域的一個極具地方特色的區域文化,它保留了本地域文化的同時,又吸取了周邊地方文化的精髓,使得多元文化在浙西這一特定地區得到不斷的發展。當今,浙西古民居建筑藝術要想體現出其藝術與商業價值,就必須繼承和創新,不斷培養傳統文化的繼承人,接受新的設計理念,不斷挖掘新的內容題材,才能在社會環境中具有競爭性。“當一種文化資源能夠滿足人們生產、生活需要時,它就自然轉變成為了一種文化資本,人們從經濟利益的角度來審視文化和藝術時,文化資本就轉化為了一種商業價值而存在。”[5]浙西古民居作為明清時期的一種建筑風格形式,它的影響力已不僅局限于本地區了,其商業價值是不可估量的。從這一層意義上來說,浙西古民居裝飾藝術的商業價值的實現,實際就是浙西古民居藝術符號發展的內在需求。如果說浙西三雕裝飾藝術是一個符號,那在現代多元化的市場經濟背景下,這個符號的推廣就必須具備品牌特點。這一品牌既要保持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又要力求在傳承中尋找突破,要堅定不移地進行浙西古民居裝飾藝術文化價值開發,創造出具有浙西地域文化品牌的優勢,以新品牌形象將三雕裝飾藝術融入社會,使浙西這一地域文化資源特色更好發揮出其商業價值的優勢。
隨著房地產業的發展,設計師們為了汲取傳統古民居建筑藝術的精華,絞盡腦汁,在設計規劃中十分注重新環境、新材料、新技術、新題材、新風格的開發運用,并通過對古建筑符號元素的提取,設計出了不少具有浙西古民居三雕裝飾藝術符號的優秀作品。魯迅先生在談文學藝術的地方色彩的同時,也講到了越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越容易走向世界的理念。因此,對于現代設計的任務和要求,不僅要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設計理念,更要立足本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創造出具有浙西三雕裝飾藝術品牌的新商業價值作品。比如浙西古建筑中的粉墻瓦黛、馬頭墻、庭院、溪流等元素,在很多建筑中將這些元素予以解構重組,形成了新的裝飾藝術品牌形式。這些全新的品牌產生,不僅使設計賦予了建筑環境的人格化和情感化,更加激發了人們對于傳統文化眷戀之情。這些年,隨著我國城市的發展,傳統民居的裝飾形式、風格和人們的生活方式都發生了變化,其原因正是由于現代設計理念與傳統設計理念沒有更好的結合,使得我國許多的設計缺乏了文化價值和商業價值。這種現象的出現促使人們對傳統文化又重新認知,特別經過對浙西三雕裝飾藝術符號的研究。樹立重視古民居建筑中的“立于形,重于意”精髓的思想,好好把握傳統文化與現代設計理念的關系,使得裝飾藝術符號神形兼備,并具備商業價值的開發和利用。這有助于當代設計師們弘揚傳統文化的精神和提升大眾的文化內涵的同時,更好地體現浙西古民居三雕裝飾藝術符號的商業價值。
4 結語
本文通過對符號學的解讀,使人們從傳統裝飾圖形符號中得到更多的借鑒和啟發。在符號學的基本原理上,以辯證發展和持續的眼光重新認識浙西三雕藝術符號的語義和商業價值,深入探究三雕符號的設計表現手法,努力挖掘傳統文化的深層內涵,更好地推動浙西三雕裝飾藝術的傳承與發展。
[1] 李爽.視覺符號的抽象程度與意義表達[J].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
[2] 劉云.從符號學角度探析徽州三雕藝術[J].安徽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
[3] 胡飛.藝術設計符號基礎[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
[4] 張道一,郭廉夫.古代建筑雕刻紋飾[M].江蘇美術出版社,2007.
[5] 蔡璨.徽州古民居藝術符號價值再現研究[D].安徽工業大學碩士論文,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