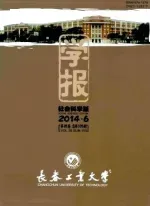論《呼蘭河傳》中的東北形象建構——兼談童年生活對蕭紅創作的影響
王金茹 王雪峰
(吉林師范大學a.傳媒學院;b.國際文化交流學院,吉林 四平136000)
楊義在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曾說:“蕭紅是三十年代的文學洛神。她是‘詩之小說’的作家,以‘翩若驚鴻,婉若游龍’的筆致,牽引小說藝術輕疾柔美地翱翔于散文和詩的天地”,[1](P558)贊譽之情躍然紙上。在蕭紅的作品中,與此評語最相配的莫過于《呼蘭河傳》了。
《呼蘭河傳》這部小說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她是女作家蕭紅的代表作,也是她傾注心血最多、成就最高但又招來非議最多的一部作品。關于這部作品的評價與解讀從它發表之后就開始了,后來經過了一段時間沉寂之后,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又重新掀起了評論熱潮。1940年12月20日,《呼蘭河傳》完稿,1941年10月25日,上海雜志公司剛出版《呼蘭河傳》僅5個月,谷虹就在《現代文藝》第4卷第1期發表第一篇評論文章:《呼蘭河傳》,開始了至今仍在繼續的有關這部作品的討論。
關于《呼蘭河傳》的解讀,不同時期的評論伴隨著當時的社會文化環境、文學思潮及受眾的審美喜好的不同,而產生了不同的聲音,著染了各種文化積淀,在現實的今天,呈現出異彩紛呈之勢。在撿讀諸多的作者傳、作品評論、讀者印象時,可以看到這部作品強大的生命力背后,是作者創作意圖與創作愿望的愈加模糊,而評論主體的主觀意識形態與臆測卻在不斷地增強,換句話說,就是文化成規與文化參與的力量在不斷地重寫著這部作品。先是諸如“寂寞論”、“個人主義”“與大時代的脫節”[2](P3)“走了下坡路”[3](P369)等意識形態式的評斷,后來隨著社會文化環境的轉變,人文主義思潮的興起,文化批評的加入,人們開始重新審視《呼蘭河傳》,發現了其中有“向著人類愚昧”作戰的努力,解剖國民性的嘗試,關注底層弱勢群體的草根情懷,更有人從“胡家婆婆”身上發現了其所承載的文化意義。[4](P177-179)還有評論者認為,《呼蘭河傳》是一部“民族憂痛和鄉土人生的抒情交響詩”,[5]更有評者把《呼蘭河傳》看成一部奇書,奇在它包羅萬象,奇在它讓讀者看到了“童年的美善,社會的辛酸,敘事詩的明朗,散文詩的輕快,民間歌謠的凄婉親切,鄉土文學的多姿多彩”。[6](P265)更有劃時代意義的是,在蕭紅百年誕辰暨作品研討會上,學者們對蕭紅作品及其創作動因展開了更廣泛的探討,提出了一系列頗有新意的見解,[7](P321)在眾多的蕭紅作品評論中,我們可以看到蕭紅卓越的文學才華與創作天賦,而筆者卻在《呼蘭河傳》中看到了蕭紅一個心事:她想讓讀者見見她的家鄉及家鄉的父老鄉親——他們生活在東北一個小鎮,一個不起眼很普通但卻生生世世地存在著的一個地方。在《呼蘭河傳》中,呈現最真切的不是主題,而是空間:呼蘭河鎮。換種思維方式,也可看作是對東北形象的一次塑造與呈現。
一、“后花園”意象的疊加
在《呼蘭河傳》中,有一個美麗的意象,那就是“我”與祖父常呆的地方:后花園。后花園是一個充滿色彩與樂趣的場所,是一個讓人樂而忘返、無憂無慮空間,在這里,“蜻蜓是金色的,螞蚱是綠色”,有“白蝴蝶”、“紅蝴蝶”、“滿身帶著金粉”的大紅蝴蝶,有嗡嗡地飛著的蜂子,有在風中呼呼響的大榆樹,還有各種各樣有花有果的植物:小黃瓜,大倭瓜。它們的藤蔓愿意爬到哪里就爬到哪里,愿意長多高就長多高,愿意結一個果子就結一個果子,愿意開一個謊花就開一個謊花,一切都是那么自由自在,順其自然,這種自然界中的自由狀態無形中也呼應了園中人物的心理狀態。園中的一老一小同樣也是如此的合諧與安詳。文中寫道:“祖父戴一個大草帽,我戴一個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祖父鏟地,我也鏟地”,當“我”把狗尾巴草當成谷子的時候,逗得祖父哈哈大笑,“我”則不以為然,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多么幸福安寧的一幅祖孫生活圖啊!這畫面沒有時間投射,沒有空間隸屬標識,仿佛就是祖孫兩人的童話世界。在這里,自然的后花園與人生理想中的“后花園”兼而重合,作家正是用她那支有溫度的畫筆為讀者勾勒描摩出一幅東北小鎮人家日常生活一景。
當我們把這幅圖景無限放大之后,它便成為東北這片土地上一個可以復制無數的點影,也就是說,在東北有無數這樣的小鎮與小花園,由此推及,小鎮上的這個小花園也就有了東北地域形象之映像這樣一層涵蘊。周錦曾在她的評論文章中說:“我喜歡《呼蘭河傳》,一方面是因為書中所敘說的那些事情和人物,有著似曾相識的感覺;再就是飽經戰禍之后,多么希望能有那種‘帝力與我何有哉’的先民生活。”[6]這種感覺便印證了《呼蘭河傳》所描述的東北民間生活其實是一種閑適舒緩的人生狀態,“后花園”里有著一幅自我建構的風景,是作家依憑記憶再造的想象的精神空間。
“人和天地在一起,天地是多么大,多么遠,用手摸不到天空。而土地上所長的又是那么繁華,一眼看上去,是看不完的,只覺得眼前鮮綠一片。”“一到后園里,我就沒有對象地奔了出去,好像我是看準了什么而奔去了似的,好像有什么在那兒等著我似的。其實我是什么目的也沒有。只覺得這園子里無論什么東西都是活的,好像我的腿也非跳不可了。”[8](P455)所以有人說,在《呼蘭河傳》中看不到壓迫,看不到剝削,更看不到三四十年代那種火熱的全民族抗戰的狀態。[2]其實說的也是實情,只不過現在看來,單純從民族國家這種宏大敘事角度去觀照蕭紅的這部作品,顯然有些視野狹小了些。而我們的東北先民生活確實就是這樣一種安靜無爭、自給自足式的生活。這種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閉塞的傳統生活,同樣也符合人們對東北地域形象的歷史想象。東北自古以來,就地廣人稀,物產豐富,民風淳樸,在中原人民的印象中,那就是一個天然的大花園,大狩獵圍場。很久以來,讀者只看到了小說中這個“后花園”,而沒有看到小說背后那個大大的“后花園”意象;只聽到了“后花園”中的小主人一聲聲的人生寂寞的嘆息,卻沒有聽懂她內心中更深沉的向往與熱愛!她要用她的筆,為世人建構一個她心中的東北形象。所以“后花園”這個意象還有待于研究者更深入地挖掘與探討。
二、“大泥坑”的隱喻
“大泥坑”在小說開篇就出現了,并且花費了作者很多的筆墨,難道蕭紅是因為獵奇講故事吸引讀者才這樣寫的嗎?顯然不是。那么“大泥坑”自有它的獨特意涵。文中寫到:“東二道街上有大泥坑一個,五六尺深。不下雨那泥漿好像粥一樣,下了雨,這泥坑就便成河了,附近的人家,就要吃它的苦頭……”“這大泥坑出亂子的時候,多半是在旱年,若兩三個月不下雨這泥坑子才到了真正危險的時候,表面上看來,似乎是越下雨越壞,一下雨好像小河似的了,該多么危險,有一丈來深,人掉下去也要沒頂的。其實不然,呼蘭河這城里的人沒有那么傻,他們都曉得這個坑是很厲害的,沒有一個人敢有這樣大的膽子牽著馬從這泥坑上過。可是若三個月不下雨,這泥坑子就一天一天的干下去,到后來也不過是二三尺深,有些勇敢者就試探著冒險的趕著車從上邊過去了,還有些次勇敢者,看著別人過去,也就跟著過去了。一來二去,這坑子的兩岸,就壓成車輪經過的車轍了。那再過來者,一看,前邊已經有人走在先了,這怯懦者比之勇敢的人更勇敢,趕著車走上去了。誰知這泥坑子的底是高低不平的,人家過去了,可是他卻翻了車了。”這段描寫幾乎沒有人關注分析過,大多數人關注的是大泥坑的作用:能給人們提供看抬車抬馬、說長道短的消遣;還有就是可以為人們吃瘟豬肉變相地提供遮掩的條件,沒有淹死的豬,哪來更多的以瘟代淹的豬肉可吃呢?分析者多從這個邏輯去解讀呼蘭河小鎮上的人們那種愛占小便宜卻又想給自己找一個合適的理由的民族心理,這也是蕭紅在作品中明確提出的。但是,透過這字面上的意思,我們似乎又可以讀到另一層深意:呼蘭河人的保守和惰性。而這種保守和惰性直接就導致了落后愚昧,而落后愚昧不僅可以導致動物的死,還可能導致人的悲劇。下文中小團圓媳婦是一例,王大姑娘也是一例。
習慣于既有的事實、安于現狀這種民族心理可以讓人們覺得這大泥坑簡直是鎮上的一個“福利”,給人們提供樂趣談資,還可以吃淹死的各種動物肉,所以“一年之中抬車抬馬,在這泥坑子上不知抬了多少次,可沒有一個人說把泥坑子用土填起來不就好了嗎?沒有一個”。因為泥坑子漲水而淹沒了道路,過往的行人認為應該讓坑兩邊的人家把院墻往里挪一挪,院子的主人說應該在路邊種上樹,這樣下雨人們可以攀樹過路,說拆墻的有,說種樹的有,就是沒人說用土把坑填平的。“在這大泥坑上翻車的事情不知有多少,一年除了被冬天凍住的季節之外,其他時間,這大泥坑像它被賦與了生命似的,它是活的,水漲了,水落了,過些日子大了,過些日子又小了。大家對它都起著無限的關切”。人們之所以如此看待大泥坑,不光是因為有肉吃有樂景看,更多的,是一種習慣和思維定勢,他們覺得大泥坑多少年前就存在著,仿佛自古如此,就如生活中那些傳統積習,一代一代地傳承下來,沒有人反思它有什么不合理,即使它給人們的生活帶來很多不便或是麻煩甚至傷害。看小團圓媳婦被折磨而死就是一個生動的例證。胡家婆婆對自己家的團圓媳婦的一番調教,最后這個健康活潑的小姑娘竟被活活地折磨死了,為什么呢?因為婆婆認為她行止做派不像個團圓媳婦,所以要“惡使三年,善使一輩子”,這是老祖宗留下的調教剛進門媳婦的經驗,胡家婆婆也不想弄死自己的兒媳婦,但傳統思想的惡習讓她自覺自愿地實踐著祖宗留下的規矩,仿佛那個“大泥坑”,明明是一種障礙和危險,但是人們習慣了它的存在,還會千方百計地找理由認為它存在是合理的。“大泥坑”的混沌與包容,變幻與詭異,鎮上人對現實的麻木與安守,這就是當時東北人民生活狀態的真實寫照。日偽統治了東北14年,有多少人安于命運的擺布,不思反抗,直到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了,才開始奮起抗爭,這也構成東北形象中一個側面。是東北這方水土養育的這方人造就了東北形象,東北形象中離不開東北人,更離不開東北的風土人情。
三、為什么會有如此迥異的東北形象?
蕭紅,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注定是一個異數,因為她的人生與她的作品都頗具傳奇色彩。2011年是她誕辰百年,100年后,她的人生經歷數度被搬上大銀幕或者劇院的舞臺。時下香港資深導演許鞍華執導的電影《黃金時代》熱播,讓當代的受眾對這位民國時期的女作家充滿了好奇與不解,走出電影院的人們各懷觀感,莫衷一是,如同影片中她的友人們對她的不同詮釋和理解一樣,蕭紅的人生及其對人生的把握與選擇充滿了不可理解的“矛盾”。其實,這本身就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更多的時候,是每個人都把自己的人生經驗投射到蕭紅的身上,去為蕭紅分析和評價她的人生,如此濃烈的解讀情結,在其他作家身上真的是不多見,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蕭紅的獨特魅力。
魯迅在《八月的鄉村》序言中寫道:“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難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蟈蟈,蚊子,攪成一團,鮮紅的在讀者眼前展開,顯示著中國的一份和全部,現在和未來,死路與活路”,這句話如果用來描繪蕭紅的人生,也未嘗不可。蕭紅的人生,是受難的一生,是充滿了抗爭與淚水的一生,但同時,她的人生又因了這抗爭與不屈而充滿了傳奇與迷幻的色彩。她的人生歷程充滿了死角,并且是她自己一次次地把自己逼到絕路,而命運又一次次地讓她絕地重生。正是這種不斷的大開大闔的人生際遇,激發了她天才的潛能,讓她的文學才華如電光火石般橫空閃耀,成為20世紀30年代中國文壇的“洛神”。相較于她的作品,人們似乎更熱衷于她的人生故事。針對這一社會現象,學者林賢治曾不無悲哀地表達:他最怕的就是“只見八卦,不見蕭紅”,“作為一個作家,如果僅僅被人們關注她的‘情史’而忽略了作品,無論如何是一個悲劇,這不能說是好現象。”林賢治是一位嚴肅的蕭紅研究者,著有《漂泊者蕭紅》,還曾編過蕭紅的作品集,他一直在做“重新認識蕭紅”的工作,像林賢治這樣關注蕭紅的學者不在少數,這也是蕭紅為什么在學界備受矚目且經久不衰的原因之一。其實在筆者眼里,蕭紅首先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女人,然后才是一位天賦異稟的女作家。在她的人生中,充滿了偶然與必然。
蕭紅的童年是在東北那個名叫呼蘭的小鎮中度過的。這座小城因為有一條河經過而得名,而這個默默無聞的小城后來卻因為一個小女孩的回憶而聞名世界,這就是蕭紅和她的《呼蘭河傳》。
童年的蕭紅是幸福快樂的,因為有祖父的寵愛與嬌慣,她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在《后花園》和《呼蘭河傳》等作品中,她在回憶祖父給她帶來的溫暖和愛時,有過真實的描寫,她想吃雞了,祖父馬上就叫老廚子把那還在下蛋的老母雞宰殺煮了,她想在后花園玩多久就玩多久,想摘哪朵花就摘哪朵花。她還因為頑皮闖過很多禍,比如下雨天把蓋醬缸的蓋子當草帽玩來玩去,導致一缸的大醬都被雨淋了,生活在東北的人都知道,大醬被雨淋就會生蛆了,所以父親一腳把她踢倒在地,她也因此對父親記了仇。她把家里的雞蛋偷出去和小伙伴們烤著吃,把饅頭偷出去送人,結果挨了母親的打,總把家里的窗戶紙當玩具捅著玩,最后祖母在窗外用針尖扎了她的小手,讓她長了記性,再也不敢禍害人了。最頑皮的事是蹲在梯子上拉屎,還嚷嚷著是在下蛋。蕭紅在講述這些情節時,少部分是懷念祖父的愛,更多的是在記恨父母與祖母對她的冷漠與無情。在蕭紅的心里,童年是寂寞而又不幸的,只有老祖父才給她全部的愛與溫暖。但在筆者看來,正是因為老祖父的溺愛,才讓小蕭紅養成了任性而頑皮的性格,一點兒不像小女孩那樣文靜乖巧,可以想見,在她家那樣的以詩禮傳家的地主家庭,父母和祖母肯定會看不慣她的習性,定然會要管教她,而祖父又總是護著她,所以她的童年家庭教育就是在這種又嚴又松的矛盾氣氛中度過的,父母管得越嚴格,她的倔強脾氣就越厲害,久而久之,她的逆反心理和復雜性格就形成了。
一個人的童年生活對其心理性格的形成具有極大的作用,有些影響甚至會持續一生。從蕭紅后來的人生與創作來看,童年時代父母對她過于嚴肅與嚴格的教育給她的心靈造成了不可撫平的傷害,而祖父的寵愛與寬容又讓她體會到了人間的溫暖與親情,這兩種極為反差的情感教育讓她養成了敏感細膩、喜歡求真,而且對事物的觀察有著迥異于常人的直覺和穿透力。一方面源于老祖父的寵愛,讓她對生活事物保有著熱愛之心,而且更可貴的是她的心地極為單純善良,沒有一點機巧之心,這讓她能更直接地切進生活的本真內容之中,創作的直覺和感悟相當的靈敏;另一方面,因為緣于對父母的怨懟,使她對生活中的一些現象也產生了厭惡與反思,這種批判性思維,讓她看到了常人發現不了的一些習焉不察的傳統陋習。有時她自己可能都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深刻,但直覺已經流向了筆端,在她的作品中,往往會有神來之筆,也正是緣于這個動因。
1940年正當抗戰文藝作為主潮時,蕭紅卻拿起筆寫她的《呼蘭河傳》,這部作品沒有抗戰的內容,所以一度引來非議,但今天看來,蕭紅有她更深一層的思考,她要用她的筆記下她的故鄉,那片被占領的土地及土地上的人們,揭示他們的生活狀態,剖析他們的思想意識,批判他們的惰性與保守,把一個真實狀態的東北留存給文學史和后人。
[1]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2]茅盾.《呼蘭河傳》序[A].蕭紅.蕭紅全集(下)[C].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1991.
[3]石懷池.論蕭紅[A].石懷池.石懷池文學論文集[C].上海:上海耕耘出版社,1945.
[4]趙德鴻,張冬梅.蕭紅《呼蘭河傳》的文化闡釋[J].學術交流,2007,(5).
[5]張國禎.民族憂痛和鄉土人生的抒情交響詩[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1982,(4).
[6]周錦.論《呼蘭河傳》[M].臺北: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
[7]任雪梅.百年視閾論蕭紅[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1.
[8]蕭紅.呼蘭河傳[A].蕭紅.蕭紅全集(下)[C].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