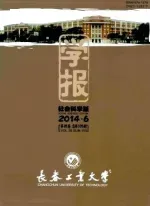女性意識(shí)下的孤獨(dú)與成長——論青山七惠的《一個(gè)人的好天氣》
王先科
(福建師范大學(xué)福清分校 外國語學(xué)院,福建 福清350300)
日本青年女作家青山七惠的小說《一個(gè)人的好天氣》,講述了這樣一個(gè)故事:年輕女孩知壽想開始獨(dú)立生活,只身來到東京,在母親的安排下住進(jìn)了七十一歲的遠(yuǎn)房親戚吟子家;在經(jīng)歷了情感和生活的一段段平淡而真實(shí)的小插曲之后,知壽決定告別一些故人舊事,面對(duì)新的生活,尋找屬于自己的好天氣。這是一部并沒有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jié)的安靜平淡的小說,卻在2007年的芥川龍之介獎(jiǎng)評(píng)審會(huì)上得到多數(shù)評(píng)委的盛贊,并最終成為這一日本文學(xué)最高獎(jiǎng)項(xiàng)歷史上第三位年輕的女性得主。
一、小說的孤獨(dú)主題
《一個(gè)人的好天氣》描寫了年輕女性似有還無的孤獨(dú)。自上世紀(jì)80年代以來,此類描寫年輕人孤獨(dú)寂寥情緒的女性小說在日本文壇屢見不鮮,如吉本芭娜娜的《廚房》、綿矢莉莎的《欠踹的背影》等。比較之下,吉本芭娜娜的小說是以愛作為主題,而孤獨(dú)只是一種情緒;而在《一個(gè)人的好天氣》里,孤獨(dú)不僅是彌漫在字里行間、流淌在人物內(nèi)心的情緒,更是小說關(guān)注和探討的社會(huì)性主題,而愛則變成了孤獨(dú)主題下一種生活元素。孤獨(dú)作為現(xiàn)代人自我意識(shí)深化的心理反映,是一種深刻而強(qiáng)烈的智慧自省。從社會(huì)學(xué)的角度來看,它是“在人與自我、人與人、人與社會(huì)、人與自然的錯(cuò)綜復(fù)雜的矛盾、糾葛與沖突中所產(chǎn)生的寂寥、苦悶、抑郁、憂慮等情愫,以及難以描述的微妙而又波動(dòng)的心理狀態(tài)”。[1]在先行研究中,有觀點(diǎn)認(rèn)為“知壽的孤獨(dú)可以說是自愿的”,[2]其自顧自地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過著簡單重復(fù)的“干物女”生活,沒有遠(yuǎn)大志向。實(shí)際上,這種觀點(diǎn)只注意到了人的孤獨(dú)感普遍的內(nèi)在成因,而對(duì)于知壽自我內(nèi)心的封閉而言,外界的疏離,或許才是造成其孤獨(dú)情緒的真正原因。
首先,知壽內(nèi)心的倦怠和虛無感,使她對(duì)一切都不太提得起興趣,不管是工作、愛情,還是生活。知壽先是在一個(gè)會(huì)議中心做招待員,后來又到一個(gè)車站的站臺(tái)小賣店當(dāng)售貨員,最后到一家公司去打工。和眾多的80后自由打零工者一樣,知壽沒有正式的工作。這樣的人群在日本被稱為“飛特族”。誠然,就業(yè)形勢(shì)嚴(yán)峻、用工數(shù)量減少是“飛特族”出現(xiàn)的直接原因,但究其根源,年青一代受成長環(huán)境等因素影響而缺乏責(zé)任感和獨(dú)立意識(shí),才是“飛特族”近年來人數(shù)激增的內(nèi)在動(dòng)因。對(duì)于知壽來說,打零工形式的工作,并不是一種對(duì)自我價(jià)值和人生意義的追求,而是她為了生存不得不進(jìn)行的“經(jīng)濟(jì)儲(chǔ)備”。除了工作,知壽對(duì)戀愛也完全沒有投入的熱情。在她的兩段荒唐而又短暫的愛情中,她始終缺乏應(yīng)有的積極和快樂。她的第一個(gè)男友叫陽平,兩人見面“一般泡在屋子里,從沒討論過任何問題,也沒吵過一次像樣的架……我們互相都感覺對(duì)方是可有可無的”,甚至最后在探望陽平而意外發(fā)現(xiàn)自己的位置已經(jīng)被取代時(shí),知壽也沒有多少悲傷和情緒宣泄,似乎對(duì)這樣的無疾而終早有預(yù)感。第二段情感亦是如此。素食般的戀情最后帶來的是知壽一個(gè)人的眼淚和辭職,在整部小說中可以算是鮮見的“情緒表達(dá)”,但即便如此,仍是虛無倦怠感充盈滿卷。同樣,在與吟子共同生活的日子里,知壽的心態(tài)和舉動(dòng)都表現(xiàn)得“平淡”、“微小”,如同小說中文版封面上的卷尾小貓,懶散而倦怠。
其次,除了知壽內(nèi)心的倦怠感以及個(gè)人本身對(duì)外界的疏離之外,社會(huì)大環(huán)境以及周邊世界的淡漠,也是造成其孤獨(dú)感的重要原因。日本向來不是一個(gè)“熱情”的國度,日本民眾非常重視保持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而隨著現(xiàn)代化社會(huì)的推進(jìn),大都市的孤獨(dú)感更是愈發(fā)強(qiáng)烈。芥川獎(jiǎng)評(píng)委石原慎太郎在對(duì)《一個(gè)人的好天氣》的點(diǎn)評(píng)中就這樣寫道:“縱觀近日社會(huì)上發(fā)生的諸般不詳事,可謂和平所釀造出來的有毒產(chǎn)物吧,令人感到人類以自我為原點(diǎn)生存下去的人生反命題的喪失。戰(zhàn)爭、大騷擾、對(duì)于生命的希求、貧困、偉大思想的消亡,等等,這些的喪失,相反地,使人們疏離,奪走人們之間的聯(lián)系,把各自變成軟弱的存在。尤其在大都市,更為嚴(yán)重。”在自幼父母離異的知壽的周邊世界里,無論是獨(dú)立的母親和概念模糊的父親,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都沒有給她帶來充分和必需的關(guān)愛。對(duì)外部世界的疏離和淡漠,并非知壽的內(nèi)心所愿,但也不是尋求改變的能力所及,這使得知壽的孤獨(dú)有了一種借口。
小說以第一人稱“我”為敘述者,“我”(知壽)的眼中有紛繁的外部世界,尤其是“地鐵站”這一場所的設(shè)定,本應(yīng)使“我”有更開闊的眼界看人待物,但恰恰這種紛繁的世界和“我”幽閉的內(nèi)心形成了鮮明的對(duì)比。如果一個(gè)人從內(nèi)心拒絕與外部世界產(chǎn)生聯(lián)系,就算整個(gè)世界都圍繞在其周圍,也必將感受不到其存在的價(jià)值和意義。而彌漫在外部世界中的孤獨(dú)感又加劇了個(gè)人孤獨(dú)意識(shí)的產(chǎn)生,使孤獨(dú)成為了生活中的一種常態(tài),也使小說的孤獨(dú)主題成為了可能。
二、女性意識(shí)下的自我成長
國內(nèi)對(duì)《一個(gè)人的好天氣》的先行研究,大多把知壽視為“飛特族”的一員,將知壽的孤獨(dú)感定位為整個(gè)“飛特族”人群,并引用青山七惠在接受采訪時(shí)所說的:“我想告訴他們,只要你肯邁出第一步,自然會(huì)有出路”,將《一個(gè)人的好天氣》定性為描寫“飛特族”的小說。雖然敘事者知壽確實(shí)屬于“飛特族”,小說對(duì)其生活狀態(tài)的描述也確實(shí)著眼于不安定性,但“飛特族”的定位,往往會(huì)使得讀者忽視青山七惠在作品滲透的女性意識(shí),而這恰恰是小說最成功、最具青山特色的部分。這種女性意識(shí)引導(dǎo)下的感知方式,決定了小說的基調(diào)、審美意象和故事走向。因此,《一個(gè)人的好天氣》中的孤獨(dú)給人帶來的,僅僅是淡淡的憂傷,而非感傷和苦悶。
所謂女性的自我意識(shí),就是女性對(duì)自我的全面認(rèn)識(shí),它包括女性關(guān)于自身的思想、感情、心理狀態(tài)、自我價(jià)值、能力特征、行為方式、自我控制和管理能力等方面的全部意識(shí)和思考。[3]關(guān)于女性意識(shí),文學(xué)批評(píng)家樂黛云做了這樣具體的分類:“女性意識(shí)應(yīng)該包括三個(gè)不同的方面:第一是社會(huì)層面,從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看女性所受的壓迫及其反抗壓迫的覺醒;第二是自然層面,從女性生理特點(diǎn)研究女性自我,如周期、生育、受孕等特殊經(jīng)驗(yàn);第三是文化層面,以男性為參照,了解女性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獨(dú)特邊境,從女性角度探討以男性為中心的主流文化之外的女性所創(chuàng)造的‘邊緣文化’,及其所包含的非主流的世界觀、感受方式和敘事方式。”[4]公元8世紀(jì)到12世紀(jì)的日本平安文學(xué)中,以紫式部的《源氏物語》為代表,女性開始書寫與女性自身相關(guān)的文學(xué)作品。作品中一系列貴族制度下被時(shí)代的男權(quán)枷鎖所束縛著的充滿悲劇命運(yùn)的女性形象,反映了在封建壓迫下女性開始努力爭取自身的一席之地,并表達(dá)內(nèi)心苦悶的女性意識(shí)。近代明治維新以后,以與謝野晶子、平冢雷鳥為代表的女作家們開始向不平衡的社會(huì)階級(jí)結(jié)構(gòu)沖擊,發(fā)出了女性參政和維護(hù)女性權(quán)益的呼聲,涌現(xiàn)了《短發(fā)》等強(qiáng)調(diào)“不要只顧道德,不要憂愁,不要畏懼”的追求自由、沖破階級(jí)和傳統(tǒng)男權(quán)束縛的女性文學(xué)作品。70年代中后期以來,小川洋子的《妊娠日記》、津島佑子的《默市》等從女性角度出發(fā),描寫出女性感覺中的婚姻、生育、家庭和性的獨(dú)特性別體驗(yàn)。至此,日本女性文學(xué)作品中的女性意識(shí),更多地體現(xiàn)于社會(huì)層面與生理層面對(duì)男權(quán)的抗?fàn)帲磉_(dá)積極而鮮明。而近年來,頻獲芥川獎(jiǎng)的年輕女作家在女性意識(shí)表現(xiàn)方面,更是開創(chuàng)了一片新天地,她們關(guān)注和書寫的是年青一代的女性,在相對(duì)寬松自由的社會(huì)環(huán)境中,女性意識(shí)的體現(xiàn)開始慢慢向文化層面滲透,并逐漸隱藏在輕松平淡的“無情節(jié)”敘述中。
除《一個(gè)人的好天氣》外,2002年芥川獎(jiǎng)得主大道珠貴的《咸味兜風(fēng)》和2003年芥川獎(jiǎng)得主金原瞳的《蛇舌》,其主人公都是在都市生活的年輕單身女性,均屬于“飛特族”,她們身上的獨(dú)孤、對(duì)生活的態(tài)度或多或少都有相似之處,然而三部作品卻又各自特色鮮明,并無雷同之感。究其原因,正是作家間不同的女性意識(shí),賦予了作品不同的感受。在《一個(gè)人的好天氣》中,知壽沒有跟隨母親去中國生活,而是選擇獨(dú)自來到東京,這個(gè)決定是知壽邁向獨(dú)立的第一步,對(duì)于為什么要來東京,小說中并沒有出現(xiàn)“我要獨(dú)立”之類的吶喊,而是借用知壽和母親之間平靜的對(duì)話,表達(dá)了她渴望走出家庭呵護(hù)、嘗試獨(dú)立的心理。而知壽來到東京后所過的平淡生活,實(shí)際上體現(xiàn)著她的與渴望獨(dú)立相矛盾的害怕獨(dú)立、不知如何獨(dú)立的心理。但在這種靜默的生活中,知壽作為女性的自我意識(shí)在慢慢復(fù)歸,她在自我體驗(yàn)、自我認(rèn)知、自我調(diào)節(jié)的過程中,逐漸實(shí)現(xiàn)了自我的成長和完善。小說的最后,知壽成為了公司的正式職員,她搬離了吟子家,開始了屬于她自己的新生活,這使“成長”由潛意識(shí)變?yōu)榉e極的意向。由“飛特族”轉(zhuǎn)變?yōu)椤罢絾T工”,知壽生活和職業(yè)上的穩(wěn)定并非“成長”的真正所指;在與吟子共同生活了一年之后,知壽開始了對(duì)自己的人生進(jìn)行認(rèn)真、獨(dú)立的思考,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成長”。在小說中,電車象征著人生前進(jìn)的方向,電車站前吟子的家象征著人生路上的歇腳點(diǎn),而最終電車的駛離,則預(yù)示著新生活的開始。
20世紀(jì)著名的心理學(xué)家和哲學(xué)家艾瑞克·弗洛姆將人從原始狀態(tài)中脫離出來從而獲得獨(dú)立性和力量的過程稱為“個(gè)體化”。他認(rèn)為個(gè)體化的過程有兩個(gè)方面:其一是“自我實(shí)力的成長”,而其二便是“日益的孤獨(dú)”。[5]知壽的“個(gè)體化”亦是如此,在打零工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被信任”,是其“自我實(shí)力的成長”,而孤獨(dú)的內(nèi)心,也是其獲得獨(dú)立、實(shí)現(xiàn)“個(gè)體化”的重要因素。同時(shí),弗洛姆還指出,對(duì)一個(gè)人來說,最大的需要就是克服他的孤獨(dú)感和擺脫孤獨(dú)的監(jiān)禁,而這只有通過“真愛”才有可能實(shí)現(xiàn)。這里的“真愛”不是狹義的愛情,而是包含了給予、關(guān)心、責(zé)任心、尊重和了解等諸多要素的人與人之間的真摯感情。在知壽與吟子共同生活的一年里,吟子以其七十多年人生經(jīng)歷所積攢的生活智慧和包容態(tài)度影響著知壽,而知壽也在潛移默化中學(xué)會(huì)了“愛”。對(duì)于和吟子的別離,知壽沒有像以往一樣掩飾自己的心情,“‘別哭啊!’說完就跑向了浴室。”而那些“偷來”的東西也不再給知壽以安慰了,在離開吟子家的前一晚,知壽想要偷偷地將之前拿走的小物件還給吟子,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吟子對(duì)自己“偷東西”的小癖好一直了如指掌,但是從未揭穿。知壽偷走周圍人的小物件,把玩并回憶這些東西的主人和她的關(guān)系,是內(nèi)心希望建立起與他人的聯(lián)系、克服孤獨(dú)感的表現(xiàn),現(xiàn)在知壽不需要它們了,是因?yàn)橹獕壑懒巳绾卧诮煌斜磉_(dá)自己的情感,如何在生活中保持與物主的聯(lián)系,這是其“愛”與“成長”的象征。
三、結(jié)語
總體來說,《一個(gè)人的好天氣》敘述的是年輕女性孤獨(dú)的內(nèi)心和自我成長的歷程。小說中沒有明顯的矛盾沖突,主人公思想情緒起伏變化不大,孤獨(dú)感的敘述并非無病呻吟,沒有過度的“告白”和矯揉造作,只是在簡單的生活里安靜地流淌。另一方面,女性意識(shí)被隱藏在孤獨(dú)平淡的生活中,不激烈、不外露,一年后的知壽不僅收獲了“愛”,更學(xué)會(huì)了給予“愛”,這是最本質(zhì)意義上的成長。在小說最后,知壽的離開,大都被解讀為“迎接春天”的成長,然而這種成長同時(shí)也伴隨著跨入“外部世界”的隱隱的孤獨(dú)和不安,可以說,這種女性意識(shí)下的孤獨(dú)和成長主題正是青山七惠創(chuàng)作得以延續(xù)和發(fā)展的一個(gè)關(guān)鍵因素。
[1]龍泉明.在歷史與現(xiàn)實(shí)的交合點(diǎn)上:中國現(xiàn)代作家文化心理分析[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2.
[2]左宇.倦怠的小曲與跌宕的悲歌——知壽與孤獨(dú)成長之比較[J].大眾文藝,2010,(3).
[3]張淑琴.論女性的自我意識(shí)[J].許昌學(xué)院學(xué)報(bào),1990,(4).
[4]樂黛云.中國女性意識(shí)的覺醒[A].張清華.中國新時(shí)期女性文學(xué)研究資料[M].濟(jì)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
[5]〔美〕艾瑞克·弗洛姆.弗洛姆文集[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