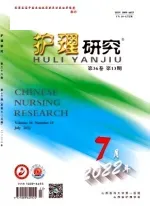循證護理在1例重度顱腦外傷病人家屬心理護理中的應用1)
陸佳韻,張永芳,葛津津
循證護理是一種工作方法,指導臨床護理人員在作出臨床判斷時,學會查詢研究證據、評鑒科研證據并利用科研證據,同時將所得到的科研證據與臨床經驗、病人需求結合,做出有效的、科學的護理計劃,提高護理質量[1]。重度顱腦外傷病人多因車禍、高處墜落等突發性意外傷害所致,發病急、病情重、病情變化快、病死率高。神經外科重癥監護病房(neurosurgery intensive care unit,NICU)消毒、隔離制度嚴格,屬于封閉或半封閉式管理,限制了病人家屬探視,這些都會造成家屬強烈的心理反應。2013年我科采用循證護理方法對1例重度顱腦外傷病人家屬實施心理護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現報道如下。
1 病例介紹
王某,女,56歲,為我科收治病人家屬。1d前搬家途中遭遇車禍,其丈夫因車禍導致重度顱腦外傷,急診送入神經外科重癥監護病房,意識不清,病情危重。當時,王某在監護病房外情緒激動,哭泣不止,坐立不安,從其丈夫入院后王某沒有吃過任何食物,拒絕遵守NICU探視制度,多次因為探視問題與醫護人員發生爭吵,并反復多次詢問醫護人員關于其丈夫的病情及預后信息,嚴重干擾醫護人員正常工作秩序。
2 提出臨床問題
病人家屬正經歷車禍導致親人重傷這個重大突發意外事件,NICU陌生的環境及其丈夫未知的病情預后等多方面原因使其出現嚴重的心理問題。針對病例特點,根據PICO原則,提出如下問題:①在NICU住院的病人家屬有什么樣的心理感受?②對重度顱腦外傷病人家屬實施心理護理是否可以改善病人家屬的不良心理感受?③個性化的探視與限制探視相比哪種方法對病人及家屬更有益?
3 檢索策略
3.1 檢索范圍 根據提出問題確定檢索關鍵詞,全面檢索循證資源網站:Cochrane圖書館、OVID循證數據庫、美國指南網(NGC)、PubMed、加拿大多倫多護理學會(RANO)循證資源庫、中國生物醫學文獻數據庫、復旦大學Joanna Briggs循證護理合作中心網站。優先檢索成熟的臨床指南、系統評價及大樣本隨機對照試驗,如果沒有,則依次補充小樣本隨機對照試驗(RCT)、非隨機臨床對照研究(CCT)、無對照臨床觀察、專家意見等,但需知這些證據的論證強度和可靠性依次降低。
3.2 檢索主題詞 采用主題詞檢索和自由詞檢索相結合的策略,中文主題詞包括:重癥監護病房、家屬、心理、探視模式、指南、系統評價、Meta分析、隨機對照試驗;英文主題詞包括:Intensive care unit,adult critical care unite,family members,psychological,visitation models,guideline,systematic review,meta-analysis,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限定檢索條件為出版年限2000年—2014年,語種為中文或者英文。
3.3 檢索結果 閱讀全文后篩選出2篇指南[2,3],2篇 系 統 評 價[4,5]、2 篇 RCT[6,7],1 篇 專 家 委 員 會 建議[8]、3篇描述性研究[9-11]。
4 評價證據
10篇文獻中,1篇來自Cochrane圖書館,1篇來自NGC,2篇來自OVID,6篇來自PubMed,將檢索結果根據RANO證據分級方法(2007版)和JBI證據推薦級別(2004)進行評價和分級,首先引用Ⅰ級證據,若無,則謹慎納入Ⅱ級、Ⅲ級證據。其中2篇指南列為Ⅰa級證據;1篇系統評價評價方法合理,但缺乏對RCT的總結故納入為Ⅱa級證據,另1篇系統評價證據來源于嚴謹的類實驗研究,但評價方法欠妥列為Ⅱb級證據;2篇RCT,設計合理,方法明確,真實性較高,納入為Ⅰb級,為A級推薦;3篇描述性研究為前瞻性多中心研究,納入為Ⅲ級證據,C級推薦;1篇專家委員會建議為Ⅳ級證據,D級推薦。
5 檢索結果
5.1 NICU住院病人家屬的心理感受 未找到關于NICU住院病人家屬心理感受的指南或系統評價,但在PubMed中找到3篇關于重癥監護病房家屬心理問題的前瞻性多中心調查研究。Pochard等[9]對法國43個ICU(包括37個成人及6個兒童)920例病人家屬進行了焦慮及抑郁量表的調查,研究發現焦慮和抑郁在所有家庭成員的發生率分別為69.1%和35.4%,其中配偶發生焦慮和抑郁的可能性更高,分別為81.1%和47.3%。Pochard等[10]隨后在2005年對78家ICU出院前或宣告死亡的病人家屬(544人)進行情感反應的調查,結果顯示焦慮和抑郁的發生率在家庭成員中分別為73.4%和35.3%,配偶存在焦慮和抑郁的比例(82.7%)明顯高于其他家庭成員(75.5%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7)。Azoulay等[11]在284例重危病人出院后,通過電話采訪病人家屬完成了事件沖擊量表(該表用于評估創傷后應激反應的嚴重性)、醫院焦慮和抑郁量表和36項簡易格式的健康普查,使用線性回歸的方式來判別與創傷后應激現象風險有關的因素。研究結果表明,創傷后應激癥狀符合中度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的主要風險值為9 4名家屬(占33.1%)。多項調查性研究結果表明,重癥監護室病人家屬存在的心理問題主要為焦慮和抑郁,有發生PTSD的風險,且配偶發生不良情緒比例高于其他家庭成員。
5.2 重度顱腦外傷病人家屬心理護理 在關于創傷后應激障礙管理的實踐指南[2]中建議,應首先做好相關評估,包括識別創傷暴露因素、不穩定的情況,如自殺、相關癥狀或精神情況等;其次提供教育和標準化預期告知,給予短期干預及急性癥狀管理。在PTSD的心理治療中包括對象的認知重組培訓或壓力管理治療、放松治療、意象操作療法(IRT)等。采用家庭會議或醫生-病人家屬溝通[3]的方式,是ICU醫療決策中的核心部分,早期干預對于家屬的經歷和長期的心理健康有著深遠的意義。Melnyk等[6]的一項隨機對照研究中,試驗組通過采用個性化的宣教、錄像或書面信息等措施,PTSD的癥狀下降了25%(P<0.05)。另一篇研究是關于法國ICU病人家屬的RCT,通過改進溝通的方式如進行家庭會議、結合病人信息小冊子的方法,結果顯示試驗組的PTSD得分以及焦慮、抑郁值均下降(P<0.001)[3]。Lautrette等[7]的一篇干預降低家屬焦慮的系統評價,認為滿足家屬的需要是對家屬最有利的干預措施,醫護人員和家屬在病人入院的時候就需要建立相互尊重、信任、同情和合作的關系。
5.3 個性化探視與限制探視效果比較 在探視模式方面找到1篇2011年發表的系統評價[5]。該系統評價通過定量與定性研究結合,評估并綜合成人重癥監護室探視模式的最佳證據,建議采用與以“病人及家庭為中心”(PFCC)的護理理念相一致的個性化探視方式。護士相信探視有利于病人的康復,但開放式探視/或個性化的探視模式,增加護士的工作量。美國重癥護理協會(AACN)于2011年發表關于探視的實踐警示公告[8]中建議,可根據病人的喜好,讓他們選擇自己喜歡的支持人員,每天24h無限制探視。證據顯示,支持無限制的探視模式,可以改善醫患溝通,便于更好地理解病人,提高病人和家庭在ICU的滿意度,除非這種探視影響到病人的治療或安全。但開放式的探視模式也應根據醫療機構的決策或實際情況而定。
6 應用策略
根據上述循證證據,結合病人的心理需求,我們與病人加強了溝通,了解病人家屬的需求,對其合理需求及時給予滿足,同時向其進行疾病知識的指導。與病人建立合作式護患關系,醫生、護士與家屬一起討論病情,讓家屬及時了解病人的治療信息和疾病預后。改變現有重癥監護病房限制探視管理模式,在保證病人治療及安全的前提下,盡量滿足家屬的需求。為家屬提供隔離衣和口罩,在做好防護的前提下允許家屬陪伴在病人身邊,并告知其健康與支持病人治療的重要性,使其主動關注自身健康。
7 效果評價
在醫護人員的積極治療和家屬的配合下,病人病情穩定,1個月以后痊愈出院。在重癥監護病房陪護的1個月里,護理人員根據上述心理護理措施與病人家屬建立了融洽的護患關系,家屬情緒穩定,積極配合治療,對醫護人員工作表示滿意。
[1] 胡雁.正確認識循證護理 推動護理實踐發展[J].中華護理雜志,2005,40(9):714-717.
[2] Management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Working Group.VA/DoD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for management of post-traumatic stress[M].Washington(DC):Veterans Health Administration,Department of Defense,2010:251.
[3] Curtis JR,White DB.Practical guidance for evidence-based ICU family conferences[J].Chest Journal,2008,134(4):835-843.
[4] Leske JS.Interventions to decrease family anxiety[J].Critical Care Nurse,2002,22(6):61-65.
[5] Ciufo D,Hader R,Holly C.A comprehensive systematic review of visitation models in adult critical care units within the context of patient-and family-centred car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vidence-Based Healthcare,2011,9(4):362-387.
[6] Melnyk BM,Alpert-Gillis L,Feinstein NF,et al.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parent empowerment:Program effects on the mental health/coping outcomes of critically ill young children and their mothers[J].Pediatrics,2004,113(6):e597-e607.
[7] Lautrette AI,Darmon M,Megarbane B,et al.A communication strategy and brochure for relatives of patients dying in the ICU[J].N Engl J Med,2007,356(5):469-478.
[8]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ritical-Care Nurses.Family presence:Visitation in the adult ICU[J].Critical Care Nurse,2012,32(4):76-78.
[9] Pochard F,Azoulay E,Chevret S,et al.Symptom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family members of intensive care unit patients:Ethical hypothesis regarding decision-making capacity[J].Critical care medicine,2001,29(10):1893-1897.
[10] Pochard F,Darmon M,Fassier T,et al.Symptom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family members of intensive care unit patients before discharge or death:A prospective multicenter study[J].Journal of Critical Care,2005,20(1):90-96.
[11] Azoulay E,Pochard F,Kentish-Barnes N,et al.Risk of post 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in family members of intensive care unit patients[J].American Journal of 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2005,171(9):987-994.